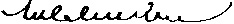魯伊·洛瑞羅教授作為本期文獻專輯的選編者,對入選文章所作的説明性和導論性的案語與序論,已足以代替本期《文化雜誌》的編者前言了。本期文獻的主要內容實際上已囊括在他的序文之中,它向讀者闡明了作者與編年史關聯的時空背景,並為讀者對所述事實的深入解讀作了引介的鋪墊工作。
《文化雜誌》出版這樣一個專輯,除了內容緊湊而激動人心之外,特別是為中國的歷史學者提供了一束資訊性質的視焦,借此可以更好地明瞭葡萄牙人民同中國相接觸以及加以瞭解的初期情況,並對由此而引發的“相互理解”作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提供可能並予以激勵。為此,本刊亦深感榮幸有加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文獻選編者的初衷就是想挑選帶有贊美色彩的文章。這種色彩,幾乎自始至終一成不變地貫穿於這些按照編年序列組排而歷時大約150年的對中國所進行的“觀察”的報導之中。早期的“觀察”,並非屬於直接性的,後期則是目擊者置身於當地生活的真情實感。
文藝復興之後,歐州曾以世界各民族和諸文化國際交響曲之中的超級文明者自居。為此,她沉迷於一個帝國的龐大和精巧之中,以表明她在文化和社會-政治等廣闊領域的優越地位。
根據國家的架構,以及諸如“天之等級”或“神聖的官僚體制”等觀念,建起了宏偉的行政金字塔,構成了一個真正的“文字的共和政體”,以皇帝為其頂點,形成了過去文明史的典型模式。
中華帝國衰落的原因儘管總是神秘莫測,其諱莫如深之處亦有待澄清,然而,在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之前不久,其歷史時刻便已明朗化了。在我們看來,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其漫長的探索和思考中,並未對造成中國科技落後狀況的現象作出完滿的解釋。就在那個時期,歐洲的科技狀況則與中國社會進步的逆轉恰成對照。
我們認為,無論如何,事實似乎是這樣的: 如果説,早期軍人、商人和傳教士的文章有所神話化的追述曾經引起對“中國方面”的誘惑作用的話,那麼,在後期,耶穌會士的著作家們的某種敘述方式則是為延續其遠東傳教的專利作出辯護而提出的一種“資訊策略”,正因為這一點,他們成為其他教團妒忌甚至嫉恨的對象。
許多編年史家的評價集中在兩個“可鄙”的方面: 傳説的中國人盛行雞姦;或者説中國人的外表“孱弱不堪”。
旁人的第一印象總是膚淺的,並且視焦往往會發生偏移: 觀察者的透鏡往往呈現主觀的色彩。上述兩個事例毋疑是由旁人自以為是的道德教條和淺薄的人類學-文化學傳統知識所造成的。
偉大的中央帝國朦朧地呈現於葡萄牙人的眼前。首先呈現的是一片令人眼花繚亂的迷人情景: 這是一種偉大的、中庸苟且而又遼闊無際的農業文明;一派女性(或陰性)的世界景象,這個世界中的一切都帶有此種象徵的特點並受其制約。
我們總是在其曆法的節律之中,在政治權力的戲劇化搬演之中,在軍事力量的崢嶸顯露之中,在攻擊性強勢昇華為禮儀的至高無上之中窺見了中國特色。
需要暴力強制、鎮壓行勳的強權是虛弱的。相反,皇帝理應受到尊敬,對他要無可爭辯地服從。他身上滙集着令人生畏的威嚴,這是神賜予的力量,根本無須解釋。他體現着權力的至高形象,是一種全然外化了的天意,一種絕對的軸心: 是最純粹的“陽”的化身,是天之驕子。
正如中華帝國鄰近諸國之臣服於中國,全國各省府鄉鎮和所有家庭均俯首聽命並絕對地服從於天子。
從這種權力禮儀化的最高形式中,從這種在中華帝國國境線內外的強勢和攻擊性力量中衍生出來的,是一種良性的被動形態,一種中國式的和平,從而昇華為道德誡諭的觀念。
鄭和舉世無雙的海上航行,目的並非野心的擴張膨脹,而是以這種方式作為向中華帝國的臣屬國家再次炫耀其偉大國力的需要。
在早期的西方人看來,中國男性在某些社會習俗和行為規範上似乎太女性化了。而西方男性則完全處於一種兇狠好鬥的文明圈中,然而這種文明早已失去了騎士道德的義勇遺風。
中國的耶穌會士編年史家,滿懷道德信條,並將其信條與聖經懲罰的熊熊烈火聯繫起來,面對“醜陋的罪惡”,表示出極大的憤慨。基督教曾經力圖使人忘記希臘、羅馬和東方的強權國家。
事實上,從中央朝廷到各個總督大臣的衙門,皇家太監是權力中心極端化的某種體現。在中華帝國,皇妃寢宮以太監為侍僕是普遍現象。據《周禮》記載,這種慣例源於周朝(公元前1100年-前256年)。在1460年一次同南方苗族(Miaos)的戰役裡,就俘擄了一千五百六十五名青少年男子,全部被閹做了太監。
在皇宮那重重簾幕背後和重重迷宮之中,千百名太監同皇帝的寵妃結成天然的聯盟,變得愈加缺乏男子氣概,然而宦黨的權勢卻越來越膨脹。有時,太監大耍陰謀詭計,刺探內情,串通勾結,玩弄權術,在宮廷皇室的小範圍內,聚集與扶植特種權力,變得越來越有威勢。
晚明時朝,耶穌會神父進駐北京皇宮,耳聞目睹了特別是從永樂皇帝開始的被宮闈太監腐朽力量侵蝕得極其衰敗的朝廷內部情景。同類現象在以前朝代的滅亡中也曾經發生,如東漢、唐朝和宋朝。此種現象實始於秦朝(公元前210年),當時,整個政權全部落入太監趙高之手。
關於上述的歷史事實,中國的早期編年史家一定“目擊”過這類傳聞的真相,並且一定對此作出過批判,尤其是在其感性的外在性方面。
有關中國男性的“女性化氣質”,利瑪竇在其著作《中華見聞錄(1608-1610)》也有記述:
我們對於同伴當中有一位戎裝男子,認為是件值得高興的事。然而對於他們來説,卻被認為那是不雅觀的,他們甚而擔心看到如此可惡的東西。因此,他們沒有任何爭鬥或騷動。而這種事情對於我們來説,為著洗去某種侮辱而動武決鬥,簡直就是家常便飯。他們認為,最為榮耀的人是那種一直退讓並且不傷害任何人的人。
利瑪竇對中國軍隊感到“沮喪”,他覺得他們刻意追求戲劇性效果、大肆排場或進行大場面大規模的練兵表演,對於他們在大型節日慶典上燃放煙花使用大量火藥而非用於軍事目的更感吃驚。他看到軍人來自社會的底層:
在我們當中,祇有較為高貴而勇敢的人才能成為軍人,在中國卻是最低賤而卑怯的人才會去服兵役。
1583年利瑪竇向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寫道:
我極其榮幸地向閣下致函,敘述中國人的實情,我將不會説中國人是好戰的人,因為他們無論外表還是內心,都像女子;如有人向他們挑釁,他們便會屈服,任何一個征服他們的人,都可以使他們俯首聽命。中國男人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來梳理頭髮,並且小心翼翼地穿著打扮,他們將其所有的最美妙的時光用來做這些事情。對於他們來説,退讓、凌辱和侮辱並非像對於我們那樣認為是羞耻之事,他們祇會表示一種女性的慍怒,相互撕扯對方的頭髮,而他們一旦對此感到厭煩,又會重歸於好。他們極少互相毆鬥彼此傷害或決鬥凶殺,即使他們有這種念頭,也缺少器械,這不僅因為士兵很少,更因為他們之中的大部份人的家裡連刀也沒有。總而言之,根本不用害怕他們,他們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罷了……
很明顯,在這些文章之中表現和展示出來的社會,符合文明的一種高級狀態,在這種狀態之中,攻擊性已得到昇華,並被加以禮儀化了。
然而,同樣明顯的是,在利瑪竇的上述引文和其他眾多作家的文章之中,對偉大中華帝國的“虛弱”和缺乏戰鬥力的報道,遮蔽了由於一個西歐強國的征服性探險而黯然失色的活力。
我們從不斷增加的各種研究計劃方面,從歷史文獻中瞭解了這種活力的存在。這在後來得到了印證和回應,並且早已成為眾所週知的事實。
從各個角度來看,明朝的政治家們是富有睿智、遠見和腳踏實地的,他們對葡萄牙人租踞澳門採取寬容的態度。靠着這一點,中國的完整性得以延續且已超過了兩個世紀之久。
總而言之,無論如何,伊比利亞文獻對中國第一印象的評估顯然是積極的,特別是16和17世紀葡萄牙文獻中所傳達的形象,那是往後歐洲在18世紀對中國所作的一種熱情奔放的發現的前奏。此中奧妙,祇要看對於某些最為翔實地報道中央帝國的著作之不斷再版,便是最好的證據。
《文化雜誌》總編輯官龍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