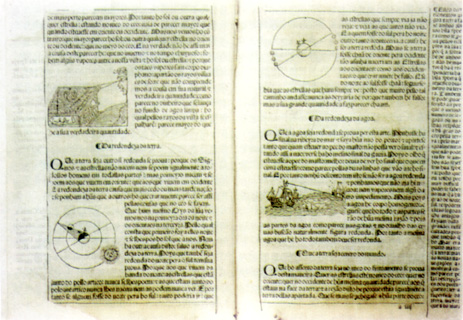 貝德羅·努內斯《球體論》中的一頁(里斯本,1537)
貝德羅·努內斯《球體論》中的一頁(里斯本,1537)
現代歷史學家已經對葡萄牙人16世紀在東方的歷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並由此為其塑造了相當嚴密和完整的形象。(1)但由於當時葡萄牙同亞洲的關係十分密切,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廣闊,而且時間漫長,加之由此產生的書面資料非常浩繁,人們總是還可以找到一些至今仍若明若暗的領域,總是能找到一些很少有人探討過或根本就沒有人探討過的然而又有必要進行新的或進一步探討的領域。比如在文化史的某些方面就是這樣。對於這些方面,人們過去在研究有關政治、軍事或經濟方面的問題時常常被忽視了。我們必須重新鑽進過去的史料堆裡去,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有創見的探索。
有關那段時間歐洲書籍和讀物在東方的歷史無疑是被我們的史家忽視研究的諸多題目之一。試想我們今天對16世紀那些懷着建立榮譽和尋求利益的夢想而遠涉重洋駛向印度的葡人的閲讀習慣到底知道些甚麼呢? 他們持之以恒地讀書嗎? 他們讀些甚麼書呢? 他們是否隨身帶去大批書籍? 他們一到東方是否就開始建立大圖書館? 在那裡他們有沒有繼續收到家人和朋友自家鄉寄去的書籍?
那時,我們的先人每年一批批地從里斯本乘船離開特茹河,揚帆出海遠航。那麼,他們是否就將自己家鄉和歐洲的文化置諸腦後了呢? 顯然沒有。他們的日常生活在穿越漫長的“海路”(2)期間儘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他們並沒有忘記將其文化模式、文化習俗和文化價值觀傳播到亞洲的土地上,這些東西在那裡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當地非文化因素的影響,但它們始終保持着自身的運作和繁衍之相應的規律。祇要我們對那個時期的大量史料進行一下概略的調查研究,就不難發現一些反映那時緊張的文化生活的可靠的蛛絲馬跡。事實上書籍和其它讀物在當時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建設的指南和傳播知識的正常途徑,而且也是在遙遠的異鄉灌輸我們民族精神的戰略武器。
的確,葡人在踏上東方土地後的最初年代最迫切的使命是偏重於物質方面的,即他們的優先任務是航行,征服,做生意,而文化問題則被擺在次要位置上。但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當時所有的“職業”船隻除載人和武器、糧食、彈藥之外,也都越過海洋帶去我們的風俗習慣、法律制度和精神思想,總之為那些新發現的地區不可避免地帶去了一個古老文化及精神世界。我們祇要回憶一下達·伽馬(Vasco da Gama)首批船隊就不難看出這點了。在他的船隊裡,不僅有水手和兵士、船長和管理人員,而且還有負責同盛產香料和甚它特產的亞洲地區建立第一道溝通橋樑的文人。正因為這樣後來才有阿爾瓦羅·維利奧(Álvaro Ve1ho)和若昂·費格依拉(João Figueira)寫出反映大發現之旅的珍貴作品,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向人們展示了葡人在征服、佔領和宣傳新的地域和社群的過程中用文字來記述其業績的必要性。(3)
我認為做出下面的結論是合乎邏輯的:一開始從里斯本登上遠航之船的許多人的行李中就帶上了各種各樣的書籍,或者説得更廣泛一點,就帶上了各種各樣的書面材料。至於都帶些甚麼,則完全取決於每個人當時的文化水平,取決於他們各自未來在陌生的土地上和浩翰的海洋中將擔任的特殊便命。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由於職業的原因,需要帶去適用的印刷書籍或手稿。駕駛戰船和三桅帆船的駕駛員在履行其職責時必須使用技術書籍,包括曆書、航行資料匯編、航海圖及航海手冊等;他們根據這些書籍和資料沿着先前開闢的航道行駛;當然,有時也新發現一些書上還沒有記載的航路(4)。宗敎人士則隨身帶去傳播福音所需要的工具書籍,比如《聖經》、《彌撒書》、《聖詩集》和《基督手冊》等,他們後來利用這些東西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傳播福音的工作。至於踏上東方航道的王國官員們,尤其是那些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他們也沒有忘記隨身帶去自己擔任相關職務所需要的書籍,如《王國法典匯編》和其它法律業務書等。與此同時,那些指揮官、監察員和管理人員則帶去了履行其職責所需的各種法律規章條例。
葡萄牙船隊中的另外一些人,出於個人的需要,在各自的行李中還帶了些認為對自己有特殊用途的書籍。物理學家和藥劑師們旅行時不能不隨身携帶那些對於他們的職業最為必需的專業用書和手冊,甚至常常携帶大量他們之前在其長期的業務工作中不厭其煩地收集整理的手稿資料(5)。一些較有文化修養的紳士以及普通平民百姓在其行李中便帶些技術性不太強的、但更適合用來供他們在旅行途中不可避免地將會面對的枯燥無味的漫長時光的消遣物。總之,一次從里斯本到果阿的正常旅行,即使在氣候極好的條件下,也很少有不需要半年時間的。這麼長一段時間對於所有那些不是以海洋事業為職業的人來説,是一定需要想方設法用一種盡可能令人愉快的方式來渡過的。(6)
葡人一在亞洲地區建立了第一批定居點之後,就立刻關心起如何透過在那些地區敎授葡國語言和文化及基督敎義來鞏固、加強和傳播其民族文化模式了。這一敎學活動是由非宗敎人士和敎士們共同開展的,其對象不僅是葡人自己以及他們的亞洲妻子和後代,而且也包括所有居住在他們所征服地區裡的東方人。他們在敎學中所用的基本敎科書就是《敎義問答簡編》(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該書由休達市(Ceuta)主敎維列加斯所著,大約於1504年由瓦倫廷·費爾南德斯和若昂·佩德羅·布奧紐米尼德·克雷莫納在里斯本印刷出版(7)。幾年後編輯出版了一些更好的敎科書,其中一部份甚至是雙語的,如:《泰米爾文基督敎義》,該書由恩里克·恩里克斯神父編纂,於1578年在奎隆(Coulão)出版;又如:馬科斯·若爾熱編寫的《基督敎義》也是用泰米爾文寫成的,於次年即1579年在科欽(Cochim)出版。(8)
阿豐索·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於1509-1515年間在印度的葡佔地執政,他很關心加強我們葡人在那裡的存在;根據當時的一個編年史學者的著作,他命令“許多”科欽的印度青年去“官立學校學習文化”(9)。到1517年(這時這位“魔鬼般”的統治者已死),在校學習的科欽年輕學生人數已超過一百五十人,因為根據史料記載,當時擔任敎學任務的安東尼奧·洛羅修士收到了從葡萄牙寄來的同樣數量的基督手冊(10)。1521年當時的總督梅內西斯(D. Duarte de Meneses)命令向那個城市的市長提供“五十本基督敎義手冊、五本《聖徒列傳》和四本《福音書》”,供敎授年輕的基督徒使用(11)。《葡文聖徒列傳》是一部關於聖徒傳記的浩繁著作,由里斯本赫爾芒·德·坎波斯及羅貝托·拉貝洛印刷所於1513年出版。(12)在果阿的情形也完全一樣:它一被佔領,葡人就在那裡積極開辦培養年輕的基督敎徒的學堂。有資料記載,在1521年就有兩百本基督敎義寄到那裡,供進行基礎敎學之用。(13)這一事實清楚表明,基督敎徒的人數當時在不斷增加。
葡萄牙王朝除了重視在印度的定居點外,還對當時叫做“普列斯特若昂”(Preste João)的王國給予特別的注意,因為在16世紀頭幾十年在葡萄牙出現一個可能同埃塞俄比亞建立戰略同盟以反對伊斯蘭敎的熱潮。因此,當時的國王唐·馬努埃爾一世於1515年給里斯本派駐埃塞俄比亞的使團寄了一千五百本左右的書籍去(其中大部份是印刷的)。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葡萄牙當局也在這裡下大力氣來實施一個文化傳播計劃,儘管這一計劃帶有強烈的宗敎成份。
在寄往“普列斯特”王國的大量宗敎書籍中,包括一千本有羊皮紙封面的《基督手冊》,十二本《敎義問答集》,二十本《使徒列傳》,三十冊《殉難聖徒的功勳及情懷傳奇》(該書是由若昂·佩德羅·德·布奧紐米尼於1513年在里斯本印刷出版的)(14),以及一百本關於耶路撒冷修道院被毀的歷史,其原文書名為:《崇高的羅馬帝王史》,該書由瓦倫廷·費爾南德斯於1496年在里斯本印刷出版。(15)這一事實證明,當時還很年輕的葡萄牙印刷所早就開始為海外市場服務了。
相當可能的是,運往埃塞俄比亞的所有書籍是先運到印度的,然後才分發到各個葡萄牙人的定居點,因為根據自1512年便生活在印度斯坦的編年史學家加斯帕爾·科雷亞(Gaspar Correia)所述,寄到“普列斯特若昂”的珍貴禮物--顯然它不限於印刷品,還包括其它許多貴重的東西--本來是供在科欽的總督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里亞使用的(16)。也許在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幾年之後在意大利流傳着一種説法,説佛羅倫薩人安德烈·科爾薩利已經同葡萄牙使者一同去埃塞俄比亞了,而且可能在埃塞俄比亞的土地上定居了,並説他在那裡經商,而且從事印刷出版迦勒底語作品。(17)
然而,從葡萄牙運來的書籍並非僅用來進行基礎敎育,因為在印度建立的宗敎團體從一開始就創辦專業圖書館,這是當時傳播我們文化的又一中心。於是在1518年1月,洛波·蘇亞雷斯總督便將“兩大箱印刷出版的書籍”交給了居住在科欽的方濟各會修士們。(18)在這批由三百本著作組成的書庫中,包括不少印刷珍品,比如其中有一本意大利奧古斯丁敎團敎士雅科普·菲利普·弗雷斯蒂·達·貝爾加莫編撰的《補充編年史》就屬於此類;這本鉅著記載了東方的種種奇蹟,於1483年在威尼斯首次出版,以後又多次再版;還有四部由盧多爾夫·德·薩肖尼亞撰寫的《基督生活》葡文版本,這套不朽巨著是由尼科勞·德·托馬斯和瓦倫廷·費爾南德斯·達·莫拉維亞於1495年在里斯本印刷出版的(19);還有三本由聖·托馬斯編寫的《概況》,這一作品可能還出版了若干西班牙文版本;以及四本《迷人的森林》,它是1515年由里斯本赫爾芒·德·坎波斯印刷所出版的。(20)約在兩年之後,卡納諾爾敎堂收到葡萄牙國王寄來的供宗敎事務使用的“四本鉅著”,它們都是“精裝和大開本的”(21)。
也許可以這樣概括地説:凡是存在葡萄牙人社群的地方,特別是那些居住有宗敎人士的地方,都有敎學活動的開展,而在這些敎學活動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葡文書籍,由此形成了從波斯灣的霍爾木茲島(Ormuz)到馬魯古群島(Molucas)整個亞洲沿海地區的戰略地位,不同程度地推廣葡萄牙的語言和文化,建立有着不同重要性的圖書館。
大約於1540年,維森特·德·拉戈斯修士在科蘭加諾爾(Cranganor)創建了第一所學院,在這所學校裡不僅傳授基礎知識,還進行高等拉丁文敎學和神學教育(22)。幾年之後,這位敎士列了一個很長的書單,請求國王唐·若昂三世“給這所學校寄書來”;在這個書單中包括“日課經袖珍本若干,聖母祈禱經若干,玫瑰經袖珍本若干,一本大開本玫瑰經,一本供唱詩班用的大開本彌撒書,六本袖珍彌撒書,還有各種有關語法的書籍”以及許多別的書籍(23)。祇要考慮到當時虔誠的國王所實行的積極支持傳敎事業的政策,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不相信這位修士的請求是沒有得到滿足的。(24)在16世紀中期,類似的學校在巴薩印、沙萊、科欽、卡納諾爾,奎隆和鍚蘭等地都有創辦。(25)
葡人在印度創辦的這些學校中,最知名的也許要數建在果阿的聖保祿學院。它開初是由皮埃達德省的敎團神父領導的,但從1545年起改由耶穌會管理。僅在這之前三年來到東方的耶穌會士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所以他們立刻便成了該校敎學和佈道活動的主力軍。後來這所“聖潔信仰學院”(這是當時民眾對耶穌會所辦敎會學校的稱呼)成了一所真正的高等學府,它一向採用當時歐洲大學所實行的敎學組織形式和敎學計劃。(26)
在這裡有必要指出,東方耶穌會使團的創始人沙勿略神父(Francisco Xavier)在1542年到達果阿時,他的行李中裝有由國王若昂三世送給他的大批重要書籍。(27)這些珍貴的書籍全是關於宗敎方面的,這表明當時來到東方的葡人很重視書籍,很重視至少在傳敎士中開展閲讀活動。
在1545年,果阿的尼科勞·蘭西略托神父為其耶穌會學院向國王索取了一批書籍,他在申述其理由的時候説,他們當時祇有“四十五本維爾吉利奧的作品和另外四十五本特倫西奧的作品”,而且所有這些書都“非常陳舊,並且有許多錯誤”(28)。顯然,他在這裡提到的是説,他們當時祇有供耶穌會學校使用的拉丁文小冊子,其中僅刊登了維爾吉利奧和特倫西奧的一些文章。這位神父向葡萄牙國王請求資助購買一些“本校所需的書籍、地圖及文具等物”(29)。同年底代理主敎米格爾·瓦斯也向國王若昂三世請求要一批“供學生用的語法書”以及“一些有關語言的書籍”供傳敎士們使用。(30)
尼科勞·蘭西略托於1546年在一封信中列舉了聖保祿學院在拉丁文敎學中所使用的著作,從而揭示了該校圖書館的某些秘密。在這位傳敎士列舉的書目中有特倫西奧著的喜劇《安德里亞》和《科學藝術小冊子》,維吉利奧的《田園詩》,奧維迪奧的《變態》,卡唐的《少兒讀物》,聖熱羅尼莫的《歌劇》,甚至有埃拉斯莫的一部名為《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ac Rerum》的作品。(31)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外國出版的,這説明耶穌會作為一個國際間的組織是如何熱心傳播各種世界名著的。此外,在上述書目中還包括達米昂·德·戈依斯的一部“關於阿比西尼亞王國人民信仰”的作品:《信仰、宗敎和埃塞俄比亞人的生活及行為方式》,該書於1540年在洛瓦納印刷出版,於1543年由一支船隊運到果阿,然後再從那裡寄到耶穌會學院。(32)
另一個證明敎會開辦有圖書館的例子是加斯帕爾·巴爾澤烏斯神父於1550年從霍爾木茲寫給科英布拉耶穌會敎士的信。他在該信中説,葡萄牙人在波斯灣的那個定居點所建立的傳敎機構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33)。兩年之後,他的一個同事又寫信説,在他們生活的那個島上,隨時都有遭受當地士兵襲擊的危險,因此所有的葡萄牙人,包括他本人在內,都將“他們的財寶放進了那裡保存着各種各樣書籍的城堡”(34)。
耶穌會創立的果阿學院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圖書館,因此在1552年為該圖書館專門配備了一名管理員,並正式制定出了居住在那裡的神父和敎友們閲讀圖書的書面規章制度(35)。兩年之後,這個圖書館的一部份圖書交由貝爾希奧爾·努內斯·巴雷托神父保管,後來由於他準備到日本去旅行,同時去執行傳播福音和外交之使命,很可能將這些書帶去了日本。果阿耶穌會所開辦的圖書館之藏書究竟有多麼豐富,我們可以透過運到日本群島的書籍目錄單來估量(36),在所運去的書中除有大量的宗敎書籍外(如《聖經》、《儀典書》、《日課經》、《聖人名著名言集》等),還有以下作品:聖·托馬斯·德·阿基諾的《科學藝術小冊子》若干本,1545年由科英布拉的若昂·達·巴雷拉和若昂·阿爾瓦雷斯印刷所出版(37);馬爾科·馬魯利克的《優秀作品集》,它一部聖徒列傳,可能還有拉丁文版(38);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多部作品;托勒密的一部作品,也許是一本《地理誌》,或是它附在佩德羅·努內斯的《地球學》裡的葡文譯本,該書1537年由熱爾芒·加利亞德印刷出版(39);盧多爾夫·達·薩肖尼亞的《基督生活》,該書前已提及;托馬斯·德·肯皮斯的《可鄙世界》,1542年在里斯本熱爾芒加利亞德印刷所首次出版(40);《敎堂史》,於1541年由里斯本路易斯·羅德利格斯印刷所出版,作者不詳,但它是由埃烏塞比奧·德·賽薩雷亞編輯的(41);恩雷庫斯·德·赫爾普夫的《完美的鏡子》,由科英布拉聖十字修道院於1533年出版;聖·博阿文圖拉的《聖神的愛的鼓舞力量》,里斯本的熱爾芒·加利亞德印刷所於1550年出版的(43)。
所運去的作品中,一些是在葡萄牙剛剛出版的,另一些則是從歐洲其它國家進口的。這些事實一方面説明當時出版的各種書籍在葡萄牙與其東方屬地之間流通速度之快,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當時已建立起來了的各國之間書籍文化交流水平之高。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穌會士們在促進書籍流通和開展閲讀活動中做出了傑出貢獻,他們所從事的這項事業是有着明確目標的。正因為如此,他們向讀者提供的閲讀材料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並且要對他們的閲讀情況經常進行檢查。這方面的例子在遠征者的通信中、特別是在那些講述印度之旅的信件中比比皆是。(44)當然,與此同時,從他們的通信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沒有宗敎修養的一般讀者在從里斯本到果阿的漫長旅行中是讀些甚麼類型的書來消磨時光的。
一個於1560年登上葡萄牙商船的神父看見船上放有許多“褻瀆神明的書籍”,於是公開表示反對。他後來對他的敎友們説,他當時在船上規勸旅行者把那些書扔到海裡去,“我向他〔們〕指出閲讀那些書會給他們帶來的危害”,在情況嚴重時,他甚至把“一些青年人手中的極壞的書奪過來撕得粉碎”(45)。兩年之後,另外一個耶穌會士曾經不得不咬了一個青年人的胳膊,其目的是為了使他馬上扔掉正在閲讀的“一本壞書”;“當他把書扔到海裡後,我就立刻給了他三本好書,於是那位青年才高興起來”。(46)為了防止有人使用非正統的書,有些乘船的神父在整個旅途中都向公眾朗讀“一些關於敎會歷史的書或關於宗敎的其它書籍”(47)。有一個於1566年乘船去東方的耶穌會士甚至向他的上級建議讓同船的所有傳敎士都讀優秀的宗敎書籍,以便能夠消除葡萄牙人平常乘船時總是讀隨身携帶“壞書”的不良現象(48)。
耶穌會士究竟禁止些甚麼作品呢? 甚麼作品被認為是褻瀆神明的呢? 甚麼書是被認為是不能讀的呢? 實際上,他們不僅把自1547年出的--開始是手抄的、後來是印刷出版的--作品被陸續列入敎會的“禁書目錄”(49),而且還可能把那些他們認為可能導致信徒們背離敎會宣揚正道的小説和消遣讀物也都當作禁書了。對於這一點,我們至少可從一個於1564年踏上“東方航道”的耶穌會神父的一封信件中看到。他在信中談到,在旅途中有很多書籍被扔進大海,其中“一些是禁書,一些是無名氏作品,還有一些是騎士讀物”,但是它們都是“不道德的書籍”。(50)在那些耶穌會士們害怕得要命的騎士讀物中,肯定包括若干本吉奧瓦利·博卡西奧的作品《費亞梅塔傳》(里斯本,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印刷出版,1541年),博斯坎和阿爾庫納斯·德·加爾西拉索·德·維加的某些作品(里斯本,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印刷所出版,1543年),無名氏作品《勇敢的英國王子弗洛蘭多編年史》(里斯本,熱爾芒·加利亞德印刷所出版,1545年),以及其它內容類似的作品(51)。
至於西班牙的情況,比我國研究的要深入得多,我想或可用來做一對比。我們鄰國的宗敎裁判所通過對其駛往印度航船的調查,得以較為準確地弄清乘客在船上的閲讀習慣。西班牙船隻很少有不帶大量印刷出版的書籍的,儘管它們的航程幾乎沒有一次超過兩個月的。他們船上帶的書主要是關於宗敎的,比如彌撒書、聖徒生活雜記、敎皇及大主敎史話、宗敎傳奇故事、道德訓誡等。但許多船隻也帶了一些關於進行冒險的和關於騎士生活的書,這些書不是散文就是詩歌,比如:盧多維克·阿里奧斯托的《憤怒的奧爾蘭達》、高拉的《心愛的人》(1578年在里斯本出版)、《費博騎士》、《英國香客》(1587-1592年間在里斯本出版),以及《卡斯蒂利亞油橄欖樹》。別的船隻還帶了民謠集和詩歌集,以及(關於歌頌儒里奧·塞薩爾、埃爾·西德、赫爾南·科爾特斯、弗蘭西斯科·皮薩羅等人的)英雄故事集。船上還帶有一些詩歌,儘管其數量不多,主要是以維吉利奧和奧維迪奧為代表的古代詩人的作品。(52)葡萄牙讀者喜歡讀的書籍沒有超出這個範圍,祇不過他們更愛讀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各國國家之間流通的具有文化價值的書籍。(53)有一個於1578年出發去東方的耶穌會士曾證實説,放在葡船上的許多書籍中有一些是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本。(54)
有一些從里斯本上船去東方的旅客在各自的行李中可能還帶了許多個人用的書籍,有的人所帶書籍之多足以裝備一個不小的圖書館。我們知道,在去印度的許多人中有不少是高級智識分子,為了與其所具有的文化修養相稱,他們不能不帶去適當數量的書籍。在這點上,如果同西班牙的情況相比,也存在類似現象。比如有個西班牙皇家的官員於1583年去菲律賓時就隨身帶去了五十五本包括各種題材的書。(55)
至於葡萄牙,值得一提的是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的名字,他是16世紀下半葉一位傑出的著作家,他撰寫了描繪東方的第一部地理學巨著。儘管他的那部《東方概況》葡文作品在當時未能得以及時出版,但是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説,它是一部實用性很強的著作,是作者對亞洲的土地和人民進行的最新調查研究的成果,從而為人們提供了許多嶄新的知識。不過,托梅·皮雷斯在其作品的字裡行間隱約地流露出對自己的博學知識的炫耀,似乎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作品也沒有甚麼,他在引用中世紀那些描寫“海洋的神奇事物”的“概況或著述”時,常常帶着某種蔑視的口吻,其實人家那些作品祇是描寫在地中海沿岸進行的一些行程極短的旅行而已。(56)
杜瓦爾特·雷森德(Duarte de Resende)是另一個去過印度的文人,他確實隨身携帶了很多書去,而且有跡象表明,他的書庫以後還不斷得到補充。據我們所知,約在1525年,在他擔任馬魯古群島管理人的時候,曾收到一本《克拉里蒙多帝王編年史》,這是若昂·德·巴羅斯所著的一部騎士小説,該書由里斯本的熱爾芒·加里亞德印刷所於1522年出版(57)。雷森德在其工作之餘,還很可能從事翻譯西塞羅的作品,其譯著幾年以後由熱爾芒·加里亞德印刷所出版,書名為《馬爾科·圖利奧·西塞羅·德·阿米西尼亞:西皮昂的悖謬和夢想》(科英布拉,1531年)(58)。若昂·德·巴羅斯本人曾説過,雷森德“是位拉丁語學者,是研究海洋和地理的專家”,還説雷森德曾從馬魯古給他寄來過一些“作品和書籍”,這些東西是葡萄牙傑出航海家費爾南德·馬加良斯的助手、宇宙結構誌學者安德雷斯·德·聖馬丁的研究成果。當費爾南·德·馬加良斯的遠征船隊抵達馬魯古群島時,雷森德這位博學者正在那裡任職(59)。
16世紀居住在印度的葡萄牙學者中還有一位叫托梅·迪亞斯·卡亞多(Tomé Dias Caiado)。1542年,這位學者在果阿大敎堂敎授拉丁文。他在那個城市住了漫長的歲月。在1557年或1558年,他曾為國王若昂三世的逝世做了一次禱告彌撒,在禱告中他特別引用了普列尼奧和西塞羅的名言,從而表現了他的經典學識的淵博(60)。他曾用拉丁文為加西亞·德奧爾塔的名著《印度藥物對話》的果阿版本題詞,該書由若昂恩登印刷所於1563年出版。(61)
大約在1512-1563年間,長期居住在東方的科雷亞(Gaspar Correia)可能用手書和印刷材料開辦了一個很大的圖書館,而後他運用這些材料撰寫《印度神話》,書中廣泛地描寫了葡人在東方的業績,不過該書直到19世紀尚未出版。此外我們從科雷亞的作品中還可以隱約看到他閲讀過一部如今已失傳了的關於達·伽馬首次東方之旅的著述,那部書的作者是若昂·費格依拉;也可看到他閲讀過杜瓦爾特·巴爾博扎的作品,那是一本大量記述東方地理情況的書,不過同樣沒有在當時得以及時出版;還可看到他閲讀過《普列斯特若昂王國的真實報道》,該書是弗蘭西斯科·阿爾瓦雷斯神父所寫,由里斯本路易斯·羅德里格斯於1540年印刷出版(62);不過科雷亞讀的可能祇是手稿(63)。他還可能收到幾本由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達所著的《葡萄牙人發現及征服印度史》,該書於1551年開始由若昂·達·巴雷拉在科英布拉出版,直到三年後才出完,他也可能有若昂·巴羅斯所著《亞洲年代》的關於前二十年情況的兩部作品,這些作品是由里斯本的熱爾芒·加里亞德印刷所於1552-1553年間出版的。(64)
我們也瞭解到關於許多雖然不是文人,一般祇是在海外擔任行政公職的官員,但他們在工作之餘同樣相當熱心於文學事業的情況。(65)我們知道,在16世紀,這些人中的許多人在王宮里都曾受過初步的敎育和培養,都曾擁有一個適合發展自己的智力及興趣的良好環境。(66)馬丁·阿豐索·德·索薩(Martim Afonso de Sousa)便是這批人中的典型代表,他當時是位知名的貴族,曾在東方渡過漫長的歲月,甚至於1542-1545年間擔任過印度省總督。他雖然公務繁忙,但據加西亞·德·奧爾塔所證實,他總是在空餘時間大量閲讀史書。這位著名的植物學家甚至證實,馬丁·索薩最愛讀的一本書是著名的《敎皇史》,該書於1518年在威尼斯出版,作者為普拉蒂納,這個名字是意大利人文學家巴托洛梅烏·薩克希的別名(67)。
1543年從里斯本出發的一位船長叫瓦爾德斯(Baltasar Jorge de Valdez),他是一個很注重東方實際的人物,他當年擔任船隊一艘船的指揮官。根據後來一份文件可知,他當時隨身携帶了許多很珍貴的書,其中有數本《基督生活》、《使徒列傳》、無名氏作品《葡萄牙統帥努諾·阿爾瓦雷斯·佩雷拉編年史》,該書由里斯本的西芒·加利亞德於1526年印刷出版;還有一本關於羅德城被毀滅的著述,作者可能是雅科莫·豐塔諾;一本是由希德·坎皮亞多爾所撰寫的歷史(68);一本是由著名人文學者埃拉斯莫所評注的語法,可能是古列爾穆斯·利柳斯的作品《關於八種句型的部份結構》許多歐洲版本之一,於1534年在巴黎首次印刷出版(69),還有一本包括塞內卡、瓦雷里奧·馬克西莫和佩特拉卡等人的作品集。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傑出的文武雙全的人物,後來戰死在第二次包圍第烏城的戰鬥之中。(70)
兩年之後,即1545年,國王唐·若昂三世請當時正準備赴印度擔任總督的唐·若昂·德·卡斯特羅在其船上為佩羅·費爾南德斯·薩爾迪尼亞大師安排“適當的和單獨的”住宿,以方便他能“携帶他的書籍”(71)。國王的這一意見使那個將隨船去印度擔任果阿大敎堂敎長的、後來(從1552年開始)又成為巴西主敎的敎士也想將大批書籍(主要是宗敎書籍)裝船帶走。這位神父是個出色的拉丁語學者,後來的一件事實充份證明了這點:就在他到達印度不久,他主動向總督的兒子請求用拉丁文來記述關於第二次圍攻第烏城的情況。(72)
雖然如此,我們有沒有想過這位大師的書是否能超過唐·若昂·德·卡斯特羅(D. João de Castro)所有的書? 他是16世紀到印度的最傑出的葡萄牙貴族之一。如果説這位知名的總督對知識的濃厚興趣已為人們所知的話,那麼他究竟使用些甚麼著作的問題至今尚無人進行過系統的研究。(73)然而,我們祇要對卡斯特羅所經歷過的各條航線進行一次迅速的考察,就會發現他在某時某刻可能讀過的書目。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他在其漫長的海上旅行中撰寫了許多重要作品,那麼我們便不難想象他一定帶了大量參考書,更不難想象他總是同這些書籍進行着關於知識的對話。通過對卡斯特羅在1538-1541年間所經歷的三條航線的調查,我們有時十分清楚、有時若明若暗地發現他所使用過的各種經典著作主要有:普利尼奧的《自然史》,龐波尼奧·梅拉的《世界地名志》,托勒密的《地理志》,以及馬爾科·維魯維奧的《建築學》。前三本著作可以説始終伴隨着卡斯特羅的寫作,他一路上總是把實際觀察到的地理狀況同傳統的權威著述進行核對。在近代出版的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當時肯定使用過佩德羅·努內斯的《地球概説》的痕迹;那本書剛剛問世,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它是1537年12月出版的,也還可以發現他參考過上述作品《普列斯特若昂王國真實報道》的蛛絲馬跡。(74)
為了滿足具有文化知識的大眾之需要,果阿當時便開辦了一間書店。儘管這間書店開業的準備時間不詳,但在1568年該市出版的一部作品中提到該書店名叫“費爾南·達·卡斯蒂略之家”,它位於一家肉店對面。(75)在這個書店裡確實可買到若昂·德·恩登所編輯出版的書:《印度藥物對話》(果阿,1563年),這是由歐洲人在16世紀撰寫的而在印度印刷出版的數量極少的幾部非宗敎題材的著作之一。在加西亞·德·奧爾塔的這部植物學著作中處處反映了果阿的文化生活,大篇幅地講到當時在東方的葡萄牙學者之間所進行的學術爭論。該作品從頭到尾都反應出文化的世界性,比如:奧爾塔為馬丁·阿豐索·德·索薩題詞,後者是當時到東方去的最有學問的貴族之一,當時住在果阿的路易斯·賈梅士在那裡首次出版了他獻給印度總督雷東多伯爵的詩歌之一;瓦倫西亞物理學家蒂馬斯·博斯克撰寫了頌揚《印度藥物對話》作者的充滿深情的文章(76),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過的托馬斯·迪亞斯·卡亞多也書寫了獻給“印度人民的醫生加爾蒂昂·阿博奧爾托”的銘文。(77)
加西亞·德·奧爾塔有一個圖書館名叫“理想圖書館”,是費卡略伯爵幫助建立的。(78)儘管如此,在這裡也許仍有必要對其附帶做些説明。他這個圖書館,從一開始就擁有他在上述《對話》一書中所引用過的所有作品。作為當時的一個文化人,他很喜歡收集各種權威性的著作,他這樣做既是為了保障他自己在著述時的查閲和引用,也是為了能更好地開展對傳統知識局限性的評論。對於這後一個目的早已眾所週知,人們總是頻繁地引用他的以下名言:“我認為如今葡萄牙人一天知道的東西要比過去羅馬人在一百年中所知道的還要多。”(79)
奧爾塔收集的作品,其中一部份可能是二手貨,也就是説,可能是抄本的抄本;另一部份則可能是屬於參考性的作品,這些作品可能與他在薩拉曼卡學習的年代裡所讀過的書有關。在這部份藏書中無疑包括特奧弗拉斯托、馬塞盧斯·恩皮里庫斯、梅蘇埃·塞尼奧爾、赫爾莫勞斯巴·爾巴魯斯等人的著作。(80)他的藏書中還有一些可能是當時同他一起住在果阿的老鄉們的,比如聖·阿戈斯蒂尼奧的作品、安東尼奧·德·萊貝里雅的《拉丁語西班牙語詞典》、喬瓦尼·皮科·德·米蘭多拉的《辯護》(該書在果阿的一般的書店裡可能也有)以及普拉蒂納的《敎皇史》(這本書是他朋友馬丁·阿豐索·德·索薩的)便是屬於這種情況。(81)
然而,從上述《對話》一書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跡象似乎表明,這位經驗豐富的植物學家有一個相當大的圖書館,其中不僅有關於世界大自然知識的專業作品,而且還有關於普通知識的書籍。在其植物學著作的旁注中,許多地方標明了其引語的確切出處,涉及普利尼奧、迪奧斯科里德斯、阿維塞納、蓋倫、塞拉皮奧和馬特烏斯·西爾瓦迪庫斯等作者的作品;這一事實證明了這位植物學家同經典醫學著作的密切關係,説明他可能有所有這些權威的、在歐洲多次印刷出版的外文版本。
《對話》這本書展示了作者極其淵博的知識。在其著作中他還引用了許多他同鄉作家的作品,這表明在其私人圖書館中可能有他們的那些作品,其中較為突出的有:盧多維科德·瓦特馬的《旅行路線志》,該書可能是1520年的塞維利亞文版;貢扎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埃多的《印度自然及一般情況簡史》,該書於1526年在托雷多首次印刷出版;以及加斯帕爾·巴雷羅斯的《某些地區的地理志》,該書僅在奧爾塔本人的上述著作出版前兩年由若昂·阿爾瓦雷斯在科英布拉出版。(82)
加斯帕爾·德·萊昂(Gaspar de Leão)是16世紀後半葉住在印度的另一個知名文人。他在埃武拉及薩拉曼卡經過長期的學習後,獲得了神學家的殊榮,於1540年被委任為埃武拉的大主敎。二十年後他赴東方去擔任果阿的首席大主敎,儘管這一職務之官階僅在敎皇之下,但從表面上看他是違心地接受這一任命的,因為在這之前他崇尚一種孤獨與沉思的生活,不大喜歡東方的“煙霧”。(83)1560年這位大主敎登上了駛向東方的船隊,在他的倡議下,有一批印刷專家及印刷工人與他同行,這批人是去印度國的首都創建第二個印刷所的,這一事實説明那個城市的文化需求當時正在增加。(84)
果阿的首任大主敎進行了大量緊張而繁忙的宗敎活動,並撰寫了各種宗敎理論著作。在1561年他剛離開印度回國不久,便發表了他的《基督精神生活要略》一書,該書是由當時剛剛在那裡創辦起來的若昂·德·金肯西奧及若昂·德·恩登印刷所出版的。(85)這是一本關於宗敎敎義及進行禱告的指南,其中也講述了耶穌基督的生活故事。四年以後,當歐洲宗敎裁判所涉及東方的土地後,這位主敎的《首任主敎致以色列人民的信》由恩登在1565年出版《聖耶羅米敎團大師作品集》時作為該書序言予以發表。(86)最後於1573年,恩登印刷所又出版了這位大主敎的代表作《迷途者的醒悟》,那是一本反對伊斯蘭敎的鉅著。(87)

肉桂樹
引自葡國醫生克里斯托旺·達·高士達《論東方印度之醫藥》(1578年,Burgos出版)
祇要對該著作稍加分析就會立刻發現在它的字裡行間反映出存在着一個龐雜的書籍網絡在支撐着加斯帕爾·德·萊昂撰寫散文作品。由此人們不能不懷疑作者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圖書館,否則他是無法在果阿寫成這本著作的。事實上,這位大主敎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已經弄清了一部份(88),從已知的情況來看,他手邊有各種各樣的宗敎資料供自己參考。僅根據《醒悟》一書就可斷定他可能有以下各種作品:《歐塞比奧初探》,這是阿隆索德·馬德里加爾所寫的對歐塞比奧所著的《敎會史》一書的評論鉅著,於16世紀初在薩拉曼卡出版,由恩里庫斯·德·赫爾普夫修士所著的上述作品《完美的鏡子》(科英布拉,1533年),由約翰·陶雷爾所著的《是敎規還是敎理》(科英布拉,1533年,可能是由若昂·達·巴雷拉及若昂·阿爾瓦雷斯印刷所出版的);由佩雷斯·德·辛充所著的《行動起來反對古蘭經》,該書的瓦倫西亞文版是於1532年出版的,以及胡安·德·維格拉斯所著的《大自然和基督敎哲學原理》,該書1550年在巴黎出版。
也很可能加斯帕爾並沒有上述著作所直接或間接涉及的著作,因為其中許多書在果阿的各個敎會組織的圖書館裡都可能有。不過,他的主要作品證明在印度首都有許多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其中至少是關於宗敎思想和敎義的書很多,這些書當時在具有文化水平的和對書籍有濃厚興趣的人中不斷地傳閲着和討論着。
最後,在16世紀到過東方地區的文人中還有一位名叫冉·海金·范·林斯卻藤,他於1583-1588年間在果阿擔任唐·維森特·達·豐塞卡大主敎的私人文書。這位荷蘭人在印度期間,通過同從事海上事業的葡人的日常接觸,精心地收集了關於亞洲的包括地理學和水文學、植物學和動物學、政治和文化、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以及商業貿易和航行等方面的大量信息。1592年他回荷蘭後,便開始從事系統地整理他以前有機會零星撰寫的所有資料,僅在幾年之內就寫出了一系列著作,並且很快得以在其祖國出版。其時荷蘭在探索印度洋和亞洲沿海某些地區方面剛剛起步。1596年,他的《旅行路線志》(書名原文為“Voyage ofte Schipvaert van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naer Oost ofte Portugals Indien”)第一版在阿姆斯特丹問世。這部獲得巨大成功的作品詳細地描寫了亞洲從曼德海峽到日本群島之間的整個海岸線的情況,書中滙集了到當時祇有葡人知道的大量激動人心的信息。(89)
在《旅行路線志》這部著作中,我們除了能瞭解作者在東方的生活情況外,還能發現他在果阿居住期間所獲得的和查閲過的以及所抄過的一批重要的葡文著作。他除做好大主敎的文書工作之外,便利用其一切空餘時間持之以恒地匯集整理葡萄牙人在16世紀所獲得的並在該世紀下半葉由葡國印刷所出版的所有關於地理和人類的材料。
經過對這位荷蘭人所著的《旅行路線志》的初步調查研究,我們發現作者參閲過各種葡萄牙語著作,其中主要有:費爾南·洛佩斯的《歷史》,這套一共八卷的鉅著是由上述科英布拉的若昂·達·巴雷拉及若昂·阿爾瓦雷斯印刷所於1551-1554年間印刷出版的,若昂·德·巴羅斯的《亞洲年代》,其中關於前三十年的作品是由里斯本的熱爾芒·加利亞德印刷所在1552-1563年間出版的,加西亞·德·奧爾塔的《對話》(果阿,1563年);在1572年由里斯本的安東尼奧·貢薩爾維斯出版的賈梅士的《葡國魂》(90),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達·科斯塔所著的《東方印度藥物志》(91),該書由布爾戈斯的馬丁·德·維托里亞於1578年印刷出版,以及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的《中國概況》,該書於1569-1570年間由埃武拉節安德雷·德·布爾戈斯印刷所出版。(92)很可能上述著作中許多都藏於大主敎的私人圖書館裡,那位荷蘭人,作為他的勤奮的文書,當然可以隨便動用它們。
從以上簡要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初步斷定:書籍總是伴隨葡人在海外的歷程。他們駛向印度的商船以及從各個方向橫渡東方海洋的船隻總是帶着各種各樣的書籍和其它書面材料,每當他們在亞洲的沿海地帶征服一個城市或建造一個城堡後,總是立即着手創辦具不同程度重要性的公共或私人圖書館。在其藏書中佔首位的是關於宗敎方面的和敎學方面的書籍,其目的是為了在其中創造一個宗敎利益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和文化環境。但其中也藏有實用性書籍和科學技術書籍,以滿足認識、瞭解、佔領和管理一個充滿地理、自然和人類新鮮事物之新世界的需要。藏書中也還有供讀者消遣的書籍和講述社交活動之各種必不可少方式的書籍。總之所藏書籍可能是難以計數的。
在東方的各個地區都有酷愛讀書的讀者,他們屬於各個社會階層,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宗敎人士和傳敎士,由於他們具有相應的文化水平,所以是其中最勤奮的諸者。但是,許多船長、管理人員或藥劑師無論在堅持緊張地閲讀書籍方面或是在持之以恒地撰寫作品方面同他們比起來也都毫不遜色;如果要在這方面做個統計,看來會是令人鼓舞的。此外,根據讀者登記的閲讀書目來看,他們讀書的種類是很多很多的,實際上涉及知識的方方面面,這證明讀者大眾的興趣是十分廣泛的。
葡人在東方建立的印刷所幾乎祇印刷精神產品,唯一的例外是印刷了加西亞·德·奧爾塔的《對話》(93)。由於這些印刷所都是宗敎人士、主要是耶穌會的神父們倡議建立的,所以它們也許不能無視敎士們主要出於維護傳敎利益而採取的出版政策。不過,雖然在東方的印刷所不印刷其它題材的作品,但是由於不斷地從葡萄牙運來那些題材的書籍而使這一缺陷得到了彌補。而且,書籍從葡萄牙運來的速度相當快。為説明這一點,人們常常舉加斯帕爾·巴雷羅斯的《區域地理學》一書為例。該書於1561年在科英布拉出版,但第二年這本書在果阿就有了,而且在1563年4月印刷出版的加西亞·德·奧爾塔所撰寫的上述植物學著作中就出現了來自那本書的引語,雖然印刷所老闆的助手由於缺乏經驗在印奧爾塔的著作時還拖了好幾個月。(94)再説書籍的交流也是相互的,比如在1561年1月,加斯帕爾·德·萊昂就給國王唐·塞巴斯蒂昂寄去了一本他自己撰寫的、剛剛由若昂·恩登印刷所出版的作品:《基督精神生活要略》(果阿,1561年)。(95)
除了從歐洲進口書籍外,在東方定居的或暫時停留的葡人還不斷用於人類各個領域之知識的作品來作為自己的精神食糧。一方面他們在海外定居點按照傳統繼續閲讀詩歌、戲劇及宗敎書籍,另一方面他們廣泛接觸當地的風土人情和新的人群,接觸從未經歷過的生活方式,從而使他們獲得了撰寫包括散文、故事、旅行路線指南、信件及通訊報道等各種題材的素材,並進而實現其恰如其份地描繪“世界上這些新的地區”的目的。(96)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中國概説》一書封面
(埃武拉,1570年)
有兩個典型例子可證明葡人儘管終年奔波在東方的海洋和陸地上,但書籍從未離開過他們的手,可以説書籍真正成了這些漂泊者的忠實伴侶。第一個例子:1519年安東尼奧·科雷亞視察勃古,身兼貿易和外交雙重任務,經過努力,最後得以同當地首領簽署了一個友好和合作條約。而當對方要求他把手放在葡人的聖書上對和平進行發誓時,他立刻拿出他隨身帶來的一本很大很大的“印刷出版的詩歌集”來使用,因為在他看來“再沒有別的甚麼書能夠像這本用整張紙印刷的書更能顯示出儀式的盛況和威嚴”。(97)這本《詩歌全集》是加西亞·德·雷森德編撰的一本不朽著作,是由里斯本的赫爾芒·德·坎波斯印刷所出版的。(98)
第二個例子是:在1578年底,有一個住在孟加拉王國的名叫吉爾·埃亞內斯·佩雷拉的人,他準備乘一艘葡萄牙船隻去印度西海岸。但在出發之前,他被總督叫到離城十多公里的他的一位親屬的別墅去“欣賞一些書籍”。吉爾·埃亞內斯接受了總督的邀請,出發時也隨身携帶了一本“跟彌撤書一樣大小的《基督生活》”去,“書中附有耶穌從降生到復活昇天的所有精美插圖”,這顯然表明,這位孟加拉貴族很欣賞這本書。(99)
以上就是本人對16世紀葡人在東方歷史的一個側面的初探。文獻資料儘管很零散,但都一致表明:葡人在海外日常生活中都很重視讀書,他們都把書當作是自己最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文化工具,即便那些在偏僻的和陌生的地區奔波工作的人們也是這樣的。如果要想對這個題目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無疑應當對我們那些在16世紀去過東方的作家作品進行更加認真細緻的調查研究,祇有這樣,才能弄清他們閲讀些甚麼,才能弄清當時在那些地方開設的圖書館可能有哪些藏書。
【參考書目】
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歷史研究》,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大學文書檔案,1972-1978,卷6。
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16世紀葡萄牙印刷出版物書目》,里斯本,國家圖館,1926。
歐熱尼奧·阿森希奧:《若昂·德·卡斯特羅收集整理的阿拉伯故事》,見《第三屆葡萄牙巴西作品國際研討會文獻集》,里斯本,1959-1960,卷1,頁395-413。
若昂·奧賓:《馬努埃爾派駐普列斯特若昂的使團》,“Mare Luso-Indicum”,巴黎,(3)1976,頁1-56。
若昂·德·巴羅斯:《亞洲:三十年代》,第一版復製品(里斯本,1563年),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造幣廠,1992年。
若昂·德·巴羅斯:《羅皮卡·普內夫馬》,I. S瓦荷出版社,里斯本,國家科學研究學會,1982年,卷2。
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若昂·德·巴羅斯:葡萄牙亞洲人文主義者及歷史學家》,新德里,Concept出版公司,1981年。
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印度葡文印刷品初步清單》,“葡萄牙文化中心檔案”,巴黎,(9)1975年,頁567-599。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達:《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馬努埃爾·洛佩斯·德·阿爾梅達編輯,波爾圖,Lello e Irmão出版社。1979年,卷2。
加斯帕爾·科雷亞:《印度神話》,馬努埃爾·洛佩斯·德·阿爾梅達編撰,波爾圖,Lello e Irmão出版社,1975年,卷4。
阿爾曼多·科爾特讓:《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況》及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作品》,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大學文書檔案,1978年。
阿爾曼多·科爾特讓和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合編:《若昂·德·卡斯特羅作品全集》,科英布拉,葡萄牙文化國際學會,1968-1981,卷4。
克里斯托旺·達·科斯塔:《東印度藥物志》,扎依梅·瓦爾特編輯,里斯本,海外研究學會,1964年。
達亞·德·希爾瓦:《葡萄牙人在亞洲:已加注釋的書目》,楚格(瑞士),I. D. C. ,1987年。
若澤·塞巴斯蒂昂·達·希爾瓦·迪亞斯:《若昂三世執政時期的文人政策》,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大學,1969年,卷2。
孔德·德·費卡利奧:《加西亞及其所處的時代》,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造幣廠,1983年。
里卡多·加西亞·卡爾塞爾:《黃金時代的文化》,馬德里,歷史16,1989年。
達維德·胡克:《國王曼努埃爾一世1515年寄至普列斯特若昂的書籍》,“Studia”出版社,里斯本,(37)1973年,頁303-315。
加斯巴爾·德·萊昂:《迷途者的醒悟》,歐熱尼奧·阿森希奧出版社,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大學文書檔案,1958年。
伊文A. 萊昂納德:《征服者作品集》,墨西哥,經濟文化基金會,1979年。
冉·海金·范·林斯卻藤:《約翰·海金·范·林斯卻藤東印度之行》,Artur Coke Burnell e P. A. Tiele出版,新德里,亞洲教育服務中心,1988年,卷2。
若澤·維托里諾·德·皮納·馬丁斯:《埃拉斯莫時代的葡萄牙》,巴黎,文化中心,古本江基金會,1977年。
路易斯·德·馬托斯:《16世紀東方的面貌:手抄古蹟,1889年》,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造幣廠,1985年。
路易斯·德·馬托斯:《(15,16世紀)印度航道上的書籍和印刷工具》,里斯本,Távola Redonda出版社,1990年。
若澤·德·瓦斯康塞洛斯·依·梅內熱斯:《葡萄牙船隊:大發現時代的衛生設施》,里斯本,航海學會,1987年。
《“基督生活”五百週年:在葡萄牙的首批德國人》,若昂·若澤·阿爾維斯·迪亞斯統籌,里斯本,國家圖書館,1995年。
加西亞·德·奧爾塔:《印度藥物對話》,第一版(果阿,1563年)複製品,里斯本,里斯本科學院,1963年。
加博里埃爾·佩雷拉:《第烏海關法官的巴爾塔扎爾·若熱在1546年的財產》,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刊、4(6)1983年,頁287-292。
保羅·埃米利奧·佩雷斯·馬利亞納:《大海中的人們:(16世紀)印度船隊船員的日常生活》,塞維利亞,1992年展覽會,省議會,1992年。
若昂·羅沙·平托:《有15、16世紀的航海日記嗎? 》,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編撰的《第六屆國際航海及水文地理會議文獻集》,里斯本,紀念葡萄牙大發現全國委員會,1989年,頁383-416。
卡門·拉杜雷特:《瓦斯科·達·伽馬:首次環非洲航行,1497-1499》,雷焦·艾米利亞,迪亞西巴斯,1994。
基奧瓦尼·巴蒂斯塔·拉姆西奧:《航行與旅行》,Marica Milanesi出版社,都靈,埃腦迪,1978-1988,卷6。
路易斯·德·索薩·雷貝洛:《葡萄牙文學的古老傳統》,里斯本,地平線書籍出版社,1982年。
安東尼奧·達·希爾瓦·雷戈:《葡萄牙與非洲及東方歷史研究》,里斯本,葡萄牙歷史學會,1994年。
安東尼奧·達·希爾瓦·雷戈編撰的《葡萄牙東方傳敎史文獻集:印度》,里斯本,海外總社,1947-1958,卷12。
杜瓦爾特·德·雷森德:《友好條約,西皮昂的悖謬及夢想》,瑪麗亞·雷奧諾爾·卡瓦利昂·布埃斯庫出版社,1982年。
A. J. R. 拉塞爾-武德:《生活在壓力下的人們:“印度航道”的社會環境,1550-1750》,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和依納西奧·格雷羅合編的《第二屆印度葡萄牙歷史國際研討會文獻集》,里斯本,熱帶科學研究所,1985年,頁19-35。
阿圖爾·莫雷拉·德·薩編輯的《16世紀葡萄牙禁書書目》,里斯本,國家科學研究所,1983年。
喬治·舒哈梅爾:《東方風情》,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所,1963年。
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16世紀葡萄牙印刷出版物清單:國家圖書館集》,里斯本,國家圖書館,1990年。
桑傑·蘇布拉馬延:《葡萄牙亞洲帝國,1500-1700:政治及經濟史》,里斯本,迪費爾出版社,1995年。
約瑟夫·維基編輯的《關於印度的文獻》,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所,1948-1988,卷18。
黃徽現譯
【註】
(1)關於這個問題的最新綜述請參閲桑傑·蘇布拉馬延的《葡萄牙亞洲帝國,1500-1700:政治及經濟史》,書中多處講到這一問題,此外,該書為讀者提供了大量的地理知識。
(2)參閲A. J. R. 拉塞爾·武德的作品:《在壓力下生活的人們:印度航線的社會環境,1550-1750》,頁19-35。
(3)加斯帕爾·科雷亞:《印度神話》,卷1,頁1。關於阿爾瓦羅·維利奧描寫瓦斯科·達·伽馬的首次航行問題,請參閲卡門·拉杜雷特的作品《瓦斯科·達·伽馬:首次環非洲航行,1497-1499》,頁31-57。
(4)關於這類作品請參閲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的《歷史研究》卷5,頁135-142,另請參閲若昂·羅薩·平托的作品:《有15、16世紀時期節航海日記嗎? 》,頁383-416。
(5)參閲若澤·德·瓦斯康塞洛斯·依·梅內澤斯的作品《葡萄牙船隊:大發現時伐的衛生設施》,頁113等。
(6)參閲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葡萄牙與非洲及東方的歷史研究》中的一些觀點,頁79-81。
(7)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16世紀葡萄牙印刷廠商清單:國家圖書館集》,頁241。
(8)喬治·舒爾哈梅:《東方風情》,頁317-327。
(9)費爾南·洛佩斯·卡斯塔涅達:《葡萄牙人發現及征服印度史》,卷1,頁689,另請參閲上述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編輯的作品《葡萄牙東方傳敎史文獻集:印度》卷1,頁222-223。
(10)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上揭書,卷1,頁338。
(11)同上,頁419。
(12)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16世紀葡萄牙印刷出版物書目》,頁1 19-120。
(13)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上揭書,頁419-420。
(14)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146。
(15)請參閲《“基督生活”的五百週年:在葡萄牙的首批德國人》,頁32,。關於這個問題,另請參閲達維德·胡克的作品《關於國王馬努埃爾在1515年寄至普列斯特若昂之書籍的説明》,其中多處講到這個問題,關於使團問題,請參閲胡安·奧賓的作品《唐·馬努埃爾派駐普列斯特若昂去的使團》,該書多次提到這個問題。
(16)加斯帕爾·科雷亞:上揭書,卷2,頁464-465。
(17)基奧瓦尼·巴蒂斯塔·拉姆西奧:《航行與旅行》,卷1,頁1 1。
(18)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上揭書卷1,頁336-337。
(19)參閲《“基督生活”的五百週年》,頁45-57。
(20)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68。
(21)(22)(23)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編撰的上揭書卷1,頁411;卷25,頁328;卷4頁206。
(24)參閲若澤·塞巴斯蒂昂·達·席爾瓦·迪亞斯的作品:《唐·若昂三世執政時期的文人政策》,其中多處提到這點。
(25)路易斯·德·馬托斯編輯的《16世紀時的東方面貌:手抄古蹟,1899》,頁33-34。
(26)參閲喬治·舒爾哈梅:《弗蘭西斯科·沙維爾:他的生活及其所處時代》,卷3,頁317-336。
(27)安東尼奧·達·席爾瓦·雷戈上揭書卷3,頁24-25。
(28)(29)(30)(31)(32)(33)(34)(35)(36)約瑟夫·維基編輯的《關於印度的文獻》,卷1,頁35;頁36;頁88;頁136;頁89;卷2,頁84;卷1,頁335;頁340-341;卷3,頁201-205。
(37)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66。
(38)已查閲的目錄僅提到1579年的里斯本版本(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140-141)。之前或有一個版本就像這裡認為的那樣? 這裡所指的很大可能是拉丁文版本。
(39)(40)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175;頁179。
(41)(42)(43)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127;頁129;頁66。
(44)參閲加斯帕爾·德·萊昂:《迷途者的醒悟》,頁38-39。
(45)(46)(47)(48)約瑟夫·維基上揭書卷4,頁614;卷5,頁531;卷6,頁295;頁772。
(49)參閲阿圖爾·莫雷拉·德·薩編:《16世紀葡萄牙禁書書目》,其中多處提到這點。
(50)約瑟夫·維基卷6,頁308。
(51)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299、302和181。
(52)保羅·埃米利奧·佩雷斯·馬利亞納:《大海中的人們:(1 6世紀)印度船隊船員們的日常生活》,頁162-167。
(53)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閲里卡多·加西亞·卡爾塞爾的《黄金時代的文化》,頁113等。
(54)參閲約瑟夫·維基上揭書卷11,頁350。
(55)伊文A·雷奧納多:《征服者作品集》,頁218-230。
(56)阿爾曼多·科爾特讓:《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況》及弗蘭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作品》,頁131。
(57)若昂·德·巴羅斯:《羅皮卡·普內夫馬》,卷2,頁3-5,另請參閲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若昂·德·巴羅斯:葡萄牙亞洲人文主義者及歷史學家》,頁146。
(58)杜瓦爾特·德·雷森德:《友好條約:西皮昂之悖謬和夢想》,該書中多處提到這個問題。
(59)若昂·德·巴羅斯:《亞洲:三十年代》,第十章。
(60)路易斯·德·馬托斯:上揭書頁37,注釋9。
(61)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151。
(62)同上,同296-297。
(63)加斯帕爾·科雷亞:上揭書卷1,頁1和134;卷2,頁833。
(64)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88-90,60-61。
(65)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閲路易斯·德·索薩·雷貝洛:《葡萄牙文學的古老傳統》,頁195-240;在這部份中作者探討了“文與武”的問題。
(66)若澤·塞巴斯蒂昂·達·希爾瓦·迪亞斯上揭書頁727。
(67)加西亞·德·奧爾塔:《印度藥物對話》,頁7背面。關於馬丁·阿豐索,請參閲孔德·德·費卡利奧的作品《加西亞·德·奧爾塔及其所處的時代》,頁65等。
(68)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1 16。
(69)若澤·維托里諾·德皮納·馬丁斯:《埃拉斯莫時代的葡萄牙》,頁93-94。
(70)加博里埃爾·佩雷拉:《第烏海關法官巴爾塔扎爾·若熱在1546年的財產》,頁287-292。
(71)阿爾曼多·科爾特讓和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合編上揭書:《唐·若昂·德·卡斯特羅作品全集》,卷3,頁53。
(72)喬治·舒哈梅爾:《東方風情》,頁150。
(73)參閲歐熱尼奧·阿森希奧:《若昂·德·卡斯特羅收集整理的阿拉伯故事》,頁395-413;另請參閲阿爾曼多·科爾等讓和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合編的《若昂·德·卡斯特羅作品全集》的注釋,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74)參閲阿爾曼多·科爾特讓和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合編的上揭書卷1和卷2,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75)請參閲《1567年在果阿舉行的第一次省代表會議》(果阿,若昂·德·恩登,1568年)的封面,以及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的《印度葡萄牙印刷出版物清單》,頁576。
(76)加西亞·德·費卡利奧的上揭書,沒有確定的頁數。
(77)同上,第228頁背面。
(78)孔德·德·費卡利奧:上揭書頁284-300。
(79)加西亞·德·奧爾塔:上揭書頁60。
(80)孔德·德·費卡利奧:上揭書頁288-291。
(81)在加西亞·德·奧爾塔的上述作品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82)同上。
(83)安東尼奧·達·希爾瓦·雷戈上揭書卷8,頁18。
(84)馬努埃爾·卡達法斯·馬托斯:《(15和16世紀)印度航道上的書籍和印刷工具》,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85)(86)安東尼奧·若阿金·安塞爾莫上揭書頁152;頁151。
(87)(88)唐·加斯帕爾·德·萊昂上揭書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頁66-103。
(89)冉·海金·范·林斯卻藤:《約翰·海金·范·林斯卻藤的東印度之行》,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90)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77。
(91)克里斯托旺·達·科斯塔:《東印度藥物志》,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92)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116。
(93)請參閲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印度葡萄牙印刷出版物初步清單》,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94)加西亞·德·奧爾塔上揭書頁229。
(95)約塞夫·維基上揭書卷5,頁231。
(96)達亞·德·西爾瓦:《葡萄牙人在亞洲:已加注釋的書目》,其中多處提到該問題。
(97)若昂·德·巴羅斯:《亞洲:三十年代》,第三編,第四章,頁67。
(98)瑪麗亞·阿爾濟拉·普羅恩薩·西蒙斯上揭書頁80。
(99)請參閲約塞夫·維基上揭書卷11,頁424。
*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文學院歷史學博士,葡萄牙Lusófona大學阿爾加維分校校長,澳門大學訪問敎授,敎育部紀念葡萄牙大發現工作組成員,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航海學會會員,澳門文化司署研究調查暨刊物處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