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將從事某項調研工作的最初動機重新展現不是一件易事,特別是若要將最初動機同其最終調研成果進行有聯繫的對比則更難了。
一開始,任何計劃似乎都難以實現。疑難問題趨向於用完美的方程式來解決,這就使得往往難以實現的調研計劃的制定被認為是必須的。但是,只是在調研的過程中,制定的計劃才逐漸變得盡可能完美。
在這一點上,對調研工作最初目的作出某種方式的更改並不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我們首先對16-18世紀的暹邏與澳門的主要社會及文明狀況做一概述。然後,我們將集中論述一下葡萄牙和澳門同暹邏的關係,特別是17-18世紀相互間的往來,這種關係是不能相互分割的。
一、歷史的回顧
1. 暹邏
1.1-概述
亞洲東南部地區,又稱東南亞,這一稱呼一般用來表示位於西起印度,東至中國這一區域內的國家。這一區域內最重要的河流有:
伊拉瓦底河(Irawadi,又稱緬甸心臟);
湄南昭帕耶河(Menam Chao Phya,流經暹邏中央地帶,簡稱湄南河);
湄公河(Mekong,流經柬埔寨和寮國);
湄公河(流經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
紅河(流經越南北方的Tonquim地區)。

那些經於巨大河谷(即上述河流的盤地)之間的地區一般是佈滿森林的高山地區。因此,居民從一個河谷向另一個河谷遷移,並不像他們沿河谷遷居那麼輕而易舉。除此之外,河谷地區比高山地區土地肥沃,從而導致居民一直向南遷移,因此經常造成勞動力的短缺。另一方面,直至上一個世紀,東南亞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缺少人口,或者説人口密度稀疏。而且,這一問題也是導致印度支那各國之問連綿不斷的戰爭之主要原動力(例如:暹邏族人同吉蔑族人,即高棉人之問的戰爭),因為,15世紀時,整個東南亞僅有一仟五百萬居民。
正因為如此,為了彌補勞動力的短缺,相互鄰近的王國之間經常爆發戰爭,擄取俘虜(即勞動力)。農業城市不僅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且也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些農業城市是以佛教的宇宙論為基礎,從微觀論出發,按平面幾何的理論將宮殿建築在城中央,在那裡,君主是世界的軸心(必須保證絕對的權力同人之間的和諧)。君主由一群官吏輔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組織農業勞動和負責税收;還有一群佛教長老或印度教首領為其服務,他們的待遇非常豐厚;作為交換,他們使君主的精神權力法律化,並為君主所提倡注重農業的舉措付出努力。
在暹邏王國內,同在這一地區其他的王國一樣,政治權力是由不同的王室家族分別執掌,每一個家族都控制著這一地區的一個戰略中心地帶,在那裡強者總是試圖將弱者置於某統治之下,並往往名正言順地通過禮儀、婚姻和其他人際間的聯繫來實行其統治。(2)
1.2居民的起源
從史前時期,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之間,便有被稱之為澳奈希奧人種(Austranésio)的後裔開始向南部遷移,他們是現代馬來西亞和整個東南亞地區居民的基礎,特別是印度支那半島和中國南部地區其他居民的同一祖先。
從中國西南部有兩支移民隊伍遷居到東南亞:一為前馬來人(Proto-Malaios),二為後馬來人(Deutero-Malaios),他們帶來了冶金術。
越南人從中國西部地區來到紅河三角洲;高棉族人從同一地區來到湄公河谷及其三角洲;孟族人(近似高棉族人)來到湄南河;在伊拉瓦底河谷出現了被稱之為弗亞(Phya)族的人群。
後來,緬甸人從北方來到了伊拉瓦底河谷。泰族人,即現在泰國的居民,老撾人和撣族人的祖先,隨後也從雲南遷居到這裡。(3)
1.3有關史前史資料
在曼谷以西的干乍納武里府(Kanchanaburi)北部清萊地區所進行的考古,發現了距今有五十萬年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在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散居在整個暹邏。
但是,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是在現在泰國的東北部地區,距曼谷五百公里的呵拉特(Khorat)高原,被稱為萬昌(Ban Chiang)地區進行的。這次考古證明原始的農民社團大約是在公元前四千年開始定居於這一地區。萬昌的傳統文化是由一個非常發達的農民社團創造的,這就使得這一地區有可能早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幾百年而製造出青銅器具,還將青銅與鐵混合在一起,用於製作器皿和裝飾品。
萬昌地區居民起源於何處,曾有許多不同的説法。一些學者認為他們來自越南的北方,另一些人則認為,根據在萬昌地區所進行的考古挖掘(發現了公元前二千年新石器文化,青銅器產生的時代),他們可能是前馬來部族人。(4)
1.4歷史主要分期
正如上所述,泰族人可能來自於中國的西南部,因為那裡的人口眾多,特別是在今天的雲南省境內。12世紀那裡建立了南詔王國(Nanchao)。其他種族的人仍繼續向南部遷移,以較小的群體進入寮國、暹邏的北部地區和緬甸(Burma)的撣高原(Shan),同當地居民混合在一起。
1253年,蒙古人征服了南詔國,並使其變成了中國最南方的一個省份,即雲南省。於是,泰族人被逼越來越向南方遷移,以逃避中國人的控制。(5)
根據學者們普遍的看法,暹邏的歷史可以分為四個時期:1)德哇拉哇弟(Dvaravati)時期(7-11世紀);2)素可泰(Sukhothai)時期(13-14世紀);3)阿育他亞(Ayuthia)時期(14-18世紀);4)曼谷時期(18世紀至今)。
1)德哇拉哇弟時期(Dvaravati)
這一時期的中心是納空巴統(Nakhon Pathon),一直延續到11、12世紀。這是藝術蓬勃發展的時期,產生了許多(明顯受印度影響的)佛教偶像、(寺廟和洞窟的)石膏浮雕,建築藝術(例如用磚建造的巨大宮殿)、陶製的(釋迦牟尼和其他神的)頭像、還願的佛教石碑和其他雕像(表現釋迦牟尼、各類神、侏儒、魔鬼、牲畜和其他題材)。在這一地區發現了一些古老的印度教偶像,代表著後古波塔(PósGupta)印度風格的雕塑,是印度南部帕拉哇王朝(Pallava)的傑作(約在7世紀)。這些印度雕塑一般所表現的都是維斯努(Vishnu)。(6)
關於德哇拉哇弟居民起源眾説紛紜。一些人認為他們是孟族人(Mon)或孟-高棉族人(MonKhmer),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本身是孟族人,是來自(位於印度東海岸奧里薩邦和安德拉·布拉德什邦邊界地區的)卡林加(Kalinga)一群印度移民的後代。
這樣看來,德哇拉哇弟的孟族人似乎是這一支外來移民同本地區土著居民相混交的一個人種,這一結論使我們可以認為泰族人是這一地區的原始居民。
德哇拉哇弟文化在11世紀隨著高棉族入侵者的政治統治而迅速衰落,高棉族人在華富里(Lopburi)定居下來。於是,贏得勝利的高棉人使得他們的文化影響滲透到當地的藝術,語言和宗教領域。孟泰語彙中某些源於梵語的詞彙甚至進入了11-12世紀高棉時期(7)(又稱華富里時代)的大眾語言中。
2)素可泰時期(Sukhothai)
1238年,出現了被認為是最早的真正泰王國,即素可泰王朝,並一直延續到1376年,而後被阿育他亞王國所吞並。
素可泰王朝的君主蘭甘杏國王(Rama khameng,1283年一1317年,將其王國的疆界擴展到湄南河盆地,把佔領那裡的高棉族人驅逐而去。並將其勢力擴大到南方的納空時探瑪叻(Nakhon Si Thamarat,亦稱“西勢洛坤”)、越南和寮國的郎普拉邦(Luang Prabang)、緬甸南部的碧古(Pegú)地區。馬來半島的一些地區也同樣向蘭甘杏王國進貢。
作為上述征服的結果,泰族人接受了高棉族人和孟族人極其豐富的文化影響。
以種植根莖植物為主的農業是經濟生活的基礎,這種生活曾以食水果和住木屋為其特徵。

葡萄牙城牆廢墟 (泰國) 艾尤提亞
素可泰的君主們信奉佛教關於王權、父權和可接觸之權的學説,這一受印度模式影響的學説影響了東南亞所有的君主們,這是因為印度的阿索加皇帝(Asoka,公元前267-227年)曾於公元前三世紀曾向這一地區派遣了一批傳教的佛教徒。素可泰王朝的所有君主都取“聖名君主”(Tha Mmaracha)之稱號,這一稱號神一般地與自稱有特殊智力的君主的佛教信仰緊密相聯,君主們按照公正、誠實、仁慈(慈悲)和臣民們的共識等訓誡進行統治。(8)
3)阿育他亞時期(Ayuthia)
阿育他亞城是由羽通國王(Uthong),即拉瑪鐵菩提(Rama Thibodi)於1351年建立的,他因為試圖征服鄰近王國,從而使其統治湄南河盆地(Menam Chao Phraya)而名聲大振。
他的這一對外進攻擴張的政策導致了作為獨立王國的泰王朝的消失,使其納入了阿育他亞統治範圍。15世紀,暹邏一直同柬埔寨(Camboja)進行連綿的戰爭,直至最後(於1431年摧毀其首都吳哥(Angkor)。這類戰爭在東南亞相鄰的王國之間司空見慣,其目的在於爭奪至關重要的資源和地區霸權。
阿育他亞統治了湄南河盆地,包括在北部建立的素可泰和清邁王國、高棉王國(包括吳哥)和南部及西部許多親王的領地。在14到15世紀之間,這種擴張達到其巔峰。(9)
16世紀初葉,暹邏同清邁的親王們多次爆發戰爭。經過1516-1538年一段停戰期後。同緬甸的戰事又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1516-1583年之間,暹邏變成了緬甸的附屬國。
在達洛呵國王(Trailok,1448-1491年)統治時期,阿育他亞牢固地矗立在泰族人居住地的中心。其君主們獲得了越來越絕對的權力,越來越尊崇布拉瑪尼古(bramânico)的“國王即是上帝”(即神)的訓誡。
在這一時期(1351-1767),君主們受到王權神聖的習慣的影響,他們的加冕要按照布拉瑪尼古儀式進行,並要採用印度的稱號。例如,阿育他亞王朝的創始人拉瑪鐵菩提的名字便是從維斯努神的化身Rama派生而來,他是一位印度史詩中的英雄“拉瑪亞納”。(10)
柬埔寨被打敗之後,暹邏王國的影響擴展到整個馬來半島。特納申林(Tenasserim)和力告(Ligor)兩王國也置於暹邏人的統治下;帕昂(Pahang)、帕當(Padang)、登甘努(Trengganu)、呵蘭單(Kelantan)、呵達(Keddah)和色蘭告(Selangor)也像馬六甲(Malaca)一樣稱臣於暹邏。當時暹邏最繁榮的港口位於孟加拉灣,靠近特納申林的梅圭港(Mergui)。中國和暹邏的商品從這裡被輸運到印度的港口,然後再運送到歐洲(最主要的商品有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暹邏的木材、錫、象牙、大象和水牛等)回程時來自印度的商品先運送到特納申林,主要是棉花,然後再溯河上運到阿育他亞城。
作為貿易上商品的一個周轉中心,阿育他亞城的繁榮主要起因於下湄南河盆地三角地區域經濟的長期發展,當自德哇拉哇弟時期以來建成的大城市消失後,在其廢墟上建造了新的城市,繼續從事經濟活動。(11)
阿育他亞城是當地原始社團經濟繁榮的成果,例如像德哇拉哇弟時期的羽通-納空(Uthong-Nakhon),巴通一空布亞地區:高棉人擴張時期的素哇納蒲-拉沃地區(Suwannaphum-Lavo),還有素攀武里-華(Suphanburi-Lop)和武里-阿育他亞地區(Buri-Ayothaya)最後這兩個地區阿育他亞城屬於同一時代。
阿育他亞城的地理位置打開了其與外部世界接觸的大門,並為這一地區相鄰的城市提供了一條商品出口的通道,阿育他亞城位於三條最大河流的交匯處(即湄南河、巴沙克河和華富里河),這使她不僅同北部和東北部各府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聯繫,而且也同內地最大的幾個王國有了往來,例如:萬納(Lanna)、萬昌(Lanchang)、柬埔寨(Cambodja)和巴甘(Pagan)王國,這些王國利用當地自然資源進行貿易,使得暹邏的貿易網不斷向亞洲的西部和東南亞擴展,甚至還達到印度科洛曼德爾海岸的港口,波斯和歐洲。(12)
作為一個農業和從事海上貿易的王國,其對外政策對於維護本身利益是至關重要的。

“葡萄牙原野”之廢墟 (泰國 艾尤提亞)
1491年拉瑪鐵菩提二世登上王位後,阿育他亞王朝便開始同外國發展外交和貿易關係,並推測波斯商人在阿育他亞城建好後,即會來訪問該城。
最早同阿育他亞王朝建立關係的是周邊鄰近的王國,例如:素可泰王國和柬埔寨高棉王國。
中國人、勒濟奧人(Léquios)、日本人等都派出長駐商人同阿育他育王朝建立了貿易關係。
1512年,最早的一批歐洲人,即葡萄牙人(他們於1511年佔領了馬六甲,暹邏的君主們一直聲明對該城的統治權)來到了這裡。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Duarte Fernandes)是受阿豐索·阿爾布刻爾克(Afonso Albuquerque)派遣,第一個踏上暹邏的歐洲人。
1538年爆發了同緬甸王國之間的戰爭,並於1549、1563和1568年三次再交戰。最後一戰使阿育他亞王國稱臣於緬甸王國,受其統治15年。
1584年,納勒敦(Naresuan)親王驅逐了緬甸人,重新宣佈獨立,1590年,達瑪拉(Thammarach)國王去世,他的兒子納勒敦登基,並將阿育他亞的文明推向最輝煌的巔峰。經過多次同緬甸交戰,他終於鞏固了阿育他亞王國的獨立,並延續了160年。在這一時期內,暹邏才真正作為東南亞最強大的王國之一而崛起,其政治逐漸趨於制度化,並有強大的經濟軍事權力予以維持。
於此同時,對外貿易關係不斷發展。我們來舉一些最有説服力的例子:
1608年,向荷蘭王國派遣了第一個泰族人使團(他們是最早抵達歐洲的泰族人)。
1621年,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通商條約。該條約規定將以本地的產品(錫、蔗糖、椰油、檀香木等)交換日本的銀和銅。
1681年,國王納萊(Narai)向法國派遣使團,並於1684年再次派遣。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泰國王的主動性予以回報,派遣了第一個法國使國,使團中有一些法國傳教士(1685年)。
1688年,因納萊國王生病,爆發了驅逐法國人的宮廷謀反。暹邏的對外開放因納萊國王的死而告終,把國家對歐洲貿易的大門關上了。
納萊國王和他的宰相死後,1688年,篡權者加冕登基,號稱碧差乍(Petracha)國王,他開始了一個新的王朝(萬彔郎王朝,Ban Plu Luang)。1709年,國王的長子繼位,號稱泰沙(Thai Sa)國王,在他統治期間,同中國的貿易往來明顯增加,主要是出口稻米。原來許多同中國及日本的貿易都是通過荷蘭人進行的,現在由私營的中國商人充當了中間商。1733年,泰沙國王去世後;發生了爭奪王位的鬥爭,最後由波羅瑪呵(Borommakot)登基稱王,其統治時期被稱為是一種“黃金時代”,他是阿育他亞最傑出的、酷愛和平的君主。他死後,兩個兒子為爭奪王位而爭鬥,最終,矣卡塔(Ekatát)王子奪取了王位,號稱波羅瑪拉乍國王(Borommaracha,1758-1767)。
1765年緬甸人再度侵犯阿育他亞,對該城圍攻封鎖了兩年之後於1767年一舉將其摧毀。(13)
4)曼谷時期
1767年泰軍將領鄭信(Phya Taksin,暹邏人,華人後裔)在湄南河西岸(東岸是曼谷)吞武里(Thonburi)建立新都。國王鄭信隨後用了15年的時間試圖對這一地進行綏靖;但是,1782年另一位將軍昭披耶節克里(Chao Phraya Chakri)登上王位,號稱拉瑪鐵菩提一世(1782-1803)。出於防御上的原因,他將首都遷移到湄南河東岸的曼谷,開始了節克里王朝,並一直延續至今。
1809年拉瑪鐵菩提二世加冕登基,在他統治期間,暹邏同西方國家的關係重新打開。那時暹邏同中國的貿易往來幾乎全部通過中國的帆船來進行,有些帆船還是在暹邏製造的。當歐洲人同曼谷重新開始通商往來時,他們使用的大貨船遠遠勝過中國帆船,以致暹邏人也想採用。可能因為這原因,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開始向暹邏人傳授造船技術。
1.5宗教的主要特點
印度的旅行者隨身將印度教和佛教的學説和禮儀,以及其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東西(君主政體概念,法典和管理方法)帶到了暹邏。
在德哇拉哇弟時期或前德哇拉哇弟時期,佛教的形態同從12世紀起便存在於暹邏的那些形式是不相同的。從素可泰時期開始,暹邏便以其最傳統的教規,用他們最原始的方式信奉佛教(分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又稱上座部佛教,比大乘佛教更正統)。
13世紀,伊斯蘭教由阿拉伯商人和冒險家通過馬來半島傳入暹邏。泰族人中的穆斯林絕大部份是馬來人,這一點反映了最南部地區同馬來西亞接壤的幾個府的文化遺產是共同的。(14)
基督教於16-17世紀由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及葡、西耶穌會傳教士傳入暹邏,後來還有新教傳教士,他們主要是規勸少數民族信教,例如中國的移民。儘管如此,基督教傳教士在衛生和教育領域曾作出過巨大的貢獻。(15)
1.6結論
位於東南亞中央地帶的暹邏,南部同馬來西亞接壤,西部同緬甸,北部同寮國,東部同柬埔寨接壤,因其地理位置(戰略上是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和豐富的資源(例如:北部地區的氟石、鎢和鎢酸鹽;西部地區的鎢和寶石;東南部山區光彩奪人的藍寶石:南部地區的鎢和東北部地區藏量豐富的鉀鹽)很早便吸引著其他民族。
但應指出,暹邏是東南亞唯一的一個從未遭受任何西方強國殖民統治的國家。
暹邏曾遭受高棉人和緬甸人周期性的侵略,二次大戰時曾被日本人佔領,但她被外族控制的時間是極其短暫的,不足以影響泰族人的個性。
暹邏擁有六千年文化、社會及經濟發展的歷史,早在中世紀便同中國和阿拉伯世界那些遙遠的國家建立了關係,隨後還同歐洲的強國進行貿易往來。
這是一個佛教佔統治地位,並一直無變化,歷史上一直保持高度發展水平的君主立憲制的王國。暹邏擁有她自己的文化(戲劇、文學、音樂、建築、雕刻、繪畫、製陶術、金銀珠寶製作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自己的飲食,拳術和自己的宗教信仰。儘管她也受到外部的影響,但她從未失去過她自己的、帶有明顯印跡的個性。
2-澳門
2.1-葡萄牙人同中國人最早的接觸
在葡萄牙航海家們踏上東方的土地之前,西方的一些旅行家從13世紀中葉開始,已經同中國建立了聯繫,例如:諾奧·德·皮亞若,德·加皮納(João de Piano del Carpine,1245-1247),方濟各會教士諾奧·德·蒙特科維若(João de Montecorvino,1291-1292);一年之後有馬可·波羅(Marco Polo)。進入14世紀後,有貝亞托·奧多利科·德·波得若內(Beato Odorico de Pordenone)和諾奧·德·馬里戈若利(João de Marignoli)。從這時直至葡萄牙人的到來前,據考證,歐洲同亞洲之間的接觸一直在減少,其原因應歸於下述事實:例如,宗教聖地最後一批自由港的關閉(1291),伊朗(1295)和土耳其斯坦(1342)的伊斯蘭化運動,中國明王朝的崛起(1367);而在這同一時期,西方爆發了黑色大瘟疫(1348)和開始了大分裂(1377)。
1508年,堂·馬努埃國王派遣迪奧戈·羅佩斯·德·塞蓋拉(Diogo Lopes Sequeira)前往馬六甲,以獲得有關中國人及其貿易的情況。1509年,他來到馬六甲,並同一些停泊在那裡的中國商船進行了接觸。但是,抱敵視態度的馬來人把他趕回了里斯本,使他不僅沒有完成所肩負使命,而還將一些做了俘虜的葡萄人留在馬六甲。
1511年,印度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經百般努力救出留在馬六甲的葡萄牙俘虜後,終於佔領了該城。馬六甲在葡萄牙人的統治下一直到1641年(後被荷蘭人侵佔)。從此之後,葡萄牙人開始進入中國海了。1513年,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手下的一位船長諾熱·阿爾瓦雷斯(Jorge Álvares)乘坐一條中國商船抵達達芒(Tamao或Tamau)海灣,後來又到過維尼亞加(Veniaga)島,該島名稱為“商業”之意(16),諾熱·阿爾瓦雷斯在島上豎了一個刻有葡萄牙國徽的十字架。
在同中國人最早進行接觸的葡萄牙人中,還有一些純粹抱有商業目的的商人。
2.2-葡萄牙人的滯留,安家和定居
最初,澳門是一個小港口,是海盜的巢穴,又是漁民的避風港。葡萄牙人同澳門地區最早接觸的年代,以及澳門開埠的時間,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葡萄牙的歷史資料都一直爭論不休。
根據中國方面的史料,1553年,葡萄牙獲准在澳門海灘上晾曬被暴風雨浸濕的貨物。對於那些曾熱切希望獲得一個比先前的港口更安全的避風港,並以其作為與日本進行貿易的中轉站的人來講,位於到處是海灘和光禿礁石的香山島(Heung Shan)最西南端的澳門(或阿媽閣),的確是一個天然避風港,同時也是修理船隻和等候季風的理想之地。今天,這一港口被葡萄牙人稱為內港,而那時中國稱其為濠鏡。
與此同時,從1548年便來到印度的雷奧內爾·德·索薩(Leonel de Sousa)受堂·諾奧二世從里斯本傳來的任命,擔負起組織兩次對中國的航行,他於1552至1554年組織了第一次航行;由於西蒙·德·安德拉得(Simão de Andrade)於1518年的所作所為,中國人對雷奧內爾·德索薩持謹慎的態度,他們關閉港口,禁止通商,導致他只進行了“少量的貿易,收益甚微”。但是,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之後,他終於同廣州的海道二等海事官員汪柏(Wan Pé或Van-Pó)訂定了一個協議;因為港口都在他的管轄之下。從此,可以在沒有官方制裁的情況下進行通商,但要交納税收(為商品價值的10%)。雷奧內爾·德·索薩同中國當局達成協議的時間為1554年,一些歷史學者認為,這即是澳門開埠的時間,或者説,從此澳門變成了一個永久的商站(17)。
大致可以肯定,從這一時期開始,葡萄牙人以半官方的形式在澳門住了下來。最初,他們搭草屋放置貨物,並供留在陸地看守貨物的人居住。逐漸地在中國人的縱容下,葡萄牙人在他們的地位還非常不穩定的情況下,建造了木頭和磚石結構的房子。
另一些史學者認為,1557年標誌著澳門正式開埠,當時“廣州的官吏應當地商人的請求,把澳門港饋贈於我們。”(18)
1555年,廣州港重新向葡萄牙人開放,每年一次(稱為年市)。
就這樣,澳門商站建立在通往廣州的一個要塞之處。
2.3-教會的影響:精神權力和時間權力
貿易結構決定了最早的民事組織機構形式,但是,天主教會作為權力體制和社會及城市空間聚合的要素,也在澳門紮下了根基,並在國際層次上為澳門的地位和合法化作出了貢獻。從澳門商站形成的初期,天主教傳教士們就在此落腳,伴陪著葡萄牙人。
主教和教會組織的權力不僅包括精神的統治,同時也包括時間的統治。教會持有大量的物業和財產,其中青洲屬於耶穌會、灣仔島,又稱神父島,屬於耶穌會和奧古斯丁會;教會還特別是民眾的引導者。但是,教會同民事權力機構之間權力分配和劃分行動範圍並不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
教會的權力往往超越宗教的範圍,干涉政府的運作,這種對民事範圍的干涉是完全合法的,因為澳門的章程指明主教可以擔任市政議會的主席。市政議會和教會干涉地方政府事宜,因為政府機構往往有經濟上依靠教區或宗教團體,並經常被迫向他們請求借貸。儘管17世紀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圈子內曾出現過一段權力危機時期,但教會繼續是最穩定的機構,市政議會在中國當局面前採取實用主義的接受態度,因為中國當局無可逆轉地看到了他們的權力進一步強化。
2.4-澳門的統治,管理及其發展
澳門市議會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向從負責航海到日本的船長,印度總督和皇室中央政府代表的葡萄牙當局負責。
17世紀前半葉,產生了代表中央權力的統治架構,即總督,他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但是儘管架構已確立,但由於總督與市議會之間持續不斷的緊張狀態,特別是多數總督的任職期限都很短,這一架構變成了一個非常脆弱的權力機構。(19)
但是,里斯本和果阿的命令和決定,或者説中央政府和印度省(20)的命令和決定,並不總是被市議會認真接受和執行,因為市議會以現實主義的態度同澳門的實際相適應,而其議員即有葡萄牙人又有中國人。
華人社團逐漸地擴大,並因此而在澳門設立了中國機構,以便從法律上對華人社團進行管理(這機構稱為Tso Tang即官吏,1736年);這一機構的設置標誌著一系列官吏來澳門的開始,並清楚説明在澳門存在著一種混合的管轄權。
總督同市議會之間的不相容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某些方面出現了嚴重問題,並加劇了不同宗教組織之間因著名的“禮儀之爭”而產生的公開不合的局面。(21)

縱觀歷史,市議會無疑是多種機構綜合匯集體中最基本的機構,它將葡萄牙的立法同推動與華人社團和葡萄牙帝國在本地的關係結合起來,並試圖對各種權力不斷地進行調和。 2.5-貿易外交關係與依賴關係 葡萄牙在遠東的貿易主要是以中國的絲綢換取日本的銀錠為基礎的。除了這兩種主要商品外,也買賣其他商品:在中國購買錦緞、麝香、黃金、瓷器等;在日本則購買銅、武器(劍和矛)、漆器等。 當時,中國同日本之間的貿易完全被切斷了,但是兩國之間仍保持著通過葡萄牙人來進行的間接貿易往來。澳門一方面擔負著向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隊提供支持和供給的職能,另一方面在當地的生活中又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持別是在日本同中國之間的貿易聯繫上。 那時的廣州是中國南方唯一一個進行對外貿易的港口,在外國人當中,只有葡萄牙人獲准可以去廣州。但是,澳門不只僅是一個出口的海港,而且也是中國的一個供應中心,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非法的或半官方的貿易變成了一種獲利的活動。除此之外,澳門不僅只同中國沿海的港口進行貿易往來,而且也同亞洲和歐洲往來,還把貿易關係擴展到太平洋其他地區,其中最突出的是從16世紀起同菲律賓進行的正規貿易。而馬尼拉在西班牙帝國的範圍內,通過一條長長的“阿加布爾科”(Acapulco)航線同西印度(即中美洲)相連,這條海路上遠航運送墨西哥和秘魯的白銀與黃金。船隊從馬尼拉將稻米,印度尼西亞的奴隸和墨西哥的白銀帶來澳門,回程時從澳門帶走的有鐵炮、青銅器、絲綢、茶葉、珍珠、香料、檀香等等。這些商品都是在以澳門為起點的各條航線上的許多供應市場上獲取的:檀香是在索洛和渧汶購買的,珍珠在印度尼西亞和錫蘭獲得,香料和茶葉則分別在馬六甲和中國購買。 還建立了其他航線,例如印度支那航線,帝汶和馬六甲、果阿等航線,有時還有直達里斯本和巴西的航線。 西班牙人對葡萄牙的統治(1580年-1640年)給澳門帶來了消極的後果,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外交和貿易關係,而且還造成了新的競爭帝國的出現,例如荷蘭船隊於1601年至1622年連綿不斷地攻擊澳門,但最終都被葡萄牙人擊潰了;1637年,出現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第一個船隊。 1639年,同獲利頗豐的日本之間貿易的中斷,給澳門的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本地居民開始尋找新的市場,發展同其他地區的貿易關係,特別是同印度尼西亞、渧汶和馬加薩等(Macassar)的關係。 1641年,荷蘭人佔領了馬六甲,這對澳門也是一個沉重打擊,因為除去失掉了東南亞最主要的供應中心之外,馬六甲的失陷也意味著航行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葡萄牙船隊失去了一個支援中心。於是,澳門需要在那一地區尋求找到新的關係,暹邏便成了澳門依靠的對像。 儘管1639年同日本中斷了貿易往來,後來又同馬尼拉也停止了貿易(1643年),但澳門同印度支那(洞清、柬埔寨和科欽支那)、暹邏、馬加薩、渧汶和索洛之間的貿易仍繼續進行,從未中斷。 </figcaption></figure>
<p>
由於只有葡萄牙人獲准進入廣州,外國人便來澳門補充給養。在不穩定的幾段時期內,特別是1604年至1644年之間,同廣州的貿易中斷了,澳門城處於一個危急的時期。但是,為回報葡萄牙人在打擊南部海岸中國海盜所提供的幫助,重新恢復了珠江河口地區的傳統供應線,直至1685年,唯一被允許進入這一地區的是葡萄牙人。中國當局通過海關控制,從這條貿易線上獲得收益,這種收益並且越來越大,於是經過1597年關始進行的一系列努力後,中國當局終於在1688年,於Praia Pequena地區設立一個海關,又稱“Hopu”。
</p>
<p>
17世紀,澳門的人口持續逐漸增加,中國派駐澳門的官員(主要是從1644年開始)也在不斷增多。
</p>
<p>
由於中國方面不斷地提出一些強力的要求(正常的或金錢的),導致向澳門居民派收新的税種,並引起了(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等)不同團群之間的衝突。為試圖解決這些問題,葡萄牙先後向北京派了三個使團:第一個使團於1667年派出,使團長為馬努埃爾·薩爾達尼亞(Manuel de Saldanha);第二個使團1726年派出,由亞歷山大·梅特羅·德·索薩·梅內尼(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zes);1752年第三個使團出發,由弗·阿西斯·巴切科·德·桑巴奧率領。三使團都一無所獲。
</p>
<p>
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確立有效的殖民統治,這一任務由費雷拉·多·阿瑪拉爾總督(又譯阿馬留總督)完成的。他利用當時有利的國際局勢和依靠外部勢力,主要是英國,而大獲好處,因為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中打敗了中國軍隊。<RETLAB1001900140021><a data-cke-saved-href=# href=#"LAB1001900140021") data-cke-saved-name="RETLAB1001900140021" name="RETLAB1001900140021">(22)</a>
</p>
<figure><img data-cke-saved-src=)
1859年2月10日於曼谷簽訂的“葡萄牙與暹羅國友好、通商及航運條約”部份(澳門歷史檔案館)
從18世紀末開始,澳門城便不斷地擴大,不停的自然或人工填海不僅使城市的面積增大了,而且也引來了無法控制的,大部份來自中國的移民潮。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完全改變了其面貌。
2.6結論
澳門是西方和東方之間第一個長期往來的交匯城市,最初僅是貿易的交往,隨著時間的推移,則開始了文化與宗教的交流。
直至鴉片戰爭結束(1839-1842),澳門一直是中國沿海唯一的一個向國際商船開放的港口,鴉片戰爭一結束,有關條約(23)所規定的五個港口城市: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便向西方列強打開了門戶;並且還於1842年8月29日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人。1858年,通過天津條約(24),這一條約為1860年的北京條約(25)所確認,中國被逼進入歐洲國家圈之內,或者説,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了國家共同體。
至此,北京可以直接聽到澳門的聲音了,不用廣州的官吏們進行歪曲事實的調停。於是,葡萄牙皇室開始尋求通過同中國簽定一個條約,以確立澳門的法律及政治地位,1862年,葡萄牙同中國簽署了“友好通商條約”,但是此條約從未被批准,葡萄牙人繼續感到有必要最終確立澳門的地位,終於在1887年,同中國簽定了第二個條約,此條約於1888年,獲批准;在此條約中,葡萄牙人對澳門的統治得到承認,從而保證了葡萄牙最終擁有澳門。
無論是饋贈,交納佔地税,還是領土侵佔,事實就是澳門的這種狀況持續了四個多世紀,從16世紀就開始在澳門落腳的葡萄牙人在這裡建立了明顯是葡萄牙式的行政管理方式和統治權,從市政權力機構市議會,後改名為市政廳,到司法機構和中央權力的代言人(最初是司令官,後改為總督),無一不是葡萄牙色彩的。
大概正是由於澳門存在著平衡的司法和立法權力,才使得澳門一直保持這種局面,以及葡萄牙人同中國人多個世紀的相處和共同生活,這都源自於兩國人民之間非言語或公開表達的相互理解。
澳門在很長時間裡,是兩種不同文明和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交匯點。
二、葡泰兩國人民間最早關係的建立
1. 葡萄牙人同暹邏人最早的接觸
葡萄牙人同暹邏人最早的接觸大概可以追溯到16世紀初,根據加斯帕·科萊亞(26)的考證,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曾派特使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去見暹邏國王,以求與他建立友好關係。費爾南·羅佩斯·德加斯塔涅達也提到過此事,以及暹邏國王也向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派出特使這一事實(27)。
這樣葡人同暹邏之間的通商關係便開始了。
諾奧·德·巴洛士(João de Barros)認為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也經曾向暹邏派出過第二個使團,團長可能是安東尼奧·德·米藍達·達澤維多(António de Miranda d'Azevedo)(28)路易·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 Brito Patalim)給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的一封信中,寫到“暹邏國王的特使們同安東尼奧·德·米蘭達一同抵達”,從而證實了曾派出後者為使者。奇怪的是,在提到安東尼奧給予暹邏使者熱情的接待後,這位馬六甲的指揮官又談到了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寫給暹邏國王的一封信,在信中阿豐索承諾讓他來統治馬六甲。暹邏國王回答説“如果閣下在奪取馬六甲之前曾提供幫助,會發生這樣的事”。(29)
似乎可以從這裡得出結論,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曾尋求暹邏國王的支持,但後者聲明對馬六甲的擁有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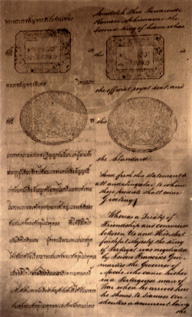
1859年2月10日於曼谷簽訂的“葡萄牙與暹羅國友好、通商及航運條約”部份 (澳門歷史檔案館)
葡萄牙佔領馬六甲並沒有引起暹邏國王的抗議,可能這位國王當時正在同清邁王國進行連綿的戰爭,以保衛北方的疆界,因此他無意再同葡萄牙人另開戰事(30)。加斯帕·科萊亞也談到暹邏國王派信使(1514)由陸地前往果阿,“請求總督閣下證實他的友好,並保證他們的船安全到馬六甲和其他所有地方通商”。信使們帶給總督一位叫馬努埃爾、法戈蘇的人寫的一封信。當時,此人正在暹邏“處理有關馬六甲商站的事”。他原來是被授命留在暹邏,準備就暹邏的貿易風土人情和港口的條件寫一份報告。(31)阿爾布刻爾克提到曾派這位馬努埃爾·法戈蘇和安東尼奧·米藍達見暹邏國王,讓他寫一本有關“這一地區的所有事物,所有商品……”的書。根據一些作者的論述,這本書於1514年1月被帶到果阿城,交給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在果阿,馬努埃爾·法戈蘇遇到了碧貢(Pegú)和暹邏王國的特使們;同時,他還帶來了馬六甲城堡指揮官路易·德·布里托的一封信,信中“向閣下講述了馬六甲的局勢”。(32)
在1518年寫給國王堂·馬努埃爾的另一封信中,馬六甲指揮官阿豐索·羅佩斯·達·科斯塔(Afonso Lopesda Costa)向我們表明曾派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到暹邏,對此行“期望獲得更多利益和順利的通商,但他對該城(即馬六甲)很不滿意”。根據同一封信,這一不滿是因馬六甲的前任指揮官諾熱·德·有里托曾命令燒掉了屬於暹邏王國的蓋達鎮。(33)然後,信中又説,暹邏國王曾是馬六甲的統治者,“是這一地區最大的君主,”擁有無盡的財富和“大量可供給的食物,而且是馬六甲最主要的商品--糧食的提供者。”(34)
從這裡可看出,葡萄牙人在同暹邏王國發展友好關係上作出努力是多麼的恰當。
上面提到的使團似乎取得了成果,因為諾奧·德巴洛士確切指出:1518年堂·阿雷蘇·德·梅內塞斯(D. Aleixo de Meneses)派杜阿爾特·科埃略前往暹邏,因為他已同安東尼奧·德·米藍達去過一次,作為葡人使團又一次受到友好的款待(35)。而且一些學者得出結論,可能在暹邏國王拉瑪鐵菩提的友好接待和表現出的宗教容忍精神基礎上,當時簽訂了第一個葡暹條約(36)。
葡萄牙駐暹邏領事安東尼奧·費里西亞諾·馬克斯(Antonio Feliciano Marques)在他“1881年報告”中清楚講到:1518年,杜阿爾特·科埃略率領的使團到後,簽訂了《葡萄牙同暹邏友好通商條約》(37)。赫清森(Hutchinson)也説,1516年,“暹邏同一個西方家”簽訂了第一個條約,葡萄牙從此獲准“在阿育他亞城和暹邏其他港口通商”(38)。沃德(Wood)提起這一事件也説,由於此條約,允許葡萄牙人居住下來,並可在“阿育他亞、特納色林、梅圭、北大年,納空時探瑪叻(即利高)”從事貿易。(39)
我們看到,由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推動的尋求同馬六甲周邊王國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目的在於使葡萄牙人可以在那一地區和平地進行通商。
暹邏是一個農業國,她需要貿易往來;另外,她擁有大量的財富吸引著其他國家。關於這一點,那一時代的年鑑和史料講述得很多。
杜阿爾特·巴博薩描述暹邏王國時,曾説:“一個偉大的王國叫作暹邏”,其國王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他提到這個王國的主要財富,談到她擁有一些優良的海港,“這些海港散佈在從此海岸到與中國相望的馬六甲海岸。”他還特別提請注意特納塞林和蓋達城,這裡的辣椒輸往馬六甲和中國(40)。

1859年2月10日於曼谷簽訂的“葡萄牙與暹羅國友好、通商及航運條約”部份 (澳門歷史檔案館)
多美·比勒斯(Tomé Pires)開始這樣説,暹邏擁有許多良港和許多外商人。他列數了暹羅的財富,特別是糧食,以前每年都有“三十多艘帆船將糧食運送到馬六甲。”但是由於馬六甲國王(曾是暹邏國王的臣民)起來反對暹邏的控制,暹邏人已有22年不同馬六甲直接通商。(41)
在馬六甲的指揮官路易·德·布里托·帕塔林的一封信中,他説曾給予暹邏國王派到馬六甲的特使以熱情的款待,並提請注意這個王國的財富,他也提到了暹邏人已有多年不同馬六甲通航這一事實。(42)
諾奧·德·巴洛士認為,暹邏國王僅次於中國的皇帝,是亞洲地區第二位重要的君主(43)。
費爾南·羅佩斯·德·加斯涅達在談到暹邏廣闊的疆土和天然的良港後,列數了其財富:黃金、白銀、香樹脂、火漆、藍寶石,以及許多農產品(44)。
費爾南·門德斯·賓托描述了“暹邏王國和索南帝國的偉大,無盡的財富和資源,肥沃的土地……”(45)他還講,暹邏是葡萄牙人尋找庇護所過冬的地方,因為東北季風使得在中國海上的航行變得困難和危險。(46)
應該指出,葡人發展同暹邏的睦鄰友好政策是有其各種原因的:馬六甲要依靠來自暹羅的稻米和食物;基本上不瞭解暹邏人的軍事和航海實力;不在這一地區再尋求樹立軍事上的敵人。
2. 葡萄牙人在暹邏定居
在歐洲所有國家中間,葡萄牙人是最早來到暹邏的。葡萄牙人主要給暹邏帶來三樣東西:先進的軍事技術和戰術,現代戰爭的藝術和技術,以及防御城堡的建築術。(47)
從葡萄牙人與暹邏人之間最早的接觸開始,軍事上的幫助在暹邏同葡萄牙在東方的權力機構之間的關係上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為換取這種幫助,雙方尋求保證使東南亞這一重要的王國在該地區的存在處於有利的地位。葡萄牙人承諾提供武器和火藥;暹邏國應該向葡萄牙提供在暹邏居住和從商的便利,並給予他們宗教的自由。(48)
當時,暹邏的國王拉瑪鐵菩提二世正在同清邁王國進行戰爭,同葡萄牙人締結盟約對暹邏十分有利,由於獲得大量的火器和葡萄牙人的幫助,暹邏國向清邁發起攻擊,一舉在喃邦摧毀其軍事力量:其後幾年,清邁一直平靜無戰事。(49)可能正是因為葡萄牙人多次向暹邏提供軍事援助抗擊緬甸人的入侵,而獲饋贈土地一塊,供他們居住。(50)
於是,在暹邏便出現葡萄牙的領地。
2.1僱傭兵和冒險家
1516-1538年之間,葡萄牙人在暹邏居住下來。1516年,馬努埃爾·法爾貢(Manuel Falcão)在半島西海岸馬來人的巴塔內王國建立了一個商站,這一王國處於暹邏人的統治下。(51)
1529年一1533年,波羅瑪拉乍四世統治暹邏,後來其叔父將其廢黜,並登上王位,號稱巴差奧國王(Prajaio,1534年-1546年)。在他統治期間,葡萄牙人在暹邏的數量大增;1538年120個葡萄牙人組成了國王的私人衛隊,並教暹邏人如何使用歐洲的火器。火炮手作為“火炮專家”編入軍隊指揮等級,並被授予重要軍銜。(52)這位國王可能於1 544年由一位叫安東尼奧·帕瓦(António Paiva)的葡萄牙商人洗禮,改信基督教(其教名為堂·諾奧),其家人也變成了基督徒。(53)
費爾南·門德斯·賓托也曾提到,1540年,馬六甲的指揮官派出一位叫貝洛·德·法利亞(Pero de Faria)的使者去解救一位在暹邏被關了23年的葡萄牙俘虜,這位俘虜叫多明哥·德·塞薩斯,曾是弗蘭西斯科·德·卡斯特羅特使的使臣。貝洛·德·法利亞受到暹羅國王的隆重接待,暹羅國王滿足了葡萄牙國王堂·諾奧三世的要求,將多明哥·德·塞薩斯和另外被關押的16名葡萄牙俘虜一同交給了葡萄牙使者。(54)
多明哥·德·塞薩斯於1523年前往特納申林為巴森(Pacém)的葡萄牙城堡採購食物,但他和另外16個正在特納申林的葡萄牙人一起被捉走了。據巴洛士的記載,他們被交給暹邏國王,國王見他們熟悉火炮,便將他們編入了暹邏軍隊,他們曾多次參加暹邏國王同鄰國之間的戰爭。多明哥·德·塞薩斯還被任命為王室部隊的指揮官,環境的力量將他變成了一位真正的“走紅運的士兵”。(55)
1545-1546年。暹邏國王巴差(Phrachai,又稱巴差奧)重新卷入了同清邁王國的嚴重的戰爭衝突,並在對清邁的綏靖中動用了葡萄牙僱佣兵。葡萄牙僱佣兵在同緬甸人的戰鬥中屢屢獲勝,暹邏國王特授予他們在暹邏經商和定居的特權。(56)
應該指出,當時在緬甸國王一方也有葡萄牙人為其打仗。那些真正的“走紅運的士兵”各為其主而戰是不足為奇的。
在篡權者猜拉差(Chairacha,又稱Prachai)國王被謀殺後,暹邏經歷了一段內部極其不安定的時期。1548年,被殺國王的一個近親兄弟登上王位,號稱猜克攀國王(Chakkraphat)。1549年,緬甸國王侵犯暹邏,並包圍了阿育他亞城。這座城府得到了近50多個葡萄牙人的保衛,他們的指揮官叫迪奧戈·貝雷拉,是一位商人,隨“他的一艘船”來阿育他亞經商。(57)
我們看到,儘管是普通商人,但許多時候葡萄牙人被逼拿起武器,他們不只是為討好國王們的喜歡,而是保衛他們自己的財產和生命。
1569年,緬甸國王再次進攻,並佔領了暹邏和清邁,他扶持馬哈達瑪拉猜(Maha Tammaracha)登上王位,立他為阿育他亞國王,成為緬甸的附庸國。柬埔寨人也利用這一局勢,多次入侵暹邏。柬埔寨人對暹邏人的劫掠,使緬甸人允許暹邏人加強其軍隊和修築城池。1580年,在葡萄牙人的幫助下,於1550年修建的阿育他亞磚結構城牆被推倒,重新建築了比過去更堅實的新城牆(58)。
1584年,納萊素王子(Naressuan,又稱“黑王子”)動搖了緬甸的統治,他驅逐侵略者,抵抗1586年-87年緬甸人向阿育他亞城發起的進攻;1593年,在暖沙萊戰役中,他擊潰了緬甸人,鞏固了暹邏的獨立地位。(59)
達瑪拉猜國王(1569-1590年)曾一直不斷地向外國人購買火炮。因此,當納萊素國王(1590年-1605年)開始從政治上鞏固其父親的王國並成功擺脱緬甸的統治恢復獨立時,暹邏皇室軍隊在戰爭中已能熟練有素地使用火器。(60)
1594年,納萊素國王入侵柬埔寨,並在羅韋科(Lowek)俘虜了一些為柬埔寨國王效力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其中有迪奧戈·維洛索(Diogo Veloso)。俘虜們被帶到暹邏之後,迪奧戈·維洛索獲得了納萊素國王的信任。1594年末,借口購買武器,他隨同一位暹邏使臣來到馬六甲;在馬六甲,他擺脱了這位使臣,又跑去為柬埔寨國王服務。(61)
須指出,許多統治者對這些僱佣兵的極大信任,在某些情況下,使他們在這些國家的軍界和政界迅速得到提升;在另一些情況下,對於那些商人們來講,獲得商業上的利益可能是他們拿起武器保衛暹邏國王的理由。
我們來看一下“馬丁·阿豐索·德·梅洛·德·卡斯特羅寫給到副王的信”中是怎麼説的,“特向陛下告知,在中國、碧貢、孟加拉、奧里沙(Orixa)和暹邏,有兩仟多流浪的葡萄牙人在為陛下服務,由於他們在印度沒有任何生活來源,許多人投靠了摩爾人,變成了摩爾人”。(62)據記載,當時,許多葡萄牙人前往“印度各地”去尋找財富,但並沒有找到他們認為好的東西,於是他們便分散到整個東方,尋找他們夢寐以求的財富。他們是冒險家、商人、僱佣兵,他們在所經過的地區,按著環境和當地人的要求,變換著他們的身份。
我們相信這就是曾在暹邏發生的事情。
2.2傳教士
17世紀出現過一些棘手的事件,打破了當地社會的沉靜的氣氛,其中有的是與宗教有關的。下面我們舉幾個例子。
1566年,葡萄牙多明我會傳教士弗雷·熱羅尼莫·達·克魯斯(Frei Jerónimo da Cruz)和弗雷·塞巴斯蒂昂·多·坎托(Frei Sebastião de Canto)受馬六甲教長費爾南多·德·聖·瑪麗亞神父的遺使,成為第一批抵達暹邏的傳教士。(63)
暹邏的摩爾人殺死了弗雷·熱邏尼莫神父,刺傷了他的同伴。這位同伴被居住在那裡的葡萄牙人救下。暹邏國得知發生的事後,命令懲罰凶手。凶手便在巴卡隆(Barcalão)將塞巴斯蒂昂神父釋放了。他後來留在暹邏,經歷此次事件,他深得國王猜克攀的寵愛;塞巴斯蒂昂又從馬六甲帶來兩位同一教派的神職人員幫助他。1569年,當緬甸人圍困阿育他亞時,他們三人都被緬甸人殺害了。應馬六甲教長弗雷·費爾南多的請求,1569年至1573年間,果阿多明我會總教長弗雷·弗蘭西斯科·德·阿布萊烏(Frei Francisco de Abreu)派遣了一些傳教士到暹邏;但當爆發的戰爭使暹邏成了緬甸的附庸國(1569-1590),這些傳教士又被逼返回果阿。(64)
達瑪拉猜國王的繼承人納萊素(1590-1605),後來起來反抗緬甸人的統治。當納萊素國王侵入柬埔寨,於1594年佔領羅韋科時,曾帶回阿育他亞一批俘虜,其中有葡萄牙多明我會教士弗雷·席爾維斯特雷(Frei Silvestre),他當時在柬埔寨,還有諾熱·達·莫塔(Jorge da Mota)和路易斯達馮塞卡(Luís da Fonseca)神父,他們不久前被派往柬埔寨傳教·諾熱·達·莫塔神父受到了暹邏國王恩寵,應他的請求,國王恩准釋放了葡萄牙俘虜,其中的傳教士都留在暹邏。他們於1599年從暹邏寫信給教會總主教弗雷·熱羅尼莫·德·聖·多明我,向他表述了暹邏國王願意讓傳教士與之相伴的願望。(65)隨這批俘虜到達暹羅的還有葡萄牙方濟各會的傳教士,是該會最早到暹邏的教士,他們是格萊高利奧(Gregório),安東尼奧·達·馬達萊納(António da Madalena)和達米昂·達·托雷(Damão da Torre)。1582年末,方濟各會傳教士奧古斯丁·德·托德西雅斯(Agostinho de Tordesilhas)和諾奧·波布雷(João Pobre)被從澳門派往暹邏,但他們僅在那裡呆了兩個月,便因前者生病而一起返回澳門。(66)
但是,馬尼拉的方濟各會教士不斷來到澳門,1583年有三個教士前往暹邏,他們是熱羅尼莫·德·阿基拉(Jeronimo de Aguiar),弗蘭西斯科·德·蒙迪亞(Francisco de Montilha)和迪奧戈·傑梅內斯(Diogo Jimenes):由於緬甸人入侵暹邏,他僅在那裡呆了三個月,便返回澳門。
1600年諾熱·德·莫塔神父作暹邏國王的使臣被派往馬六甲,但他在海上去世了。獲得國王寵愛的路易斯·達·馮塞卡神父於1600年3月21日在教堂內被一位“有權勢的摩爾人”所殺害。(67)
此時,平定了王國內戰亂的納萊素國王發現葡萄牙人已有二至三年沒有來過暹邏,考慮到同馬六甲和中國進行貿易所帶來的利益,他給馬六甲去了一封信要求派遣方濟各會傳教士來暹邏,並特別指出要葡萄牙人,安德烈·多·埃斯比利托·桑斯神父被選中了,他從馬六甲同以費爾南·德·阿爾布刻爾克(Femão de Albuquerque)船長為首的使團,以葡萄牙國王的名義,登船前往暹邏。(68)他受到了國王的熱情接待;他在暹羅修建了一座教堂,並在那裡生活了好幾年,似乎在他之後,作為教長的安德烈·德·聖·馬麗亞(André de Santa Maria)神父和同一教派的安東尼奧·馬達萊納神父也到過暹邏王國。(69)
1606年,第一位耶穌會傳教士巴爾達薩·塞蓋拉神父到達暹邏,他受耶穌會印度省教長加斯帕爾·費爾南德斯神父(Gaspar Femandes)派遣而來,他建造了耶穌會在暹邏的第一幢寓所。(70)
1625年,耶穌會神父佩德羅·莫雷瓊,安東尼奧·加爾丁和日本神父羅芒·尼希起程從澳門前往暹邏,並於1626年3月抵達那裡。1627年,還從馬六甲派遣儒里奧·凱撒前去擔任傳教團團長。但是,後來西班人同暹邏人之間發生衝突,1628年,因松丹國王(Songtam)之死而造成的暹邏內部的不穩定更加劇了暹邏人同西班牙人的矛盾,傳教士們被逼撤離了。(71)
被派往暹邏傳教的還有在印度出生的諾塞·德·聖·瑪麗亞(José de Santa Maria)和西蒙·多斯·安儒斯(Simão dos Santos)神父,前者死在旅途中。在他們之後,諾奧·德·聖·貢薩洛(João de S. Gonçalo)和弗蘭西斯科·達·馮塞卡(Francisco da Fonseca)神父來到暹邏,前者被任命為教長。幾年之後,又有一些教士們接踵而來,暹邏的基督徒在不斷增加;馬六甲陷落後,暹邏又接收了許多人,於是,教長路易斯·多羅薩利奧神父(Luís do Rosário)又建造了一座教堂,並在那裡成立了聖·羅薩利奧兄弟會。(72)
1655年,耶穌會特使塞巴斯蒂昂·達·馬雅(Sebastião da Maia)將托馬斯·瓦爾瓜內拉神父(Tomás Valguarnera)從澳門派到暹邏,並建造了第二幢耶穌會寓所(1655年-1709年)。
1569年,諾奧·加爾多索(João Cardoso)神父被從澳門派到暹邏,他曾在特納申林傳教至1663年底,後被升為暹邏傳教團團長,來到阿育他亞城。隨他之後,1664年,諾塞·迪薩尼(José Tissanier)神父同一位葡萄牙神父安德烈·戈麥斯和一位法國神父佩德羅·阿爾貝來到暹邏。(73)1675年,瓦爾瓜內拉神父從澳門來到暹邏,接替傳教團長職務;他於1677年去世,諾奧·巴迪斯塔·馬爾多納多神父(João Batista Maldonado)接替團長一職,直至1691年(他於1673年從澳門來到暹邏)1691年,耶穌會特使阿雷蘇·科埃略(Aleixo Coelho)從澳門抵達阿育他亞,指命安東尼奧·迪亞斯(António Dias)為傳教團新團長。在其之後,加斯帕爾·達·科斯塔曾任團長,他從1703年到1709逝世,一直孤獨一人。(74)
後來,出現了巴黎外國傳教團會社,這一會社開始干涉葡萄牙教會擁有管理權的地區,抗議我們對洞清、暹邏、中國、科欽支那等地區的管理權。衝突變得極其激烈,這時教廷提出建議,由其任命只聽命於教皇,而不服從任何教區的各教派會長。(75)
葡萄牙提出了抗議,但是,由於葡萄牙當時所處的逆境,即教廷沒有承認其1640年擺脱西班牙後的獨立,而是拖到1668年才承認,其抗議無人理會;1658年任命了第一批主管“洞清、科欽支那及其鄰近國家傳教團的教長”。(76)
經過一系列衝突,葡萄牙對暹邏的管轄權被取消了。為傳播聖經的宗教團體的傳教士們受到了帕納拉(Phra Narai)國王及其宰相康斯坦丁·帕爾空(Constantino Falcão)的保護,但是,葡萄牙對暹邏的影響從此開始減退。
三、貿易、外交及宗教關係
儘管如此,兩國人民之間的接觸仍將繼續下去。暹邏國王埃加托沙拉(Ekathotsarat,1606-1620)在其兄弟(納萊素)死後,一登王位就寫信給印度副王堂·阿雷蘇·德·梅內塞斯,請求重新發展貿易關係。正在梅里亞波(Meliapor)的葡萄牙商人特利里當·戈拉奧(Tristão Golaio)帶領耶穌會神父巴爾塔薩·塞蓋拉前往暹邏。(77)
1616年,暹邏國王松丹的使團抵達果阿。作為回報,堂·熱羅尼莫·德澤維多副王派出一位曾在暹邏居住多年的多明我會神父弗蘭西斯科·達·阿努西亞松(Francisco da Anunciação)為特使,葡萄牙人與暹邏人之間重新開始通商,傳教士又重新進入這一王國。(78)
為了不拖延關於同馬六甲通商的談判,1608年至1609年曾任馬六甲神學院院長的安德烈·貝雷拉,於1619年被派往阿育他亞,同暹邏國討論有關和平條約;同行的有梅里亞波教區的巡視要員康斯坦丁·法爾貢(Constantino Falcão)和“一位已婚,住在科欽”,叫力斯帕爾·帕切科·德·梅斯基塔的人(79)。
在這以後,由於荷蘭人和英國人的插足,同暹邏的通商及派遣傳教士都中止了。但是,非官方的貿易往來可能一直持續到1633年。
1630年,暹邏古老的王朝(馬哈達瑪拉猜王朝)被新的巴沙通王朝(Prasatong,1630年1655年)所取代。暹邏因松丹國王時代葡萄牙人曾緝獲過一艘荷蘭商船這一遺留事件,同葡萄牙進行戰爭;這時,巴沙通國王給菲律賓總督(應指出,葡萄牙正處於西班牙菲利浦統治下,1580年-1640年)表示希望同葡萄牙人重新發展友好關係。(80)1633年,隨著葡萄牙使者抵達阿育他亞,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正式結束。
1636年,暹邏國王向菲律賓總督派出一使團作為對葡萄牙使者來暹邏的回訪。1639年,澳門總督堂·塞巴斯蒂昂·洛博·達·西爾瓦派出一使者前往暹邏,“一位已婚的澳門居民弗蘭西斯科·德·阿基亞·埃萬熱奧”,他也從暹邏國王那裡帶回重新發展貿易關係和要求派遣傳教士的請求。澳門區教長安東尼奧·德·聖·多明哥(António de S. Domingos)神父決定同哈辛托·西梅內斯神父前往暹邏,他們於1640年抵達。他們的到來遭到了荷蘭人鼓動的一些暹邏大臣的反對,主要是“一位小人”。(81)
至此,我們看到歐洲其他一些民族開始對這一地區感興趣了。其後果是在17世紀,暹邏王國出現了互為競爭敵手的外國人。先是荷蘭人,然後英國人,法國也來了。
我們舉幾個關於這種相互敵視的幾個例子。暹邏同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關係開始於1604年,從此,葡萄牙人在暹邏的影響便開始跌落,同樣,當其他西方國家出現在舞台上時,葡萄牙在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影響也漸減弱。(82)
1612年,英國人來到巴塔內,並在那裡開了一個商站,然後又前往阿育他亞城,受到松丹國王的接待;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阿育他亞城設了另一個商站。(83)
1621年,丹麥人抵達暹邏,但他們僅在梅圭經商,沒有在阿育他亞城建任何商站。
1641年,馬六甲失陷,貿易霸權終於從葡萄牙人手中轉移到荷蘭人手中。1660年,葡萄牙人被荷蘭人從馬加薩(Macassar)驅逐。這導致了1661年初,二百多個葡萄牙人乘坐一位富有的商人弗蘭西斯科·維埃拉的商船,涌向澳門、渧汶和暹邏,這一個商人的船隊當時正在這一區域經商。同年六月,一百一十多個葡萄牙人乘坐一艘荷蘭船前往暹邏和其他地區。(84)
1662年,法國傳教士抵達暹邏,受到國王帕納萊(1656-1688)的接見。儘管法國人明顯對暹邏的貿易感興趣,但是僅在1680年,法國國王堂·路易十四才向阿育他亞王朝派出第一個使團,開始了兩個國家之間的通商關係。(85)帕納萊國王轉向法國人是為削弱荷蘭人在暹邏的影響,因兩國在歐洲是敵人,常發生戰爭。
1683年,葡萄牙國王的特使佩德羅·瓦斯德·塞蓋拉從澳門來到暹邏,要求帕納萊國王保護葡萄牙傳教士,但毫無結果。(86)
1686年,暹邏國王的“王鷹號”船來到澳門,並帶來一封康斯坦丁·法爾貢的信,信中請求免除對“國王的布匹”的征税。(87)1686年,市議會開會討論法爾貢的請求。最後,市議會決定,應向征收本地居民商船的税一樣,征收這些布匹的税,因為澳門的商船在暹邏也要交税。(88)
1687年6月20日,市議會同安東尼奧·德·梅斯基塔·皮門特爾總督(António de Mesquita Pimentel)再次舉行會議,討論兩艘去柬埔寨驅逐中國海盜,並帶回一些中國俘虜的暹邏戰船進入澳門港一事。市議會不同意這兩艘船進入澳門,以避免引起中國當局的不滿。(89)
第二年(即1688年),市議會就暹邏國王之死討論是否派“一艘船前去暹邏王國”,因為“本城需要同暹邏王國發展友好往來及通商……商談葡萄牙因本城所欠暹邏之債務。(90)”因1670年,暹邏國王帕納萊應澳門市議會請求,向其提供過借貸,當時澳門的“資金已枯竭。”由於中國當局在不斷施加壓力(掠奪、要錢等),澳門的狀況又如此糟糕,這筆借貸分期拖了許多年才還清,最後一期還款於1722年付清。(91)
阿育他亞城被摧毀後(1767年),鄭信奪取了湄南河西岸的小港吞武里,並在那裡建都。建立起他的基地後,鄭信便開始征服其他地區,以其通過降服其敵手來恢復中央政權。1768年,鄭信國王向隨同他一起征戰的葡萄牙人饋贈了新首都內的一塊地,葡萄牙在此定居,修建了一座教堂(即吞武里聖十字教堂)。(92)
國王拉瑪鐵菩提一世(1782年-1809年)登上王位,開始了節克里王朝(Chakri),首都遷地到曼谷,位於吞武里下方,湄南河的東岸。在他的統治下,暹邏曾饋贈給印度一塊地“以建立一個商站”;葡萄牙駐暹羅領事安東尼奧·費里西亞若·馬格斯·貝雷拉在其1881年3月1日的報告中曾提及此事。(93)
這一饋贈由於設立在暹邏的神聖傳教聯合會的反對,沒有能夠實現。
另有記載,葡萄牙人及其後裔在曼谷暹邏國王(1786年)賞封的一塊土地上定居,這塊地被稱為“羅薩里奧領地”,他們在那修建了一座教堂(即羅薩里奧聖母教堂)。(94)
阿育他亞王朝被推翻後,暹邏進入了一個動蕩和戰亂的時期,並持續了四十年。而那時的歐洲,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而且波及到了澳門(特別是英國人的危脅)。至此,暹邏同歐洲各民族之間的關係中斷了。(95)
直到19世紀,澳門、葡萄牙同暹邏的關係才開始恢復。
四、結論
葡萄牙人不是最早到達暹邏的歐洲人,因為在他們之前曾有人去過那裡,例如:馬可波羅曾於1292年遊覽過暹邏的南部地區;威尼斯人尼古拉·迪·康蒂(Nicolo di Conti)在1430年前後也曾到過那裡。但是,是葡萄牙人第一個到達阿育他亞城,並同暹邏王國建立了官方的關係。
葡萄牙人同暹邏當權者的關係不是高度和諧的。他們之間曾特別因為貿易問題,發生過爭執和衝突。但是從整體上看,葡萄牙人沒有捲入阿育他亞王朝宮廷複雜、虛偽的政治鬥爭,他們從事商業活動,充當僱傭兵或傳播福音書,直至1767年阿育他亞城被摧毀。
作為“走紅運的士兵”,在暹邏同緬甸人頻繁的戰爭中,葡萄牙人以向多個暹邏國王提供幫助而作出自己的貢獻。為此,他們先在吞武里,後在曼谷被授予封地,為繼續葡萄牙在暹邏存在的悠久傳統而作準備,這一傳統從阿育他亞王朝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

葡萄牙在曼谷公使館建築物的正面圖,1918(澳門歷史檔案館藏)

17、18世紀澳門與暹邏關係往來圖示
微笑譯
【註】
Denys Lombard:《東南亞城市史》,載ESC年報,1970年7月/8月合刊,第850頁至854頁。
(2)Srisakara Vallibhotama的“古都阿育他亞”,載於《阿育他亞歷史中心》,Allied Printers出版社,1990,第22頁。
(3)Brian Harrison:《東南亞簡史》,London,Macmillam Press 出版社,1968,第36-40頁。
(4)Abha Bhamorabutr:《萬昌-泰國史前文明的搖藍》,Bangkok 1988,第13,14-16頁。
(5)John F. Caby:《東南亞及其歷史發展》,新德里,T. M. H. Edition,1976,第143頁-145頁。
(6)M. C. Subhadradis Diskul:《泰國藝術簡史》,曼谷,Amarim Printing Group,1991,第4-9頁。
(7)D. G. Ha ll:《東南亞史》倫敦,Mac Millan Press,1981,第182-184頁。
(8)同上,第185-188頁。
(9)Dhiravat na Pombejra:《阿育他亞王國及其對外關係》,阿育他亞歷史中心刊物,曼谷,Allied Printers,1990,第59-65頁。
(10)《八十年代的泰國》(《進入八十年代的泰國》訂修本),曼谷,Editorial Board,1984,第44-91頁。應該指出:當人們談論泰國文化時,應該將古典的宮廷文化與大眾文化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但又相互補充的文化。前者反映的是宮廷官場複雜的結構和色彩,並明顯受到印度的影響。
(11)Plubplung Kongchana:《港口之城阿育他亞》,載於《阿育他亞歷史中心》刊物,曼谷,Allied Printers,1990,第38頁。
(12)Dhida Saraya:《阿育他亞的集權制國家》,載於《阿育他亞歷史中心》刊物,曼谷,Allied Printers,1990,第56-61頁。
(13)Dhiravat na Pombeja:《阿育他亞王國及其對外關係》,載於《阿育他亞歷史中心》刊物,曼谷,Allied Printers,1990,第109-114頁。
(14)《八十年代的泰國》(《進入八十年代的泰國》修訂本)。曼谷,Editorial Board,1984,第43-46頁。
(15)同上,第53-54頁。
(16)J. M Braga《葡萄牙俘虜筆下的達芒》,澳門,Tipografia Salesiana,1939年。
(17)J. M. Braga,《西方開拓者與澳門的發展》,澳門,Imprensa Nacional:1949年。
(18)Austin Coates,《澳門,歷史的回顧》,澳門文化學會,1991年。
(19)從1628年至1633年,澳門曾有過三位司官。
(20)《印度省》是對從好望角至遠東葡萄牙人統治範圍的稱呼,其權力(政治、經濟、法律等)自1505年起由葡萄牙國王授於印度的副王和總督。
(21)《禮儀之爭》是神職人員之間的衝突:總督和主教反對市議會和耶穌會(1709年)。1720年,這一衝突隨著(教皇克萊芒十一世的)特使梅查巴爾巴的到來而告結束。
(22)《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因禁止售鴉片,中國同英國之間發生的衝突。
在中國,其貿易曾由英國人操縱,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後,向西方強國開放了五個港口,即所謂所《五港通商》,並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人。以往強大的中國在軍事上被打敗後,進入了一個依靠外來勢力,特別是依靠英國的一個時期,這狀況到本世紀才結束。
(23)參閲上一注釋。
(24)《天津條約》,即《第二次英中戰爭》,又稱《鴉片戰爭》後,中國分別同英國、法國、美國和俄國簽定的一系列條約。這些條約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條約,因為上述各國都從中獲得了“最惠國待遇”。
(25)《北京條約》,是於1860年,英法聯軍結束戰爭,進入北京後簽定的。同天津條約一樣,北京條約被認為是第二個殖民條約。根據此條約,中國必須給西方列強更多的特許權,例如:在北京設立外國的外交機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 使各國可直接同皇室接觸;開放更多的港口同外國通商;鴉片貿易和苦力貿易合法化等等。
(26)Gaspar Correia:《印度的傳説》,第二卷,第30章,Porto,Lello&Irmãos出版社,1979年;第26-33頁。
(27)Fernão Lopesde Castanheda:《葡萄牙發現及征服印度史》,第三卷第62章。波爾圖,Lello&Irmãos出版社,1979年:第649-650頁。
(28)João de Barros,“亞洲三世紀”,第二卷第四章。里斯本,Sam Carlos書店;第149頁。
(29)《路易·德·布里托·帕塔林致堂·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的信》,摘自《葡萄牙東方島國傳教團史文件匯編》,Artur Basílio de Sá編輯和注釋,第一卷(1506年-1549年)。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出版社,1954年:第43頁。
(30)Ronald Bishop Smith、《暹邏與1596年前泰族人史》,A. D. Bethesda-Maryland,Decatu Press,1966年第72頁。
(31)Gaspar Correia;《印度的傳説》,第二卷,第二冊第30章。波爾圖,Lello&Irmãos出版社,1975年第381頁。
(32)《紀念偉大的阿豐索·德·阿爾布刻爾克》(從葡文版翻譯),第四卷。紐約,Burt Franklin出版社:1970年,第89-90頁。
(33)《致堂·馬努埃爾副王的信》(馬六甲,1518年8月20日),摘自《葡萄牙東方島國傳教團史文件匯編》,Artur Basílio de Sá編輯和注釋,第一卷(1506-1549):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出版社,1954年:第98-99頁。
(34)同上注釋,第99頁。
(35)João de Barros:《亞洲三世紀》,第二卷第四章,里斯本,Sam Carlos書店,1973年,第150-151頁:“當他按照我們的宗教儀式開始為和平和友誼祈禱時,一個刻有該王國國徽的巨大木製十字架在城中最顯眼的地方豎立起來,以示對和平的紀念和見證。”。
(36)同上注釋,第150頁。
(37)澳門歷史檔案館(A. H. M),民事管理,第106條。296號,“葡萄牙駐暹邏領事的報告”(1881年3月1日)。
(38)E. W. Hutchinson《暹邏17世紀冒險記》,曼谷,D. D. Brooks,1985年:第21-22頁。
(39)W. A. R Wood;《暹邏史》,曼谷,The Siam Barnavich Press,1933年;第98頁。這一日期(1516年同向我們提及的文件中的日期不相符,因為杜阿爾特·科埃略的確是1516年到達暹邏,但他只不過在科欽支那同一起前往中國的多美·皮雷斯的使團遇上了惡劣的天氣。請參閲João de Barros的“亞洲三世紀”,第二卷第四章,Sam Carlos 書店出版,里斯本,1973年:第149頁。
(40)Duarte Barbosa:《東方所見所聞寫真集》Augusto Reis Machado作序和注釋。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1946年;第199-200頁。
(41)Tomé Pires:《東方大全》,Armando de Cortesão作序和注釋。科英布拉,Imprensada Universidade,1978年:第242-243頁。
(42)“路易·德·布利托·帕塔林到副王的信”(馬六甲,1514年1月6日),摘自《葡萄牙東方島國傳教圑史文件匯編》。Artur Basílio de Sá編輯和注譯,第一卷(1506年-1549年)。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954年:第67頁。
(43)João de Barros,:《亞洲第三世紀》,第二卷第4章。里斯本,Sam Carlos書店,1973年:第153頁。
(44)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發現及征服印度史》,第三卷第62章,波爾圖,Lello & Irmãos出版社,1979年;第648頁。
(45)Fernão Mendes Pinto:《東方朝聖》,第189章,波爾圖,Lello & Irmãos出版社,1984年:第545頁。
(46)Hugh Clifford:《遙遠的印度》,曼谷,While Lotus Co,出版社,1990;第87頁。
(47)Prince Damrong Rajanubhab:《傳入暹邏的西方文化》,曼谷,1925年:第107頁。
(48)W. A. R. Wood:《暹邏史》,曼谷,The Siam Barnavich Press,1933年;第98-99頁。
(49)同上,第100頁。
(50)Dhiravat na Pombjera:《阿育他亞王朝及其對外關係》,阿育他亞歷史研究中心。曼谷,Allied Printers,1990年,第109頁。
(51)Hugh Clifford:《遙遠的印度》,曼谷,While Lotuas Co,出版社,1990年;第87頁。
(52)David K. Wyatt:《泰國簡史》,New Haven,Yale Univesity Press,1984年;第89頁。
(53)Manuel de Faria e Sousa:《葡屬亞洲》,第三卷,波爾圖,Civilização書店,1945年;第127頁。需要指出,所舉事件未得到任何證實。
(54)Fernão Mendes Pinto:《東方朝聖》,第188章。波爾圖,Lello & Irmãos出版社,1984年;第525-526頁。
(55)João de Barros:《亞洲第三世紀》,第三卷第二章。里斯本,Sam Carlos書店,1973年,第248-259頁。
(56)W. A. R. Wood:《暹邏史》。曼谷,The Siam Barnavich Press,1933年;第102-103頁。
(57)Diogo de Couto:《亞洲第六世紀》,第七卷第9章。里斯本,Sam Carlos書店,1974年:第128-129頁。
(58)David K. Wyatt:《泰國簡史》。New Haven,Yale Univesity Press,984年;第100頁。
(59)同上,第103頁。
(60)W. A. R. Wood:《暹邏史》,曼谷,The Siam Barnavich Press,1933年,第128頁。
(61)Bernard P. Groslier:《葡萄牙人及西班牙筆下的十六世紀柬埔寨吳哥城》。巴黎,Presses Universitairse de France,1958年,第38-39頁。
(62)António da Silva Rego:《葡萄牙東方傳教團史料匯編-印度》,第九卷。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1953年;第539頁
(63)同上-注釋,第七卷,第458頁。
(64)Pe. Manuel Teixeira:《葡萄牙在泰國》。澳門,Imprena Nacional,1983年:第281頁。《以精神征服東方》,第三部份。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7年:第439頁。
(65)同上注釋(37),第九卷,第539頁。
(66)Fr. Dalup da Trindade:《以精神征服東方》,第三部份。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7年:第439頁。
(67)同注釋(37),第七卷第416頁。
(68)同注釋(41),第440頁。
(69)同注釋(41),第464頁。
(70)António da Silva Rego:《傳教學課程》。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1956年;第584頁。
(71)Father P. Cerutti,“泰國的耶穌會傳教士”,S. L. ,S. d. ,第3-4頁。
(72)同注釋(37),第七卷,第465-466頁。
(73)Pe. Manuel Teixeira:《葡萄牙傳教團在暹邏》,摘自澳教區基督教報,第60卷,第696期,1962年4月:第338-339頁。
(74)同注釋(45),第584頁。
(75)António da Silva Rego:《傳教學課本》。里斯本,社會政治科學研究所刊物,第56期,1961年,第174-175頁。
(76)同上,第175頁。
(77)W. A. R. Wood:《暹邏史》曼谷,The Siam barnavich Pfress,1933年;第159頁。
(78)同注釋(37),第七卷,第462-463頁。
(79)同注釋(48),第330頁。
(80)Rong Syamananda:《泰國史》,曼谷,Taiwatana Panich,1990年,第70頁。
(81)António da Silva Rego:《葡萄牙東方傳教團史料匯編-印度》,第七卷。里斯本,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1953年:第463-464頁。這位“小人”是一位有權勢的摩爾人,他曾經給巴加朗(Barcalão)帶來巨大災難,但他卻加禍於葡萄牙人,他們給暹邏带來災難;據暹邏人供認,他曾向教會內部派遣過間諜。
(82)Ronald Bishop Smith:《暹邏與1596年前泰族人史》,A. D. Bethesda-Maryland,Decatur Press,1967年:第31-32頁。
(83)同上-注釋,第37-38頁。
(84)Charles Boxer:《光復時期的弗蘭西斯科·維埃拉·德·菲蓋雷多和馬薩加與渧汶的葡萄牙人》(1640-1668),澳門,Escola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Salesiano,1940年;第16頁。
(85)同注釋(55),第77頁。
(86)Fr. José de Jesus Maria:《亞洲的中國與日本》,第二卷,Charles Boxer注釋。澳門,文化學會及澳門海事研究中心,1988年:第103頁。據Bryan Souza記載,佩德羅·瓦斯·德·西蓋拉被皇室和澳門市議會選中,作為澳門派往暹邏的信使,他的主要使命是要建立通商(但他沒有達到此目的)。摘自George Bryan Sousa的《帝國的幸存:在中國的葡萄牙人(1630年-1754年)》,里斯本,D. Quixote出版社,1991年,第63頁。
(87)“議會議員們開會對在季風季節來到該城的帆船和暹邏國王的貨品做出了決定。”摘自A. M. 第二系列,第一卷第二冊,1941年2月13日版,第73-74頁。
(88)同上,第73頁。
(89)“議會議員們和本市港務局的官員開會就兩只將要開進本島港口一事作出決定,他們説是邏國同柬埔寨港進行戰爭的船。”摘自A. M. 第二系列,第一卷第3冊,1941年4月15日版,第153-154頁。
(90)“鑑於暹邏發生革命,有了新的國王,議會議員討論向暹邏王國派船是否適宜。”摘自A. M. 第二系列,第一卷第五冊,1941年9月10日版,第275頁。
(91)“1720年澳門寫給暹邏的信”,摘自A. M. ,第一卷第三冊,1929年8月版,第51頁。
(92)Joaquim de Campos,《暹邏商站(2)》澳門教區基督報,第35年,1938年5月第410期,第872頁。
(93)澳門歷史檔案館“民事管理”第六箱,第296號卷宗,《葡萄牙駐暹邏領事安東尼奧·弗·馬克斯·貝雷拉的報告》(1881年3月日)。
(94)Pe. Manuel Teixeira:《葡萄牙傳教團在暹邏》,摘自澳門教區公報,第七十卷,第703期,1962年11月,第931頁。
(95)《遠東曼谷第八屆醫學大會文件匯編》,澳門檔案館,第四系列,第七卷第1.2冊,1987年1月/12月,第64頁。
*Leonor Seabra,歷史系畢業,澳門大學葡萄牙與亞洲史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