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化哲學提出一個重要命題: “文化發生: 人的類本質的形成和體現”,其基本原理有三:1)勞動創造了人,這既導致了人區別於動物的匱乏性,又為人創造了克服這一不足的特殊的遺傳基因,為人類自由自覺的文化創造提供了重要的生理基礎;2)文化的發生和勞動創造人的進程相伴而行,可供自由驅使的語言象徵符號的產生是人的自由自覺的類本質形成的根本標誌,是人類文化發生的契機;3)文化的發生是人類自由自覺的類本質的體現,外在自然的人化與內在自然的人化的互相推移,使人類從動物的“兩種生產”中提升出來。(1)這就是説,文化發生的過程,是人在勞動中的自我產生的過程,是人的自由自覺的類本質的形成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通過勞動的實踐,使“人化的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的人化”互相推移,並創造了可供驅使的語言符號系統,使自身得以通過這一中介將自身從動物的勞動轉化為人類的勞動,從動物的群體關係轉化為人類的社會關係,從而把自身從動物的“兩種生產”中提升出來,作為文化的動物出現在世界上。
由於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所面對的現實的存在對象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人類生存的前提,亦是文化創造的前提。人類是在與自然的現實對象化關係中、在這種關係的動態發展中創造出文化來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有著人對自然的投射,而且有著自然對人的投射--在人的對象化活動中,自在地起作用的自然界仿佛是自為地塑造著人、人類和人類的文化。這樣,自然地理環境不能不對人類文化的形成、發展、演變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在人類文化的發生期,尤為巨大。它突出地表現在人類產生到特定文化類型形成的整個過程中。因此,在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和對中華文化現代的探討中不能不要涉及這個問題,特別是在考察中西文化的發生及其後來不同的發展路向和特點時更不能漠視這個問題。
鑒於此,本文擬通過對中西文化發生時所依托的自然地理環境的考察,來弄清二者的地理環境類型,重點是試圖論證屬於“大陸型”的中華文化並不是“封閉型”文化,而恰恰是一種“開放型”文化,有良好的“以我為本,兼收並蓄”的兼容機制,因此中華文化的現代化是在兼容東西方古今文化過程中的對自身傳統的現代化,絕不是甚麼“以蔚藍色文化取代黃土文化”。
中華文化的自然地理環境考察
地圖顯示,中華文化所賴於發生、發展的華夏大地是一個東面瀕臨茫茫滄海、西北横亙漫漫戈壁、西南聳立著世界屋脊而內部又是以黃河、長江流域遼闊平原相毗連的地形地質複雜、氣候氣溫多樣、水系縱橫交錯的廣袤疆土。這樣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在創造中華文化時難於超越華夏大地向外開拓,然而內部又有廣闊的天地可供回旋。因此,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先民們在這片華夏疆域內對自然進行“人的對象化”活動的結果,也是這片疆域的自然地理環境對其居民塑造的結果,是自本自根的。
不過,由於這片廣袤疆域內的地形地質的複雜和氣候氣溫的多樣,居住在不同地區、不同地域的中華民族先民所面對的自然地理條件不盡一致,因此,在文化發生之初他們在各自的活動範圍裡創造出適應不同自然地理環境的集團的、部族的文化。據考古學,自公元前6000餘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華夏大地上已形成了以關中、晉南、豫西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中游文化區,以泰山為中心的黃河下游文化區,以太湖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下游文化區,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中游文化區,以燕山為中心的燕遼文化區,以甘肅青海為中心的黃河上游文化區,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軸的華南文化區以及北方狩獵漁獵文化區等(2)。這些文化區既是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先民對自然的對象化結果,又是這些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對他們的塑造結果。這些不同的文化區並非完全隔絕,相反,由於文化的本質就是開放的,衝破隔離是文化發展的絕對要求,因此,這些在各自地域內所發生的文化,都在以當時所能獲得的手段和所允許的方式自在地進行交流,以致釀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和文化大融合的時代--先秦,構成了夏夷對舉的格局,塑成了夏商周三代的五大民族集團及其文化,即居於“中國”的以夏商周三族復合而成的華夏族集團及其文化和東夷族集團及其文化、北狄族集團及其文化、西戎族集團及其文化、南蠻族集團及其文化,這些集團及其文化最終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華夷五方相配而又統一於“天子”的政治模式。後來又經歷了秦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遼宋金夏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並在元明清確立了當代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格局。可見,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既是自本自根的又是多頭淵源的。
不少學者從自然地理環境和中華民族先民的“雙向投射”關係上,將上述諸多文化區形象地歸結為源於“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對立互補。“小米文化”以仰韶文化為代表,其分佈區域是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帶。這一帶氣候乾寒,雨量不多,地表多半是由數十萬年來由戈壁吹來的黃沙覆蓋而成,其土質結構鬆軟多孔,有較強的滲水性,遇到雨水,可以像海綿一樣對水起保存作用。水份滲入深處,蒸發緩慢,不僅能長期保存,而且能在乾旱季節,由地下經植物毛細管供給植物所需水份,與此同時,黃土風化程度較弱,顆粒中所含礦物質不易流失,具有較強的肥力。正是在這樣乾寒的環境中,居住在這一帶的中華民族先民培植了耐乾寒的小米,創造出了“小米文化”、“稻米文化”主要包括華東沿海的河姆渡文化和江漢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等。這一地區地勢低窪,氣候濕熱,雨量流沛,適合於需要較多水份的稻米生產,於是居住在這裡的中華族先民便培植了“稻米文化”。總之,中華文化之“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的出現,充份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先民在創造文化過程中同自然界的“雙向投射”關係,充份説明了自然地理環境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制約關係。
問題還在於這些相對獨立的不同部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是如何匯合成蔚為大觀的中華文化的呢? 自然地理環境在這過程中發揮了甚麼作用呢? 對此,錢穆先生是這樣分析的:
古代中國文化環境實與埃及巴比倫印度諸邦絕然不同。埃及巴比倫印度諸邦,有的祇藉一條河流,和一個水系,如埃及的尼羅河。有的是兩條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倫之底格里斯與阿付臘底河,但其實祇好算一個水系,而且又是很小的。祇有印度算有印度河與恆河兩流域,但兩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簡單,沒有許多支流。祇有中國,同時有許多河流與許多水系,而且是極大和極複雜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許多等級。如黃河長江為第一級,漢水淮水濟水遼河等可為第二級,渭水涇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則為第三級,此下還有第四級第五級等諸水系,如汾水相近有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灃水鎬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國古代史上皆極著名。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似乎先在此諸水系上開始發展,漸漸擴大蔓延,彌漫及整個大水系。……祇有中國文化開始便在一個複雜而廣大的地面上展開。有複雜的大水系,到處都有堪作農耕憑藉的灌溉區域,諸區域相互間都可隔離獨立,使這一個區域裡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適合的濃度,再一面又得四圍的天然屏障而滿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則極適合於古代社會文化之醞釀與成長。但一到其小區域的文化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又可藉著小水系進到大水系而相互間有親密頻繁的接觸。因此中國文化開始便易走進一個大局面,與埃及巴比倫印度,始終限制在小面積裡的情形大大不同。(3)
可見,華夏大地的多水系所造成的天然屏障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多源頭、多方位和多根系,同時也正由於有了這些水系才使到在各區域內自行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各種“次中華文化”得以匯合並綜合成一個整體--中華文化。究其原因,就在於華夏大地這諸多水系是被隔在東海之內、戈壁之下、“屋脊”之側的,因此在發韌之時中華文化是難於跨越這些環繞四周的屏障向外拓展的,於是祗好努力向內,不斷地對華夏大地之內的各區域、各部族文化進行融合與綜合,從而出現了前述的先秦時期的第一次民族的文化的大融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相對獨立的各區域、各部族文化在融合的過程中並非漫無中心的,各次文化有各自的中心,而就中華文化的整體融合而言也有中心。這個中心,有的學者認為,就是龍山文化。這也就是説中華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與大綜合,一方面是龍山文化對周邊文化的不斷攝取,另一方面又是龍山文化對周邊文化的不斷輻射,並最終鑄成了中國式的農業文明。這一文明,以“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為其兩翼,以求人與自然的高度和諧即“天人合一”為其精神。
從此,中華文化便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地在更大範圍內進行文化的離析與整合,以致生生不息、綿延不斷。
總之,中華文化憑藉著廣闊的大陸沃野在中華民族先民們對自然的人化和自然對中華民族先民們的類化中產生與成型,它自本自根、多源匯合、獨立發展,是一種以“我”為本、一以貫之的文化,具有強大的攝融力、凝聚力和輻射力。在這一攝融、凝聚和輻射的過程中,其外延逐漸擴大、內涵日益豐富,樣態也不斷“現代化”,而根本精神卻始終不變。因此,雖源遠流長卻萬世不衰,雖兼收並蓄卻獨樹一幟,雖數歷逆境卻化險為夷,成為人類文化史上少的有古有今、隨遇而安的文化。
西方文化的自然地理環境考察
人們祇要翻開世界地圖冊稍加比較即可發現,作為西方文化發生之地的愛琴海區域,其自然地理環境同華夏大地大相徑庭。
愛琴海區域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以及小亞細亞半島西海岸地帶。在這塊不大的地區中完全看不到有像黃河、長江那樣的大水系,然而海陸交錯,山巒重疊。它和海的關係密切,海洋佔了其中大半的面積。希臘半島算是其中一塊較大的陸地了,但它東臨愛琴海,西接愛奧尼亞海,南對地中海,全半島除北部外沒有一處是離開海洋50公里以上的,而且海岸線曲折。愛琴海中則島嶼星羅棋布,總數多達480餘個,就像跳石那樣密佈在海面上。其間的最大島--克里特島位於愛琴海南端,橫臥於地中海中央。由此往東可達兩河流域文明區的腓尼基等地,向南可至尼羅河文明區的埃及,朝西可至西西里島與意大利,向北可達希臘半島,還可穿過愛琴海再通過赫勒斯滂海峽(今之達達尼爾海峽)進入普羅彭提斯海(今之馬爾馬拉海),而後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可達黑海。在陸地方面,面積本就不大的希臘半島還被西北部的品都斯山和東北部的奧林普斯山、中部的巴那撒斯山、南部的太吉特斯山分割成三大塊及許多小塊塊,其間沒有大河所沖積而成的廣大沃野,祇有一些不大的平原,可耕面積非常有限,加上夏季少雨,其農業遠不及東方古國發達;克里特島地勢雖較平坦,也有一些小河流,而且氣候滋潤,比較適宜農業發展,但畢竟面積非常有限,全島東西寬祗有250公里左右,南北長也祇有12至60公里左右。這一區域雖產有小麥、大麥、豆類等,但不能自給,還得以所盛產的橄欖、葡萄以及大理石、陶土、金屬礦產等同埃及、黑海沿岸地區換取糧食。
由於內部無回旋餘地,古希臘人不能不要走向海洋;由於糧食不足,古希獵人不能不要以本身的物產去換取糧食;而愛琴海夏季的風平浪靜又為他們的揚帆出海開展對外貿易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不但維持了希臘先民的生存繁衍,而且促進了與非本土文化乃至異類文化的交流。因此,作為古希臘文化源頭的米諾斯文化和邁尼錫文化並非是單純的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綜合,其間無不折射著尼羅河流域文化和兩河流域文化影響的印記,甚至包容了這些文化的因素。質言之,古希臘文化正是在希臘本土文化同非本土文化乃至異類文化的交流中而日臻定型、成熟,並於公元前11至9世紀構成了史稱為“荷馬時代”的最繁榮最鼎盛時期。
古希臘文化在不斷攝取域外文化和異類文化的同時,也不斷向外輻射並影響於其周邊地區。這一影響在荷馬時代或伴隨著移民浪潮或伴隨著軍事擴張而日益加強,最終導致了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化”。其最典型者,莫不過是意大利半島的“希臘化”及古羅馬文化的發韌。
意大利半島的自然地理環境同希獵半島差不多而各有千秋。它三面環海,東為亞得利亞海、南為愛奧尼亞海、西為第勒安海,均與地中海相接。該半島河流要多於希臘半島,古羅馬城就建在第伯河南岸。東部依山傍海,適宜畜牧;北部肥沃的波河平原,西部、南部以及西里里島上的一些平原,土壤肥沃,宜於農業。該半島氣候良好,雨水充足,不僅可以栽種橄欖和葡萄,而且能夠培植大麥、雙粒小麥、小麥等,西里里島以盛產穀物著稱。因此,公元前8世紀,意大利的農業、手工業已相當發達。隨著軍事征服,特別是羅馬稱霸地中海後,其海外貿易也得到長足的發展,其商人足跡遍及提洛島、巴爾幹、小亞細亞與高盧。由於羅馬的海灣可以出入當時最大的船舶並建有最大的商品倉庫,也吸引了各地的商人雲集羅馬,這不但使羅馬成為意大利內外貿易的中心,而且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匯的中心。古羅馬文化正是在古代意大利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了伊達拉里亞文化、兩河流域文化、特別是古希臘文化而成熟並繁榮起來的。史稱,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向西里里島與意大利南部大量移民,建立了敘拉古、他林敦、庫米等移民城邦。這些移民帶來了管理葡萄園、培植橄欖的技術以及手工業方面的生產技術,而且也帶來了古希獵的文學、藝術、哲學、宗敎等,從而促使了古羅馬文化的“希臘化”,並同古希臘文化一起成為西方文化的奠基石,不僅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發展格局與運行機制,而且共同創造了西方世界的文明。
顯而易見,與中華文化是不斷對境內各地域、各部族文化進行融合綜合、在攝融凝聚中逐步擴大其輻射範圍、又在更大範圍內進行新的融合、綜合不同,西方文化是在不斷地同外來文化包括異類文化的交流中,通過大量吸收外來文化因素來對原有文化進行重新整合乃至被取代的一種過程和結果,而這差異歸根結底是自然地理環境制約所致。
大陸型文化不等於是封閉型文化
不少論者認為,中西文化發生時所依傍的不同自然地理環境終於將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分別塑成了大陸型文化與海洋型文化。就前述的中西文化發源地之自然景觀而言,此論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有的持論者把大陸型文化等同於封閉型文化而把海洋型文化等同於開放型文化。
前已有述,中華文化是多源頭、多方位、多根系的,它一開始就是以“我”為本地、滾雪球似地、不斷地同周邊文化進行交融與綜合,其結果是構成了“小米文化”和“稻米文化”的對立互補。這是就主要糧食產品、生活資料而言的。若就水系來看,實際上是以黃河文化為中心的長江文化、遼河文化、珠江文化的兼容結果。若就考古發掘到的古代文化遺址之地理位置來作進一步歸納、則有六大文化區,即中原文化區(仰韶-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交融綜合結果)、吳越文化區(馬家濱文化、良諸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交融綜合結果)、湘楚文化區(以屈家嶺文化為其濫觴)、巴蜀文化區(大溪文化的發展結果)、東北文化區(以遼西文化為其代表)、嶺南文化區(以石峽文化為其代表)等。當然,古代中華文化不僅僅這六個文化區,其它諸如內蒙、甘肅、青海、新疆、雲南和西藏等地有相應的文化區。不過,從大處著眼並有確鑿的考古事實為憑據的,這六個大文化區在中華民族進行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時代已經形成,其文化已經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最基本架構。此後的中華文化正是這些文化區的文化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長期交融綜合的結果。所謂以“我”為本,就是以中原文化為本。因此,中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中原文化之所以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盛邦和先生提出了五大論據: 其一,中國最著名的原始文化叢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都產生於中原地區;其二,夏、商、周等中國古代文明都無一例外地誕生在黃河之濱與黃土高原上,而且中原地區一直是中國文明史演變的主要舞台;其三,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亦誕生在中原地區並演化成現代漢字;其四,中國古代的大規模統一戰爭的主要戰場是在中原地區,“吞併六合”而統一中國的政治力量秦國屬於中原文化系統,後又“漢承秦制”,繼承並弘場了中原文化的傳統;其五,古代中原地區集中了“天下”的大部份人口與財富;因此,中華文化雖然是多元組合而成的,但其核心祇有一個,即中原文化。(4)
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陳正祥先生從自然地理環境上如此解釋道: 第一,黃土高原東南部黃河各支流的河谷,特別是兩岸的河壩,因為高出河流的洪水線,近水而可避水害,又比較易於防禦,常被中華民族初民選為聚落地址;第二,原生黃土有垂直的節理,便於穴居,而其顆粒均匀,疏鬆易碎,性能肥沃,又適宜原始農耕;第三,黃土高原東南部的雨水集中於夏天,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5)盛邦和先生還從人種源地上作了補充説明。他根據中國人種是由北方人種(蒙古人種)和南方人種匯合而成的理論認為,北方人種源地在中原、華北一帶,恰好與黃土、黃河地區相接近,甚至相疊,因此使到這一地區人口集中,並形成文化中心區的地位;相反,長江流域地區一方面距離北方人種源地較遠,另一方面又與南方人種源地即印尼爪哇等地相隔重洋,以致無法成為人口密集區;而文化是人創造的,與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區相比,人口稀疏的長江流域地區自然無法成為中心文化區。(6)
有必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即使是中原文化自身,也是複合而成的。這明顯地體現在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融合上。傅斯年先生1934年在其<夷夏東西説>中就指出: “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這一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體系。這兩個體系,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7)這也就是説在中國古代史上最早的三個朝代,其先來源不同,分屬東西兩大部落集團。先是夏商的對峙而商滅夏,並促使了兩部族文化的融合;後是周與商的對峙而周滅商,從而將東西兩系合一,並進一步推動了東西兩大部族及其文化的融合。由於周本身是由山西南部西遷的一支夏人,“夏”又有“雅、正”之義,於是周完成黃河中、下游的統一大業後,仍以“夏”為其所復合而成的新的更大的部族的族稱;由於周朝崇尚赤道,“華”含有“赤”之義,於是凡遵守周禮尚赤的地區和部族,均稱之為“華”;二者統稱“華夏”,這意味著周代以後是以夏文化為中心在更大的範圍裡展開了華夏文化,亦即中原文化的復合。由此也產生了所謂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經·大雅·民勞》)這樣的“中國-四方”概念。盛邦和先生認為,這個概念在無意中卻道出了中華文化區的“內核”和“外緣”的二重結構特點,並圖示如下: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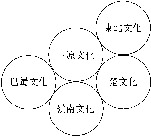
無庸置疑,這種概念是一種“華夏文化中心主義”,並導致了是“以夏變夷”還是“以夷變夏”的“夷夏之辨”以及“尊王攘夷”的政治會盟。然而,不論主觀意圖如何,既然要“綏四方”、要“以夏變夷”,就不能不進行文化交流,有交流就肯定會發生文化的新融合與新綜合。當然這種新融合與新綜合依然是以華夏文化亦即中原文化為核心。(9)因此,到了戰國時期,被視為戎蠻的秦楚,與三晉、燕、齊並列七雄,同稱中國與華夏,均是以當地華夏文化為核心並各自融合了夷、蠻、戎、狄等的文化而成為各區域的文化中心,並最終導向秦滅六國統一中國的政治結局。在文化上則在吸收不少來自西北和北方遊牧部族的文化因素的同時,第一次實現了北方旱地農業文化(小米文化)與南方水田文化(稻米文化)的交融與綜合,最終達到了秦漢文化--秦漢時期之中華文化的高度統一。
可見,由於文化自身的運作規律,特別是文化交流的雙向性,“華夏文化中心主義”並沒有導致中華文化的封閉性。中華文化恰恰是以中原文化為中心與周邊文化進行著不斷的交融與綜合,並不斷擴大自身的主體及其輻射範圍。如此循環往復,以至其輻射範圍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能夠超越了當今中國的疆界,而其主體內涵秦漢時期是“夏中有夷,夷中有夏”,宋明時期是“儒釋道三合一”,近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代則是“土洋並舉,洋為中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試問這樣一種文化是封閉性文化嗎? 封閉性文化能夠這樣隨著交流範圍的擴大和時代的變遷而不斷地兼容並蓄嗎?
當然,在中華文化與周邊文化以及後來的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的交融綜合中,其文化結横的內核或曰基本精神--“天人合一”宇宙觀始終被堅持著。一切外來文化,凡有與此相抵觸,都會引起激烈的文化衝突、引起國人的熱烈討論;而且不論有些國人自近代以來如何“恨鐵不成鋼”而疾呼諸如“全盤西化”一類的口號,並且往往搞得沸沸揚揚好生熱鬧,然而一旦塵埃落定,人們卻發現中華文化依然是中華文化,祇不過其間已有機地兼容了不少外來文化因素,以致綿延至今。與此同時,人們也不難發現,凡不尊重中華文化基本精神的所謂“吸收”、“兼容”,雖然在一定時期裡風行一時,但最終都被中華文化給過濾掉了,能夠在華夏大地真正扎根開花結果的,都是那些能夠與中華文化基本精神兼容的或曰能為中華文化基本精神所改造的部份,而且與中華文化結合得水乳交融,難以離析。古時傳入的印度佛敎,祇有能“中國化”的敎派才得以扎根開花,便是典型的一例;今時引進的音譯詞大多被意譯詞所取代又是一例。於是,有人以此認為中華文化實在是太封閉了。我們恰恰認為,這並不能證明中華文化的封閉性,祇能説明中華文化具有良好的兼容運作機制。因此,當它在時代性上領先於世界文化時能夠自覺地吸收外來文化;當不能領先時,特別是受到外來文化強大的衝擊時,又能在堅持自身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進行自我調整,雖然這種調整有時(特別是近代以來)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地步;因此,能伴隨著時代前進的步伐而不斷的“現代化”,雖然有時這種“現代化”的進程在某些急功近利的國人看來是“蝸牛爬行”! 然而,文化內在的運作機制作為相對獨立於某個人或某些人之外的一種客觀存在,是有其自身規律的,當它確實需要慢的時候自然就慢。無數歷史事實已經證明,行政干預往往難於奏效,急於求成往往適得其反,這就是古代哲人所謂的“欲速則不達”吧! 試想,要是按照當年狂熱的“全盤西化”論者的方案,把漢字取消,代之以拉丁字母,還需要討論甚麼漢字的現代化嗎? 還會有今天的中文電腦嗎? 還會出現詞語電腦輸入速度要快於拉於字母輸入法的方塊漢字輸入法嗎? (10)擴而言之,中華文化還會存在於今天的華夏大地上嗎? 可見漢字的現代化祇能是漢字本體的現代化,取消了漢字也就無所謂的漢字現代化可言! 漢字作為“中國文化的脊樑”(11),其現代化的道理是如此,其它中華文化要素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現代化道理也莫不過如此! “全盤西化”論者的最大失誤也就在於欲求丢棄本族文化之本體來實現所謂的現代化。暫且不論這種丢棄簡直就像某人欲扯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一樣不可能,即使是能夠實現所謂的現代化,也已經不是中華文化本身的現代化了。在我們看來,中華文化那種以“我”為本的堅持自身基本精神的兼容機制,並不能作為中華文化是大陸型文化因而是封閉性文化的根據。相反,這是任何仍有生命力的文化正常的運作機制。更難能可貴的是,中華文化的這種機制在它自身的時代性不能領先於世界文化時還能運作,這既表現出中華文化堅韌的生命力,也是它能夠成為如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古有今的屬於十幾億人的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試想,一種封閉型文化會有如此的功能嗎?
海洋型文化也不全是開放型文化
西方文化,不僅從其發源地愛琴海區域,而且從它首先覆蓋的歐洲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上看,都呈現出同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及其後來所覆蓋的區域--中國大陸迥異的樣態。例如,南歐巴爾幹半島、亞平寧半島、伊利亞半島和附近島嶼,西歐的英國、愛爾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北歐的日德蘭半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帶和冰島,以及中歐、東歐部份,無不同愛琴海區域一樣,即河流短小湍急,缺少廣闊的流域平原,但海岸曲折而多良港,以致歐洲人很早就向海外拓展,並在這過程中創造和發展了西方文化。這種文化被形象地稱之為海洋型文化,本也無可非議,但如果將它完全等同的開放型文化卻有失偏頗。
前已有述,這種海洋型文化比起大陸型文化是能在其形成、定型過程中較早地接觸到域外文化、異族文化甚至是異類文化,因此,可以這麼説,它的成型本身就是本土文化與域外文化、異族文化、異類文化交融綜合的結果。這似乎要比大陸型文化“開放”。於是乎,一些論者就簡單地將海洋型文化等同於開放型文化。其實,這種看法完全忽略了任何文化都具有兼容性又有排他性的屬性,而認為海洋型文化只是兼容不排他。其實,海洋型文化在一定時期裡也會表現出極端的排他性。
文化學原理告訴我們,文化的排他性主要是自然的文化隔離機制與人為的文化隔離機制所鑄成。高山、江河、沙漠、大海構成了文化隔離的天然屏障,形成了自然的文化隔離機制;在人為的文化隔離中則包括了經濟的、政治的、精神心理的等方面的因素。此外,一種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類型文化定型之後,其發展會有“文化慣性”,這種慣性本身就有排他性。應該進一步指出的是,文化隔離機制同世間萬物一樣也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促成了相對獨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異類文化並自成系統地進行運作,從而使人類文化顯得五彩繽紛,也使人類世界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類型文化又往往具有排斥域外文化、異族文化和異類文化的本能,從而妨礙人類間各種文化的正常交流。文化的排他本能,有的表現為以主流文化或本土文化去兼容、消融非主流文化、外來文化;有的則表現一種外來文化去消滅、取代另一種本土文化。前者表面上是一種排他,實質上是一種開放的表現,中華文化在許多情況下即表現為這種“排他式的開放”;後者才是徹頭徹尾的排他,西方文化在許多情況下即表現為這種“取代式的排他”。例如,古希獵文化雖然是由古代歐、亞、非諸種文化因素融合而成,但卻是以米諾斯文化和邁尼錫文化的湮沒為代價的;到了中世紀,古希臘文化本身也沒有逃脱澌滅殆盡的命運而為敎會的加洛林文化所取代,致使歐洲進入了世稱的“黑暗的世紀”。文藝復興之後,西方文化日趨興盛,隨著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泛濫,西方文化日顯其文化霸權主義和極端的排他性。例如,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打著“神聖十字軍”的旗號,以殘酷屠殺的手段完全征服墨西哥之後,便派遣一批傳敎士到了那裡,摧毀了當地的幾百所神廟,建立起天主敎堂,把保存了上千年的阿森提克文化古蹟、印第安人歷史文獻全部毀滅,以消滅瑪雅人原有文明,迫使當地人民改信天主敎,放棄本民族的各種神祗。又如,在非洲、西方人也直接向哪兒強行輸入西方文化,致使非洲文化產生兩種反常現象,一是把歐洲文明直接帶給非洲,使歐洲在漫長的歷史階段裡所形成的西方文化極大地推動著非洲的開化、文明與發展;二是由於運用行政手段強力推行西方文化,壓抑了非洲本土文化,扼止了它的正常發展與健康成長,造成了許多口頭傳説、口傳文學由於當地語言為英語、法語等歐洲語言所取代,便隨著最末一代老人的離去而消失。非洲從此失去了一筆可觀的文化遺產。西方文化這種先是自相“殘殺”後是文化霸權的運作機制,表面上頗為“開放”,實質上是如此不容人,哪裡還有兼容的影子呢? 因此,我們認為,海洋型文化並非何時何地都是開放的,海洋型文化與開放型文化之間沒有天生的固定不變的等號。這裡的關健是,“走向海外”和“開放兼容”分屬於不同的概念範疇,前者是就文化輻射態勢而言,後者是就文化發展機制而言,務必分清。
綜上所述,不論是大陸型文化還是海洋型文化都具有開放性和封閉性這二重性,這是任何相對獨立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類型文化的天生屬性。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並不在於封閉性和開放性上,而在於它們自身內部的不同運作機制及其與異類文化不同交流方式,這是由這兩種文化發生、發展時依托著不同的地理環境所塑成的。中華文化雖然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由於種種原因,曾表現出“夜郎自大”而“拒外”“排外”,近代以後在時代性上也出現過並至今尚未徹底解決的落後於世界文化時代潮流的現象,但經過百多年來的自我調整,如今已顯露出新的生機。這再一次地體現出它那以“不變應萬變”為核心的發展機制的良好狀態和無限生命力。因此,中華文化的現代化是一種在兼容古今中外文化過程中對自身傳統的現代化,而不是拋棄自身傳統的以一種外來文化的移植或取而代之的現代化。我們深信,21世紀的中華文化將是兼容更多的世界文化因素而又更具中華民族傳統特色的文化。
【註】
(1)詳細的論證,參閱許蘇民《文化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62-72。
(2)更為詳細的論證,參閲陳連開<中華文化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載陰法魯、許樹安主編《中國古代化史》(1),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41。
(3)引自《中國文化導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頁4-5
(4)引自《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學林出版社,1988,頁51-52。
(5)(6)轉述自注(4)所揭書,頁53。
(7)見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35年版,頁1035;轉引自注(2)所揭書頁20。
(8)見於注(4)所揭書,頁53。
(9)不僅是古代而且是近、現代,這種交融與綜合為何是以中原文化(後是中華文化)為核心,而且許多周邊文化是自願向中原文化(後是中華文化)認同,這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有待於作深入的專題研究。
(10)近年來,我國的科技工作者已成功地將漢字分解為基本的筆型單元。經過試驗,字型的輸入比英語更快。因為每個漢字平均擊鍵只需2.8次,而英語每個字母需擊鍵1次,絕大多數英文單詞字母都在4個以上。
(11)L. R. 帕默爾語。引自《語言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3,頁99。
*楊啟光,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敎授,文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