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發現者飛船能夠證明傳説中的不明飛行物、星際漫遊、“第三類接觸”的存在,又或者能夠證明外星人存在於本銀河系的不知名星球或其它有待發現的銀河系,世人的反應將會如何呢? 我們如何將這些外星人分類呢? 他們會否受歡迎呢? 他們會否得到如我們地球人一般的平等的待遇呢? 他們會否與我們分享一切事物?15和16世紀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將回教徒從13世紀以來他們一直統治的伊比利亞半島逐出,並在隨後的“發現年代”裡,發現一個“新世界”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沙勿略生平及耶穌會在印度最虔誠傳教士業績
由該會路賽納編輯 里斯本
PedroCrasbeack印刷 1660
選自《大三巴遺蹟:永垂青史的紀念碑》頁135
沙勿略生平及耶穌會在印度最虔誠傳教士業績
由該會路賽納編輯 里斯本
PedroCrasbeack印刷 1660
選自《大三巴遺蹟:永垂青史的紀念碑》頁135
大約從1418年起,葡萄牙人在航海家亨利王子(1390-1460)、約翰王二世(r.1416-1495)及其繼承人的指引下,為歐洲人發現了撒哈拉沙漠南面的非洲大陸,並且繞航非洲南端(他們稱之為“痛苦之角”,後來被委婉地叫作“好望角”),於1498年到達印度。同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開始他第三次向屬於西班牙的“新世界”航行,這是他於1492年為卡斯提爾國王發現的。當時國王要求向西航行,尋找海路到印度。(1)
教皇們支持這些航行,因為在他們的歷史裡曾有過十字軍東征,而且,他們宣稱,所有至今未被基督教王子佔領的土地都分別為葡萄牙和西班牙君主不可侵犯的財產,並在這些地區給予這兩國貿易專利。
在這些新發現的早期,這兩個基督教國家垂涎東印度群島。因此,為避免衝突,他們請求教皇干預邊界的劃分,這樣統治的範圍就能清楚和正式地界定,因而有1493年5月3、4日的教皇訓諭。然而,1494年的特爾德西拉斯條約,規定了新的邊界並得到教皇的同意而替代了1493年的協定,雙方都誓言要在各自新發現的土地上宣揚基督教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東印度羅馬區保護權就是來源於這些特權。(2)
因此,葡萄牙能作出新努力,在這些判歸給她的領土上建立強有力的統治。1498年3月1日,當華士高·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莫三比克遇上第一艘載滿印度貨物的阿拉伯船的時候,葡人又有了新動機去繼續探險和擴張:通過香料買賣牟利。然而,盈利並不能替代十字軍精神,祗能將其淡化。當非洲的障礙已經清除,印度就在眼前的時候,葡人仍有必要在其全盛時期保護他們的成果,以防回教徒的破壊(3)在近東和地中海流域發生的事件可為此作證。16世紀初,土耳其人贏得威尼斯,使這個依靠與東方回教世界進行傳統貿易的歐洲商業都市日漸式微,並打開土耳其人進入歐洲中部的通道。
 Gaspar Castner關於在上川島建立沙勿略信徒東方大墓地的記載(1770年)
1700年Castner於上川島督促修建了一座小教堂
沙勿略神父1552年於該島謝世
Gaspar Castner關於在上川島建立沙勿略信徒東方大墓地的記載(1770年)
1700年Castner於上川島督促修建了一座小教堂
沙勿略神父1552年於該島謝世
要從印度到達非洲,葡人要依靠阿拉伯回教徒。1498年,伽馬從馬里多(肯亞)沿著馬拉巴海岸航行到卡利卡特,船隻由阿拉伯舵手阿曼特·伊賓·馬俊(AhmadibnMajin)駕駛,因而葡人能夠到達印度,而在他們眼前的是東亞的大海。(4)然而,與東方進行傳統貿易的航道仍然操縱在埃及馬穆魯克軍事統治者手上。1507年,當葡人從回教徒手中奪得索科得拉島和荷莫茲島兩個要塞時,這條與東方貿易航道上的兩個主要海峽,紅海和波斯灣,就被他們封閉了。1509年,回教徒艦隊被打敗,回教徒在帝裕(Diu)的防御主力被打破。1510年果亞被攻克;1511年,馬六甲也落在葡人手中,他們隨後在香料群島修築堡壘,更改非洲一帶的貿易航道,里斯本便成為16世紀歐洲的商業都市。當時,葡萄牙人的新座右銘是:“香料和生命”。(5)
但葡人並未因此而停步。到1513年,歐維士(Jorge Álvares)到達中國;在隨後的1514年,一個貿易使圑相繼到達:1515年,拉帕爾·佩雷斯特羅(Raphael Perestello)乘坐中國帆船到達南中國;1517年,安德拉斯(Simão Peres d'Andrade)沿珠江航行到廣州,葡國首位駐華大使湯母·貝雷斯(Tomé Pires)也於1520年到達北京。1542年,安東尼奧·達·莫塔(António da Mota)和兩位同伴被風吹襲而首次到達日本。幾十年間,回教的前線被側翼包抄打而破,後方的聯繫也被切斷。東西方之間有了更多直接聯繫。歐洲發現了,或者説,重新發現了非洲和亞洲--一個新的世界。(6)
葡人是在土耳其人蹲在中世紀通往東方的陸路上,令商人感到困難和無利可圖時發現通往印度及東方各地的海路。耶穌會俗家修士貝托·德·戈斯(Bento de Góis)(1563-1607)於1602年應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要求,從亞格拉經陸路到中國,以便探索陸路和求證利瑪竇的假設:馬可勃羅和中世紀修道士所指的Cathay 就是中國。臨終時,戈斯回憶説,這段旅程是多麼漫長、多麼疲累和多麼危險,因此,任何俗家修士都不應步他的後塵。雖然有這樣的忠告,人們還是作了多次嘗試去尋找另一條道路來代替一般漫長、疲累和危險的的海路。這些嘗試多半是在與中國建立了陸路聯繫之後,計劃通過俄羅斯領土進行。(7)
中國也有和葡萄牙一樣重大的成就,她很久之前已發現我們現在所稱的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從永樂皇帝(r.1403-1424)統治時期的1405年開始,在鄭和(1371-1433)的領導下,曾進行過七次遠征,西行遠至非洲。(8)
發現年代至到達日本時結束,接著是殖民地年代的開始。如今天一樣,葡萄牙是一個細小國家,難望征服巨大的亞洲和非洲。但作為一支海上力量,她要通過建立貿易代理店、堡壘來維持對重要港口和貿易中心的支配,從而達到控制貿易航道,保護本身利益的目的。(9)
由於東南亞的葡人和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發現了這個陌生文化的新世界,他們很快就醒悟到,基督教的信仰僅僅是屬於歐洲人。當初,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都被很多人視為魔鬼的傑作。這樣的醒悟給了歐洲人一種天命感,一種要征服和改變有別於中世紀歐洲的事物的決心,一種認為自己是“優良種族、尊貴教士、神聖之國、另類民族”的信念。(10)
然而,對於東方的民族來説,這些西方新來客被視為蠻人。中國人稱他們為佛朗機;他們後來稱紅髮的荷蘭人為紅毛人。俄國人從西北接近中國,被視為是北方蠻人,稱作羅叉和俄羅斯人。(11)
早期離開歐洲前往改變這個新世界的傳教士也曾企圖將之西化。在葡萄牙屬土,皈依基督的人洗禮時,不僅被給予一個基督教的名字,而且還被勸諭使用葡人姓氏,穿歐洲衣服,遵守歐洲禮節。西班牙人在他們的地域裡也做同樣的事情。當時,任何對於歐洲文化的更改都被視為與神對抗,別説要更改基督教義。塔瑟斯的保羅修改教義,以便適合希臘羅馬文化(目前還是一個猶太小教派),他的精神和事例被置之不理。伊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於1534年建立“耶穌會規則”,其主要目的是保衛和宣揚基督信仰,他的兒子們受了他在規則裡所表現的精神所鼓勵,模仿聖保羅,試圖以他為榜樣。像這樣的嘗試非常少見。(12)
到這個屬葡國教權管轄的新世界的首批傳教士為天主教聖方濟各修士及多明尼克修士,在這裡,他們繼承中世紀前輩的事業,從事傳播福音的難苦工作。在葡屬的要塞,俗家基督教士從事牧師的工作。耶穌會會員隨後於1542年到來,葡人在東方傳教歷史的第一階段宣佈結束。深刻的轉變開始發生。(13)
在耶穌會士之中,首位到達的是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耶穌會於1540年正式建立,目的是在任何教皇希望其會員去的地方傳播基督教。在一年之間,沙勿略和其它四人相繼離開歐洲到東方。沙勿略受葡萄牙國王派遣,以葡國教區傳教士的身份前來,並獲教皇授予教廷大使的權力。他和他的同伴的傳教活動開始時依賴葡萄牙殖民地,他希望得到當地政權的支持和幫助,但最終令他大失所望。正如他自己所説,(14)他從葡人管轄範圍“逃”到日本,在那裡,沒有那些對本地人苛刻的歐洲官員能破壊辛苦建立的事業。在印度,沙勿略比起其它傳教士顯得更能容忍當地的習俗,縱然他是在願意以歐洲形式接受基督教的貧苦漁民和低下層人士之間工作。
在日本,沙勿略在受過佛教僧侶的挑戰後,他的傳教方法有了新的發展。日本人的反應令他醒悟到,要在亞洲成功傳播基督教,傳教士們必須以當地人語言來與當地人接觸:以當地語言講、讀和寫;成為某一文明社會的一部份,做到入鄉隨俗。正如後來人們所説的“要為耶穌基督得到中國就要先成為中國人”。因此,在學習日文的同時,沙勿略寫道:“蒙神庇佑,在這六星期裡,我們已經可以用日文講解十條誡律了”。(15)
沙勿略甚至曾經把Dainichi,即偉大太陽(在大乘佛教裡為大佛,在真言宗教派被奉為神)這名稱與基督教概念中的神視為等同。這是一個不願意的選擇,因為無論如何解釋,Dainichi不能和基督教概念中的神相比,甚至不相近。當他發現自己的錯誤時,他便不再使用這個名稱。他的繼承人在以後的五十年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並決定採用傳統的葡萄牙用語或者拉丁用語來表達基督教的概念。Deus這個字後來變成Deusu Christiano變成Kirishtan等等,正如幾個世紀以後日本人採用beisuboro(棒球),aisukuremu(雪糕)等等。他們後來避免這些用法,因為在16世紀的戰爭時期,日本已是一個開放社會,願意以西方形式接受基督教義、槍砲和貿易。(16)
為接近日本貴族,以及在他們面前與佛教僧侶作鬥爭,沙勿略作貴族打扮,穿著以金鍊裝飾的昂貴衣服,説話時,有隨從跪在跟前。但所有這些皇家的排場祇為一個目的,就是要那些他們視為基督教死敵的佛教僧侶丢臉。(17)在與他們辯論的過程中,他明白了兩樣東西:第一,將來到日本的傳教士必須是有學問的人,“是有實力的學者,勤於練習方言……以便擊破詭辯和找出錯誤教條中前後不一致和互相矛盾的地方”;(18)第二,要日本皈依基督的秘訣在於先要中國皈依。沙勿略寫道,“日本人試圖以這一點來反駁我們:如果事情真如我們講道時所説的一様,為甚麼中國人一點也不知道? ”(19)
當沙勿略最初登陸日本時,他就觀察到日本人和他們的中國宗主們一樣,以理性為主導,而且對科學表現出極大興趣。他是這樣描寫日本人的:
他們不知道世界是圓的;他們對太陽和星星的運行軌迹一無所知,因此,當他們提問時,我們就解釋……他們熱切地傾聽……視我們為非常有學問的人,十分尊重。我們廣博的知識打開了他們的心扉,從而使我們能播下宗教的種子。(20)
日本人和他們的中國宗主們對道德行為的強調也教沙勿略留下印象。在這方面,他認為東方和基督教的道德規範都很接近。因此,未來的傳教士必須是高道德標準、高學問、對科學有深刻認識。沙勿略是第一個意識到科學對於進入東亞社會的重要性的人。(21)
沙勿略決定到中國去瞭解更多日本人信仰、價值觀的淵源,和令皇帝明白基督教的真蒂。他抱有這樣的希望:一旦天子改變了信仰,所有的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會追隨,不久,整個東亞都會皈依基督教。但他始終未能衝破中國自我封閉的圍牆,在奮鬥的過程中,於中國海岸的上川島(今天也叫聖約翰島)去世(1552)。
我們不能認為,沙勿略所進行的無數次旅程,是他這個來自那瓦爾的人要表現他的冒險精神,也不能解釋為,他這個主管由好望角到日本這一廣闊區域的長官本人希望探訪他所有的信徒和檢視他們的工作。(22)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傳教士,他的使命是一位開拓者、探索者的使命,是要為人們開路,這是教皇和他的上司羅耀拉所付予他的。沙勿略當時僅僅45歲,對他來説,似乎有充足時間來策劃如何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尋找優勢,借此在東方實現基督化,這是他前進的動力。依賴當地的神職人員(南印度、馬六甲和摩鹿加斯群島)並不能預示有好的未來,即使這種依賴是暫時的。軟弱不振、心不在焉、不思進取的人隨處可見,這是難有所成的。就在這一刻,有人告訴他,日本人截然不同;當他一見到日本人,他就知道他沒有被欺騙,他的願望獲得實現。日本人告訴他,他們的老師和宗主是中國人。因此,經過艱苦的努力,他得出結論:要日本皈依基督必須先要中國皈依。(23)
然而,要實行這個計劃,就要先克服一個巨大的阻力。16世紀明代的中國,雖然仍是一個行政有序、政治穩定的國家,但未肯拆除自我封閉的圑牆,不像印度和日本,戰爭、動亂和開放的社會使葡人和耶穌會士能在那裡立足,甚至可以用歐洲形式推廣基督教。不過,明朝(1368-1644)之前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24)
在蒙古人(元朝)被打敗和逐出之後,洪武(r.1368-1398)和永樂(1404-1424)兩位明朝(漢人統治的最後皇朝)最早的統治者試圖保護中原,使其不受海陸威脅。洪武帝曾發動九次運動,對抗當時仍然有威脅力的蒙古人,盡可能將他們逐出長城以外更遠的地方。永樂年間,曾有過七次海上遠征,使中國與東南亞和非洲有了聯繫。至少在元朝初時,中國是大蒙古帝國的一部份,外國“蠻人”從四面八方而來。
至1429年,四周邊界都得到鞏固之後,中國關閉所有大門,實行自我封閉來清洗自己及其文明,使其免受世界大同思想的污染,以恢復本身文化的純潔性。日本海盜對中國海岸的威脅令中國的封閉更加加強。一般中國人認為葡人要比日本海盜好一些,而S. P. 安德拉斯的例子確實是這樣。(25)
當時到中國去的外國人就等於去受死或坐牢,沙勿略沒有因此而裹足不前。他建議東印度群島的葡國總督委任其中一名葡人出使中國,而他就作為教廷代表一同前往。他希望以此方法來把他的情況向最高當權者提出,他將攜同禮品獻給皇帝,請求他修改不許外國人進入的法律和釋放囚禁在廣州的葡國人,以及准許他和他的同伴傳播福音。
該總督認為這個計劃值得試行,因為他早已目睹過沙勿略成功排除過許多似乎不可能排除的障礙。因此,他委任沙勿略的朋友迪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為大使,而沙勿略就與他同行。但所有的努力都被馬六甲總司令阿爾瓦羅·達伽馬(Álvaro de Ataíde da Gama)和這位航海家的不肖子華士高·伽馬破壊載著大使的船停在馬六甲時,這位總司令不允許離開,除非對佩雷拉的委任獲得撒銷。阿爾瓦羅這個十分貪婪的斂財者想自己坐上這個有利可圖職位。沙勿略想,無論他向中國皇帝的請求如何成功,最終也歸於阿爾瓦羅,因此,他放棄了所有以正常方式進入中國的希望,獨自乘船以走私方式進入這一帝國。在實行他的計劃之前,他寫了一封告別書給佩雷拉大使,該大使曾給他金錢,以便買通到達中國的路。沙勿略寫道,如果佩雷拉去探望他,他不在廣州監獄就是在京城皇宮,據説皇帝就住在那裡。(26)後來於1552年8月,在與一位忠實的中國傳譯員到中國海岸的上川島途中,他與一位中國商人做好安排,送他到大陸。但是,後者並未出現,沙勿略在12月3日死於荒島上,他打破中國自我封閉的努力付諸東流。
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沙勿略的精神和處事方法仍然留存:在以後的三十一年裡,他的同仁和繼承者以令人欽佩的毅力試圖打開中國的大門,但始終未有大的成續。就算有些人能成功進入(曾有25人)也未獲得居留,祇好在短期内離開。這25人的故事是這樣的:1555年7月20日,印度耶穌會葡人大主教梅施爾·努内斯·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1519-1571)在去日本途中訪問上川島並在那裡主持彌撒。他由卡斯巴爾·維雷拉(Gaspar Villela,1526-1572)神父和四名耶穌會教友陪同;美士爾(Melchior),安東尼奧·迪亞斯(António Dias),路易斯·弗來斯(Luis Fróes,1528-1597)和埃斯特旺·德·戈斯(Estevão de Gois,1526-1588)。8月3日,他到達澳門以西28里格的蘭浦高島(譯音),(27)同年的8月和11月之間,他兩度到廣州,每次停留一個月,試圖令獄中的三名葡國人和三名本地基督教徒獲得釋放。(28)1556年的四旬齋期間,他第三次到廣州。隨後他於6月5日繼續前往日本,留下德·戈斯教友在中國學習語言,但他因病於1557年返回果亞。(29)
1556年末,卡斯帕·達·克羅斯(Gaspar da Cruz,O. P.)到達廣州,在那裡停留了一個月(30)。1560年1 1月21日,巴爾塔薩·加戈(Baltasar Gago,S. J.1515-1538)從日本歸來途中,由於天氣惡劣,被迫在海南島躲避,直至1561年5月才離開,經過30天旅程到達澳門,停留至1562年1月1日離開。(31)
1562年8月24日,意大利耶穌會士哥瓦尼·巴帝斯特·蒙特(Giovanni Battista de Monte,1528-1587)和他的葡人同伴弗來斯在澳門停留,至1563年中才離開。(32)
1563年7月29日,耶穌會士弗郎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éz,1514-1583)、馬努埃爾·特舍拉(Manuel Teixeira,1536-1590)和安德烈·平托(André Pinto,1583-1588)隨葡國駐中國大使佩雷拉到澳門,如前所述,這次出使不成功。(33)
1565年11月15日,西班牙耶穌會士胡安·伊斯哥巴(Juan de Escobar)和前面提及的佩雷斯到廣州,11月23日請求當局准許他在中國居留,但被拒絕。(34)
1565年,佩雷斯和特舍拉在澳門建立了耶穌會的會所。(35)
1567年8月15日,西班牙耶穌會士胡安·波提斯特·雷貝拉(Juan Bautista de Ribera,1525-1594)和兩位同伴到澳門,然後於1568年9月到達廣州。他計劃前往南京,但不久被迫返回澳門。(36)
1568年10月前,佩德羅·勃納文杜拉·烈拉(Pedro Bonaventura Riera,S. J. ,1526-1537)與一些葡國商人一道前往廣州。(37)
1569年,另一位耶穌會士(可能是主教)梅施爾·卡內路(Melchior Carneiro,1519-1583)在廣州停留了一段時間。(38)
安東尼奥·瓦斯(Antonio Vaz,S. J. ,1523-1573?)曾於1574年2月7日至3月20日(大約)在廣州逗留。(39)
1575年,克利斯多旺·達·高士德(Cristóvão da Costa,S. J. ,1529-1582)曾兩次陪同葡國商人往廣州,分別停留兩個月和一個月,但未准許居留。(40)
約於同時期的1575年,主教卡內路試圖在廣州立足,但未能成功。(41)
1575年,兩名奧古斯丁教士以及西班牙人馬爾丁·德·拉達(Martin de Rada)和麥西哥人熱羅尼莫·馬林(Jerónimo Marín)從菲律賓到達福建省,於9月14日回菲律賓。(42)
1579年2月一些耶穌會士前往廣州。(43)
同年6月23日四名聖方濟各傳教士和三名第三會會士以聖方濟各教士打扮到達廣州。這幾名傳教士分別為意大利人哥瓦尼·巴蒂斯德·盧卡雷勒·巴沙路(Giovanni Battista Lucarelli da Pesaro,1540-1604),西班牙人佩德羅·德·阿爾弗羅(Pedro de Alfaro,卒於1580),安吉斯蒂諾·德·特爾德西拉斯(Augustino de Tordesillas,1528-1629)和塞巴斯蒂奴·德·巴埃薩(Sebastiano de Baeza,卒於1579)。那三名第三會會士分別為西班牙士兵弗郎西斯科·德·杜納斯(Francisco de Duenas)和胡安·迪雅士·帕多(Juan Diaz Pardo,卒於1615),以及麥西哥人佩德羅·德·維拉羅爾(Perdro de Villaroel)。他們在廣州監獄被囚禁50天後,被迫離開中國。(44)
1580年復活節(4月3日),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S. J. ,1543-1607)前往廣州,在河邊一間房屋居住。1581年,他兩次回到廣州,第一次由教友貝雷斯(1563-1632)陪同,第二次由安德烈·平托神父陪同。(45)第一次他停留了三個月,第二次停留了二個月,都住在暹羅使館內。(46)1582年4月和5月,他第四度到廣州,逗留了一個半月,5月2日,阿羅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S. J. ,1551-1614)和兩個聖方濟各教士加入,其中一人為第三會會士帕多,他已是第二次到廣州。這些人都是從菲律賓經廣東省東北部一口岸進入。桑切斯從5月2日到29日都停留在廣州。(47)羅明堅曾兩次從廣州出發到肇慶,這是兩廣(廣東和廣西)總督府所在地。他在6月份第一次前往時,由一位法庭稽查員馬提亞斯·番納拉(Matías Panela)陪同,而12月27日第二次前往時,就由法朗契斯哥·巴休(Francesco Pasio,S. J. ,1554-1612)陪同。兩次到肇慶之間的一段時間,他返回澳門。1583年3月,羅明堅和巴休第二次從肇慶返澳,而兩位聖方濟各教士就經澳門和日本返回菲律賓。(48)
1582年6月,隱修士傑諾尼摩·德·布爾戈(Jerónimo de Burgos,卒於1593),馬丁(依納爵·羅耀拉之姪),特爾德西拉斯(第二次),日羅拉莫·德·阿及拉爾(Girólamo de Aguilar,卒於1591)及安東尼·德·威蘭奴瓦(Antóniode Villanueva)本想前往澳門,但卻在福建省泉州登陸,同行的有由兩位俗家修士弗朗西斯哥·德·戈爾多瓦(Francisco de Córdova)和克利斯多弗羅·戈麥斯(Cristóforo Gómez)以及三位士兵。他們被當作間諜帶往廣州,但後來被釋放並送往澳門。(49)
1583年5月,另一組隱修士,迪雅哥·奧羅佩薩(Diego de Oropesa),巴托羅米·諾伊斯(Bartolomé Ruíz),弗朗西斯哥·德·蒙蒂亞(Francisco de Montilla)和佩德羅·柯提斯·卡貝薩斯(Pedro Ortiz Cabezas)在從安南國到菲律賓的途中因颱風吹襲登陸海南島。陪同的四名聖方濟各俗家修士為戈麥斯,迪雅哥·占門尼斯(Diego Jiménez),弗朗西斯哥·威拉連奴(Francisco Villarino)和一名見習修士馬紐爾·聖地牙哥(Manuel de Santiago)。他們被當作間諜帶往廣州,在葡人付給捐贈之物後獲得釋放。(50)
如果不包括澳門耶穌會的人員,進入中國的人次(包括重複進入)算起來有:32名耶穌會士(24名神父,9名見習教士或俗家修士),24名聖方濟各會士(13名神父,11名俗家修士或第三會會士),2名奧古斯丁教士和1名多明尼克教士。如果我們剛以進入中國的個人來算,不考慮他進入的次數,算起有:25名耶穌會士,其中17名為神父,8名為見習教士或俗家修士:22名為聖方濟各修士,其中12名為神父,10名為俗家教士或第三會會員,兩名奧古斯丁教士,一名為多明尼克教士。這份名單一點也不完整。名單上的僅僅是那些在1552和1583年間成功地打破中國自我封閉並在那裡建立固定居所的人。(51)
這就是傳教士在中國這個一直與西方敵對的國家堅持不懈地傳教的故事。然而,1557年,中國當局准許葡萄牙在廣東省的一個半島末端建立一個名叫澳門的貿易站,條件是要葡人協助消滅一個特別令人煩惱的海盜首領。(52)初期,人們在該半島的頸部建起了障礙物,除了一年兩次可以從有嚴密守衛的中央門口出入之外,無人能進出,但後來門口變得更闊,而且人們有更多辦法繞過圍牆。因此,葡國和廣東當局之間的定期聯繫就越來越多。
傳教士試圖進入中國的熱情並未減退,而且得到歐洲上司的全力支持。在歐洲,這種熱情受到一個意外消息的鼓舞而變得更加高漲。在沙勿略去世(1552)前的一年,傑出的西班牙貴族甘地亞公爵弗朗西斯·波吉亞(Francis Borgia,1510-1572)放棄他所有的頭銜和財產後,被立為耶穌會神父。他從前的地位及其與別不同的個性使他説每一句話和做每一件事都特別有權威。1559年他訪問葡萄牙,因為東方(從印度到日本)是葡國教權管轄下的教區,他能直接獲得關於建立澳門和打入中國報導的第一手資料。他公開表示,在中國展開傳教工作很有希望。他説的話在耶穌會內引起很大反響,各區的老少教士紛紛向上司遞交請願信,請求參加這項工作。
1565年,波吉亞被選為耶穌會的首腦,這項計劃就更有機會獲得支持。他對於傳道的興趣不限於他的聖職範圍之內,有記載他在1568年與羅馬教皇庇護五世的一次談話中建議組成一個特別的議會來指導一切有關令非基督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活動,因為當時的傳道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當政者,而這些人已再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個建議成了1622年的傳道議會(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的建立。(53)就他的職責而言,他做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是接納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進入耶穌會,他是東方第二大耶穌會傳教士。(54)
這位傑出的年青人是教皇保羅四世的一個親密朋友的兒子。他在帕度亞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為教皇作法律服務,開始他前途無量的生涯。27歲時,他放棄了這份職業,加入耶穌會。由於他從前的學問,他不久就被委任為神父。五年後,他出任羅馬克里那爾的聖安多尼區見習修士總管助理職務。1571年,見習修士總管不在職,給了他極好機會去接受另一位有前途的法律學生成為見習修士,這就是利瑪竇,他當時20歲。他們的相識很有意義,因為他們的生命將連在一起,並對中國的傳教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當年輕的利瑪竇完成見習期後,聽説范禮安要求被派往東方的傳教區,當時的范禮安已是馬塞雷特(Macerata)(這是利瑪竇的家鄉,范禮安可能見過他的家人)耶穌會學院的院長。他的願望獲得實現,但他並不是以普通傳教士的身份前往,而是作為一位巡官,巡視全面的傳道工作,並為將來的發展作出指導。范禮安於1574年3月離開里斯本,9月6日到達果亞。他作為巡官一直停留在這個從好望角開始延伸的廣闊地區直至1583年10月;後來他被委任為印度大主教。他一直任此職位直至1587年他再度被委任為亞洲區的巡官為止,1595年他轉任遠東地區巡官,直到1606年去世。他到達果亞後,注意推動商業發展。隨後他乘船到日本,但被迫停留澳門十個月(1577年10月-1578年7月),等待順向的季候風。這是他三度到日本的其中一次。其餘兩次為1590-1592及1598-1603,每一次都在澳門停留。然而,他在澳門逗留的十個月是天意的安排,在這裡,他獲告知人們為進入中國作了不懈努力,但未能成功,他發覺一些耶穌會士有悲觀情緒,他們認為再度嘗試也難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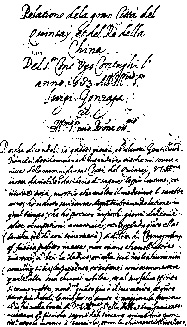 杭州--手寫標題為“中華大都市Quinsay(馬可波羅對杭州的稱呼)寫實”。杭州是(在澳門之後)第二大基督教社圑所在地,該教圑創始人為羅明堅神父和索德超神父。
杭州--手寫標題為“中華大都市Quinsay(馬可波羅對杭州的稱呼)寫實”。杭州是(在澳門之後)第二大基督教社圑所在地,該教圑創始人為羅明堅神父和索德超神父。
范禮安是一個以開放思想看每一樣事物的人。當他初到印度這個東方世界的時候,他決定盡可能去瞭解每一樣關於中國的事情。他像沙勿略一樣,打聽有關中國人的事;通過個人交往,他認識了幾位中國人。他在寄往歐洲的信上形容他們是“一個偉大和有價值的民族”,(55)並得出結論:未能使他們認識和接受基督教的原因是他們已接受了一套思想方法。他在寫給派遣他的耶穌會大主教波吉亞的信中寫道:進入中國的方法要與目前耶穌會在所有其它有宣道團的國家所採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他相信,中國人尊重學問,而且他們願意以明智的方式聆聽任何在他們面前提出的東西,這一點可以用作打開他們的心扉,使其接受基督教,但他同樣明白到,他們會排斥每一樣聲稱來自比他們優越的文明社會的東西。因此,他發出指示,所有派往中國做傳道工作的人,都必須學會讀、寫和講中國語言,以及熟悉中國文化和風俗習慣。
他原以為任何在澳門的傳教士都適合做這項工作,但由於他們的看法與他相反,令他不敢抱太大希望。因此,他寫信給果亞的耶穌會大主教維森特·羅德理戈(Vicente Rodrigo),要求派遣當時是交趾教區長的年青意大利神父巴納甸奴·德·法拉里斯(Bernardino de Ferrariis)。為何他要選擇這個人和為何這個人不能去,原因不大清濋,但大主教派遣了一個他認為是很好的替代人:羅明堅。(56)
正如他的前輩沙勿略一樣,范禮安醒悟到有學問的人是必要的,他不僅要求這些人從歐洲派遣,而且還十分注重知識訓練,他重組果亞聖約翰學院的教學,在芬耐(Funai)、日本建立學院,為澳門的學院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架構。范禮安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沙勿略的文化融合方法,而且使它制度化,並且在日本付諸實行,正如他在1581年的一本書(Ⅱ cerimoniale per i missionari del Giappone)中所體現的。(57)他為進入中國作了準備,派遣了三名傳教士,他們將在那裡實行文化融合。范禮安有三方面比沙勿略有利:他得益於沙勿略所開拓的見識,他有更多的時間(他三十二年而沙勿略祇得十年),在最後的十一年裡,他祇需關注東亞地區。
當被召派到中國開展事業的羅明堅於1579年到達澳門時,范禮安已出發到日本,但他留下簡短的指示,吩咐羅明堅如何為那些艱苦的工作做準備。羅明堅滿腔熱忱地展開工作,首先編了一本教義問答集,後來在兩名中國傳譯員的幫助下,把儒家四書之一的《大學》譯成拉丁文。(58)其它澳門的傳教士沒有給他甚麼鼓勵。他們人數不多,主要是在士兵和商人之中工作,他們希望他分擔這些工作,因為他們對獲准在中國傳教不抱甚麼希望,或者覺得完全無望。然而,羅明堅繼續勤懇工作,但發覺學習中文與學習印度方言大不一樣。雖然他熟悉中國朋友的禮節,但要通曉中文對他來説十分困難。他對於學習中文已不存甚麼幻想,因而寫信給在日本的范禮安,建議派遣與他一同到印度的利瑪竇到澳門加入工作。范禮安同意該建議並寫信到印度叫利瑪竇和巴休兩人到澳門工作,這兩人是和羅明堅一起從意大利來的。巴休當時準備出發到日本。那時候,信件傳遞非常費時,范禮安本人竟然比這兩位傳教士先到達澳門。
與此同時,羅明堅決定盡可能用新的方法來處理中國的事務,他請求被允許和葡國商人一起到廣州,這些人每年到廣州兩次。他在澳門的第二年才能首次到廣州。這一次,他對中國人的每一樣禮節都格外留意,而商人們卻毫不在乎。這一點立刻受到中國官員的注意,他們在首次會見他之後,便邀請他出席每一個與外國人見面的場合。
冰封被成功地打破。次年,羅明堅第二度訪問廣州時,受到特別的禮遇,他被看作是一名外國學者而不是商人。在與官員見面的時候,其它人都要下跪,而他卻被允許站立。到他第三次訪問時,一些軍政官員參加了他的彌撒。
這是范禮安於1582年從日本回到澳門時的狀況。他看到了文化融合的成績,這正是他在日本所提倡的。現在,他可以在中國將之實施,而且同樣有成功的希望。由於戰勝那些墨守成規的傳教士的可能性不大,於是,他更換了澳門地區的主管,以及為中國傳道團建立了架構,這將大大有別於平常在士兵和商人中的傳道工作。
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范禮安有充份的理由相信新的方法會成功。麥哲倫於1522年發現菲律賓群島之後,它們成為了西班牙的屬地,也變了一個新的教區。1578年,一群西班牙耶穌會士被派往加入當時已在當地工作的傳教士。(59)其中一些人很迫切地要參加令中國皈依基督的工作,尤其是菲力普二世成為葡萄牙國王(1578)之後的1580年,他們經福建到廣州,因而繞過澳門。廣東省的官員認為這是未經批准而擅自利用祇給予來自澳門要員的特權。首府設在肇慶的兩廣總督命令澳門主教到肇慶,在那裡他將會被知會政府在這件事件上所採取的政策。1582年末,范禮安派羅明堅代表主教前往,這位年輕教士的禮貌及謙和令他贏得勝利。結果,他在返回澳門的途中就接到總督的正式邀請書,請他到肇慶永久居住。范禮安立刻同意,並委派剛從印度來的巴休陪同羅明堅一起前往。總督對他們熱情款待,送了一座塔子給他們居住,還在他們安頓好之後,進行禮貌性拜訪,並送了他一幅字畫。
但好景不常。當總督失寵,被召回北京接受盤問時,他認為把這兩個耶穌會士打發走是明智之舉。他們無可奈何回到澳門。(60)羅明堅於是寫信給廣州的官員,要求給予特權。在很短時間內他獲准回去,並如他所要求,獲撥給一小塊地建房子和教堂。其時,巴休已經去了日本,因此羅明堅把在1582年8月7日到澳門的利瑪竇帶往肇慶作為同伴。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日子,雖然是范禮安決定了在中國傳道的新方法,羅明堅卻是首先將之付諸實踐的人。但是,令這種方法完全獲得成功的是利瑪竇。從這時開始,他成為中國大地上一位舉足輕重的耶穌會士。(61)
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生於意大利的馬塞雷特,正是沙勿略去世的那一年。他在家裡十二個孩子中排行最大,9歲時,他入讀本地的耶穌會學院。1568年,他被送往羅馬大學讀法律。三年後,他進入克里那爾的聖安多尼區作見習修士。他首次宣誓後,曾在佛羅倫斯耶穌會學院短暫任教,其後,他回到羅馬學院,在著名的克里斯托弗·卡拉維亞斯(Christopher Clavius,1537?-1612)門下攻讀哲學和數學,這位老師是開普勒和伽利略的同事和朋友,也是將凱撒曆改良為格列高里曆(1582年頒佈使用)的領導者之一。利瑪竇同時學習歐幾里德幾何學、物理學、托勒密的天體力學、地圖繪製學和機械學。關於這些學科的大部份科學論著後來都由他或在他的指導下翻譯成中文。他還有實用的才能,從製造日規和星盤到時鐘和其它器具,他都稱得上是能手,而且造出的款式甚有創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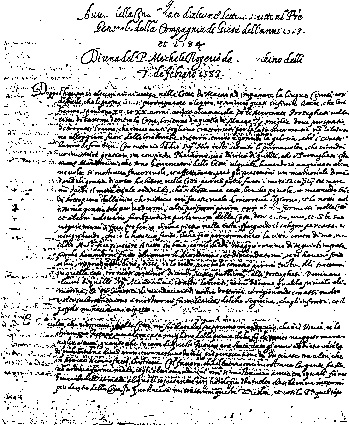 羅明堅神父的信函(肇慶府,1583年2月7日)
表述他想學習中文前往廣州的意願
羅明堅神父的信函(肇慶府,1583年2月7日)
表述他想學習中文前往廣州的意願
當他轉學宗教時,同樣表現得出類拔萃。耶穌會教授(今天稱神學家)羅伯特·巴拉邁(1542-1621)是當時的大辯論家和“異教徒的強對手”。利瑪竇修讀他的辯論課程,學懂了如何對教義進行清楚的解釋,後來他把所學的都運用到實踐中去。每一個人都預期這位年輕學生會當一名出色的教授,但是,隨著文藝復興思想鍛練的加強,他的興趣又轉向新發現世界的傳教工作,而這個新世界的開放又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成就之一。1577年,他被接納為葡國教權轄下的印度耶穌會傳道團成員。到了葡國,為了充實自己,他進入科英布拉大學繼續攻讀神學,之後,於1578年3月乘船離開里斯本。在交趾作短暫停留之後,他到果亞的聖保羅學院任教四年,1580年7月在該學院被立為神父。其後,他被范禮安召到澳門,到達時為1582年8月7日。如前所述,該調派是由羅明堅所提議的,而羅明堅本人是於1579年奉召到澳門,以便在中國展開事業。
從1580年-1582年,羅明堅曾先後四次到廣州,其中一次直接往肇慶,這一次由巴休陪同,當時為1582年12月。利瑪竇因由印度而來,經過了一段風浪旅程,身體仍然虛弱。(62)他打算稍後再加入這兩人的工作。(63)但是,巴休和羅明堅並未能長期留在肇慶,他們被迫返回澳門。然而,數月之後,於1583年9月10日,羅明堅和利瑪竇成功地在肇慶立足。自此,利瑪竇從未離開過中國。1588年,范禮安決定派羅明堅到羅馬去報告當時的情況,並請求教皇派大使到中國。但四位教皇一年半之內相繼去世,令派遣正式宣道團的事情不獲考慮。隨著時間的消逝,最好的時機已經錯過。在歐洲,羅明堅的健康欠佳,再不能回到中國。
利瑪竇獨自留在肇慶,直到1589年。這一年兩廣(廣東和廣西)總督去世,由另一人繼任。曾有三任總督干涉他的逗留,但這一任卻要設法驅逐他出境。由於他已慣於和官員打交道,通過巧妙的爭辯後,他獲得修改法令,條件是要他遷居另一城市。所以,他遷到了廣東省北面更遠的韶州。他在那裡逗留至1595年,當時,他的一位當高官的朋友(是軍部成員之一)因日本侵華問題而被召回北京,邀請利瑪竇同行,至少也要他陪同走一段路。進入中國心臟是他一直等待的機會。他與這位官員一直同行到南京,他希望在此停留一段時間,但未能如願,因南京是該帝國的第二大城市,當時籠罩著戰爭的氣氛。幾個星期之後,他回頭向南走,到達江西省會南昌。這是一個學者眾多的城市,他在這裡逗留直至1598年6月,然後啟程前往帝國的首都北京。由於無法在那裡立足,他於是回到南京,至1600年5月19日,他再度出發到北京--這一次他獲得成功。他於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他於1610年5月11日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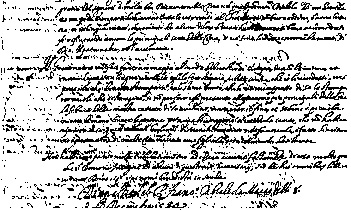 羅明堅神父的信函(肇慶府 1583年2月7日)
羅明堅神父的信函(肇慶府 1583年2月7日)
這就是這位非凡人物的簡短故事。在他去世時,耶穌會的傳教士已經遍佈全世界,他們在不同的國家用不同的方法傳播福音,以適合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但在中國所採用的方法就與別不同。古老、成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使中國有別於其它國家,要把基督教移植到中國,就必須先認識這樣一種值得敬仰的文化。
現在,我們尚要檢討一下利瑪竇用來達成目的所採用的方法。利瑪竇的文化融和方法並不是僵化的政策而是在反複試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理智做法。他運用了前人的思想和實踐,但他是有選擇地運用的。他保留那些事實證明為有用的,其它的加以改良或將之放棄。他繼承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中國人是很有智慧和理性的民族,他們高度重視道德規範和道德行為,同時也很注重科學。
最早到中國的葡人和傳教士,包括沙勿略和范禮安都確信,如果中國皇帝能被説服賜給他們一個演講的機會,他們將可以説服他允許葡國和中國進行貿易,甚至允許在他的子民之中傳播基督教。這就是為甚麼傳教士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翻譯教義問答集。他們認為,最有必要的事是把譯本傳到皇帝手上,如果不能,就傳到那些官員手上,由他們交給皇帝閲讀,其餘的事可接著進行。正如他們所覺得的,問題在於如何能接觸皇帝。
從與中國人初次接觸的葡國人就醒悟到,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葡國國王派大使或印度總督到中國。這可以是個外交使團,如在范禮安同意之下,羅明堅促請教皇派往中國的一樣;這還可以是一個貿易使團,如沙勿略所提倡的迪戈·佩雷拉的使團。(64)傳教士會跟隨這些使節,抓住機會向皇帝解釋基督教義。由於困難和障礙使使團出發延誤,有些人甚至提倡以武力對付中國,他們認為,這是合理的措施,因為中國人無理地抗拒福音。對武力的提及不僅能在最早期的葡人報告書中找到,(65)而且也可在1580年代的西班牙人報告書中找到,當時西班牙傳教士到中國的人數在菲勒普二世即位葡萄牙國王後,有所增加。
利瑪竇同意這樣一種基本看法:中國人是一個有智慧、講求道德規範和對科學有興趣的民族,但他比別人有更強的領悟力和理解力,因而得出與前人不同的結論。他是第一位學懂中文而不需要依賴翻譯員或作過囚犯的葡人所寫的報告的人。在北京的九年期間,他從未見過皇帝,但是,甚至在到達該城市的1601年之前,他已經對這個儒家天下的國家的政治社會結構有深刻的認識,並且領悟到:皇帝在理論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其實有限,如果皇帝懦弱,甚至大臣、太監或者兩者都可以謀朝篡位。他同樣了解官紳文人階層所起的作用。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他放棄了利用大使的想法;至少他沒有像范禮安和羅明堅那樣大力提倡或把它放在優先位置。至於用武力對付中國,他完全沒有考慮,甚至沒有在書信中提及,他目睹1592年豐神秀吉(1536-1598)侵略韓國徒勞無功的事例。
當利瑪竇和羅明堅於1583年首先進入中國時,作佛教僧侶打扮,這是他們的前輩沙勿略和范禮安建議他們這樣做的:但當他們知道那些文人看不起佛教,和目睹某些和尚的生活方式和無知時,他們採納了文人的整套生活方式,而他們一些文人朋友也催促他們這樣做。早前,兩廣總督也曾提議羅明堅這樣做。(66)再者,利瑪竇的興趣也主要在於文化人階層,因此,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他們身上。
利瑪竇的前輩沙勿略、范禮安和羅明堅知道中國人尊重和欣賞科學技術,因而主張用這些手段,或者有人説是“魚餌”來吸引中國人。同樣地,當知道儒家對道德行為的注重,而這方面又似乎和基督教很相似時,他們認為已經找到另一樣吸引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教義和信條的東西。利瑪竇則有更深刻的觀察和領悟,他明白到中國人的世界觀,也就是意識形態是全面的,包括科學、技術、倫理學、哲學所有這些組成了一個有機體。因此,他認為有必要用相似的方法介紹基督教,把基督教作為一個有機的、全面的世界觀來宣揚,而他的相識、朋友或中國的皈依者將稱這套世界觀為“西書”或“天書”。(67)利瑪竇在1603年首次出版的著作原名為《天書實義》,雖然後來更為人所知的名稱是《天主實義》。(68)
利瑪竇的態度最能體現在1583年他向兩廣總督提出准許逗留肇慶的請求。他在請願書中説,他被中國政府的盛名所吸引,他千里迢迢到來,祗為能在一間小教堂和一間房子內服務於“天主”(這是利瑪竇1583年以來一直使用的詞)。判官王泮(譯音)在看過他的世界地圖之後,批准了這個不太過份的要求。利瑪竇沒有隱瞞他的真正目的,而且還表達得很清楚:但他的要求獲得批准是因為他出示了地圖,他從未忘記他的最終目標:傳播福音和使中國皈依基督。(69)
而這種改變得從最高和最低層開始,但主要的還是要從最高層開始,傳教士將要在人群中做工作,而某些傳教士則要在統治階層工作,以保持他們對基督教的好感。當然,利瑪竇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皇帝和文人身上。利瑪竇完全明日到非説教的東西將能吸引高層。後來他坦白承認,在他獲得聲譽的六個原因之中,説教排行最後。在這些原因中,首要的是他作為外國人學會用漢語講、讀和寫;第二,是他驚人的記憶力以及熟讀《四書》;第三,是他的數學和其它科學知識:第四,是他帶來的古怪禮物;第五,是他自稱懂得學問和有煉金的經驗。(70)當然,在普通人之中,有這些學問確是與別不同。
要中國皈依基督,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優先次序是必要的。要貴族階層和普通百姓都接受基督教義或叫天主學説,首先它必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而且要把它從洋人的有害教條的清單上除名。對利瑪竇來説,“本土化”比數量更加重要。他知道這是需要時間的,但他有耐心。
他同樣醒覺到要在貴族之中實行“本土化”需要文字:書本。另外,高等階層的“本土化”並不是在教堂或禮拜堂進行,而是在書院,它在明代十分流行,(71)這正是人們學習西方學問和其它各方面知識的地方。也是交流思想,甚至非基督教思想的地方,對那些文人學者,在講到教條和信仰之前,首先要對那些能通過推理證實的信仰要素進行解釋。這是利瑪竇《天主實義》這本書的力量所在。這種漸進的過程不必在人群之中言明,但教堂仍然是他們做禮拜的地方。然而,這不意味著利瑪竇這種方法有欺騙成份,它祗不過把重點放在不同地方,它從未隱瞞或去除基督教的精髓。
“本土化”要通過一種四個層面的方法進行:生活方式、表述方式(強調觀念和概念)、道德規範、禮儀與習俗,而這些都是受意識形態所影響,要令“本土化”獲得成功,這四個方面都同等重要,但實現的難易程度不同。這四方面最不具爭議性的是第一方面,最具爭議性的是第四方面,而最關鍵和最困難的是第二方面,讓我們簡單地看一看這些文化調和方法。
生活方式。在進入中國之後,利瑪竇變成一個生活在中國人之中的外國人。(72)他接受了中國人的禮節、飲食、睡眠方式和打扮,長袖服、肩帶、腰帶、帽子和顏色。甚至連意大利人飲葡萄酒這種小習慣他都放棄,改飲米酒。他去世後,他其中一位重要朋友上書皇帝,請求説,考慮到利瑪竇的功德,應賜一塊墓地來安葬他。
觀念及表述。利瑪竇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將西方文字翻譯成漢語。這並不純粹是用詞的問題,至關重要的是將字面背後的意念傳達給中國人,例如,世界的產生是神的精心傑作這一點。利瑪竇相信,神的概念對中國人來説並不陌生,而且,他們已經是神的接受者。(73)越深入接觸中國文化人的生活,利瑪竇就越為在最古老的詩書裡所找到的中國學説基礎而感到震驚。在這些古典著作裡,簡直沒有神論,中國人也沒有像希臘人、羅馬人、印度人和大乘佛教徒一般有萬神殿,他們認為天神是屬於個人的。神要由皇帝來拜祭,百姓不能擅用這種特權。當然,皇帝除了拜祭天神之外,還拜祭山神、河神和名人,平民則被允許或促請拜祭村裡的守護神,家庭則各自拜祭他們的祖先。但所有這些神都在天神之下,因此,中國在道教和佛教之前的最原始宗教是-神教。所以,當談到真正的神或天主時,利瑪竇和他的繼承者都用中國古典著作所指的“天”或“上帝”。這與使徒們所做的不大相似,他們毫不猶豫地用希獵文中的theos一字來指舊約全書中的真神。
利瑪竇時代的儒家已經失去神的原概念,因為他們用了宋代新儒家的創新概念,把上帝和天看作與“太極”等同,太極是非人類之王,它以“氣”和“力”作為萬物之本。這些概念是在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下,由唐宋新儒家所創立,企圖為儒家思想建立玄學式的上層結構。儒學是中國的國學,起源於漢朝(206B. C.-A. D.220),隨著漢朝的沒落,它失去了信服力。結果,在唐(618-906)、宋(960-1280)之前的戰國時代(220-618),道教和佛教崛起和佔有重要地位。要恢復儒學,令它戰勝有玄學體系的佛教和道教,儒學本身也要有玄學體系。但是,正如利瑪竇所觀察到的,在發展過程中,他們同樣敗壊儒學,它已演變成,如果不算是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話,起碼是不可知論。最原始的儒學基本上是一個社會道德系統。利瑪竇和當時的新儒家展開論戰,他把天主和古典中的上帝劃上等號,並指出,上帝是個人所奉信的,而太極則是存在中的宇宙萬物。(74)
這種有關造物主的基本觀念同樣有很多伴隨而來的概念,例如,靈魂和軀體的分離、報應等等,(75)這些都引起各種不同的反響,也引起與當時新儒家思想之間的矛盾。但祗是造物主這一概念和新儒家思想發生矛盾,就傳統儒家思想而言,它同樣引起一些尖銳的問題。如果上帝創造世界和宇宙萬物,它一定也創造了中華民族。如何解釋呢? 如果中國人有了一種優越感的話,這就不僅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敏感和危險的問題了。這一點如果和基督教教條和禮儀混在一起時,問題變得很大了。
道德規範。利瑪竇和他的繼承人就新儒家的玄學和宇宙論世界觀進行辯論,並試圖將其貶抑,他們堅持,孔子的社會道德教育不僅沒有和基督教的道德相衝突,而且還能將之完善。在《交友論》一書中,利瑪竇將基督概念中的“愛”與儒學概念中的“仁”視為等同。他説,在真正的友誼中,對待別人應像對待自己一樣。(76)他還將這種概念再擴展,他説,“仁”的意思可以用兩句話來透切表達:愛上帝重於愛其它事物;愛別人如愛自己。如果人能做到這一點就會擁有所有美德。上帝對所有人同等愛戴;如果一個人真正愛上帝,他怎會不愛所有的人呢? 孔子自己也説過,仁者會愛所有的人。“不愛其他人,又怎可證明(自己)對神的愛是真呢? ”(77)利瑪竇的論點非常清晰。如果中國人能掌握對上帝的原始概念,他們將會被轉化為真正的仁者。這樣,他所説的用基督教的道德來完善儒家思想這一句話的意義就清楚了。利瑪竇和他的繼承人沒有向儒家道德體系中的各種親情(根據五種倫理關係劃分)挑戰,他們反而主張用基督教來完善儒家思想。(78)這樣,中國將能在古時的“原始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創造一個協調的、道德完整的社會。
利瑪竇為儒家們提供了一個檢驗外國人説教是否奏效的方法。如果不是一方超越另一方的話,可以説,他令基督教在道德上表現得和儒學同樣有説服力,他將基督教儒學化,或者説把儒學基督化。如果基督教要為人所接受,它將要被人們以儒學的標準來判斷和評估,在道德上,他必須是有影響力的。明代最著名的皈依基督者徐光啟(1562-1633)提出“基督教能補充儒學,替代佛教”。(79)他甚至説,西方沒有“叛亂”和“無政府”這些詞,在上帝的指引下,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生活在和諧之中。(80)這種將西方誇大為永久和平的説法並不是耶穌向他們撒謊的結果,而是徐光啟用有力的措辭來強調基督教的價值觀,以此作為道德改革的主導力量,而上帝就是這股力量的推動者。徐光啟和其它人都把利瑪竇及其追隨者視為賢人,因為他們所走的是真誠之路。
他們都是有美德的人,致力於服務社會。很多其它的中國人都覺得驚奇:這些蠻人在如此高的道德標準之下生活。祇是後來的傳教士的不道德行為傷害了傳道工作,這種傷害比任何其它傷害都大。他們不是所有人都以利瑪竇為榜樣,這可能是他估計上最大的錯誤。
禮儀。中國道德體系的核心是奉獻和服從於父母和合法的權力,至今天,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如此。這些孝心的全部或部份是對先輩的孝敬。這些先輩的名字被刻在木牌上,叫作先人靈位;人們在這位靈位面前叩頭(伏在地上,把前額向地上敲),燃點香燭,供奉食物和燒紙錢。這些行動被認為是為那些在另一世界的亡魂服務。為尊敬孔夫子,官員和文人也要做類似的工作。如果在初階段禁止這些儀式,要中國皈依基督是決不可能的。如果在中國人面前提及聖保羅命令父母們照顧他們的孩子,而不是要孩子照顧父母,定會引來極大的憤怒,這樣,傳教士就幾乎不需要再説任何東西了。
在這一點上,利瑪竇本人似乎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如果他禁止這些儀式,但祇能爭到幾個信徒。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用説,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基督徒都不許相信這些牌子就是亡魂的靈位,或者燒紙錢對已去世的人有幫助。但是,不是所有的習俗都是同一性質的。而且,事實上中國的文人都表明,他們叩拜孔子祇是為了向這位導師和典範致敬,並不表示祝願他獲得富貴、榮華和才能。也就是説,在孔子面前叩頭祇是禮貌、感恩的表現,而不是一種宗教儀式。同樣,對利瑪竇和他的追隨者來説,在先人的棺木前叩頭,或者陞官後向孔子靈位叩頭似乎是許可的。當然,在普通人之中,也有一些人做這類崇拜是希望得到富貴、子孫和其它福蔭。但在中國的古典著作中,有某些章節表明這些儀式的原始意義並非這樣;因此,從其原意和方式來看,進行這些儀式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向先人供奉食物(這些食物後來又由參加供奉的人規規矩矩地食用)祇是一種令自己有與先人在一起的感覺的方法。這一點尤其可以讓這樣一個事實地證明:“供奉”這個字的意思並不一定等於我們的to sacrifice(獻祭)這個字。(81)
如果要提防與這些儀式有關的迷信觀念的話,也有必要提防新儒家們對這些儀式的解釋,他們是朱熹(1130-1200)學説的追隨者,是唯物主義者。根據這些學説,孔子的靈魂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的祇是他的名字和記憶;人們的祖先自然也是同樣道理。如果以同樣的解釋,人們顯然不能向祖先祈求,而且也不會祈求到任何東西。朱熹對儒家著作的見解延至1552年才由朝廷正式宣佈採納:然而,人們不能忘記,雖然這種無神論或不可知論成為正式的教條,但未必能夠令文人確信,而大眾也未必同意這位學者的觀念。他們對先人的崇敬和供奉之物是宗教的行為。根據利瑪竇及其追隨者,這兩方面的錯誤都必須通過恢復古典著作中的原意來加以糾正。
利瑪竇本來也禁止這些儀式,但當他看到人們對活著的人(例如皇帝和父母)都叩頭時,他就允許對祖先和孔子的拜祭。但即使最初時這種猶豫不決的態度也產生了不良的印象,在1616年對傳教士的迫害中,這是針對他們的其中一項最嚴重的控罪。(82)一段時間之後,耶穌會士似乎認為這些儀式屬於中性,有關這些儀式的爭議和衝突祇是後來托砵僧出現後才真正發展。
利瑪竇和他的繼承者醒悟到,作這些讓步令他們處於危險的境地,這可以體現這樣一種事實:他們祇是暫時容忍這些儀式,那怕是無知者所為。利瑪竇在1603年的訓令(這是文化融合的最早模式)就很清楚地證明了這點。該訓令是耶穌會使用儀式規則的開始。也就是説,利瑪竇的意圖是從內部(中國禮儀)加速文化融合。以此過渡到從外部(西方禮儀)進行長期的文化融和。他的繼承人和康熙都明白他在這方面的意圖,這可從康熙皇帝1700年的宣言中證實。(83)這叫做“耶穌會理論”:利瑪竇和他的繼承人對由來已久的非基督教的思想和行動習慣(這些習慣從內部表現出不能容許的迷信觀念)所採取的態度。法國耶穌會漢學家安東亞尼·波萊瓦列爾(Antoine de Beauvollier,1657-1708)用一句簡短的話來為這一理論下定義:“允許這些儀式固然危險,但將之禁止更危險。”(84)
除此之外,耶穌會士對給予利瑪竇的文化融合方法一個神學的解釋“可能做法”(probabile,immo valde probabile)感到滿意。利瑪竇和他的繼承者不否認反面的意見是“較為安全”,但這正表明他們為何不像那些好戰對手那様做,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在那些覺得遵循學過的較嚴謹的宗教觀念良心會好過些的傳教士身上。然而,我們不能忘記,沒有耶穌會士的這種方法,這些對手將無法在中國立足。因此,我們可以説,耶穌會理論是在基督教道德準則允許的合理前提下的一種平衡的半辯證法,它是要在中國傳播福音的必然做法。當然,在那個世紀的進程中,在耶穌會的各階層裡,會偶然出現一些不同意見者,而其它人則會將證據大大地加以豐富(那些相信者)。絕大多數的耶穌會漢學家都認為利瑪竇的文化融合是一種“可能做法”,而唯一不贊成整個方法的是卡羅德·達·威斯特魯(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8)。(85)
在利瑪竇去世(1610)至托砵僧出現(1632)這段期間,關於他的文化融合的各個方面,在耶穌會會士中有過熱烈的辯論。圍繞著基督教用語和詞義,尤其是“上帝”一詞的辯論最激烈。1600年,范禮安同意了利瑪竇的用詞。對於用詞最早表示有保留是來自日本的耶穌會士。在那裡,傳教初期,這個問題已經出現。如前所述,沙勿略曾經用Dainichi(多神論的真言宗佛教徒用語)來指上帝。其它用詞有jodo(樂園),jigoku (地獄),tennin(天使)等等。沙勿略醒覺到自己的錯誤後,再不使用這些用語,而耶穌會士在以後的五十年都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最後決定用傳統的拉丁文或葡文用語來表達基督教概念。(86)在發生過不幸的Dainichi事件之後,用拉丁葡文就顯得更加安全。日本當時是頗容易受影響的,因為這個國家當時正處於兩敗俱傷的戰爭痛苦之中,因而產生了一個開放的社會,願意以西方形式接受基督教,同時也願意接受槍砲和貿易。
然而,中國是一個封閉的社會,一個孤立的國家,不願意打開她的大門,直至利瑪竇推行文化融合。因此,當他選擇自己的表述方法,以及當他的作品到達日本時,耶穌會士感到困擾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不明白,這個問題在中國和在日本是有所不同的。他們向設於澳門的耶穌會東亞總部表達了他們的憂慮,而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就是從澳門獲悉這些憂慮的,繼承利瑪竇中國耶穌會傳教主管職位的尼哥羅·倫哥巴地(Niccolo Longobardi,1565-1655)同意日本耶穌會士的意見,就利瑪竇的用詞和詞意的正確性在學者之中進行了一次調查,並且出版了一本含有他所下結論的書。(87)另一位與利瑪竇意見不同的同事是塞巴斯蒂奴·德·尤亞西斯(Sebastiano de Ursis,1575-1620),雖然其它同事例如圭里奧·阿倫尼(Guilio Aleni,1582-1649),阿爾瓦羅·德·塞門多(Alvarode Semedo,1586-1658)和尼哥拉斯·特里哥爾特(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都支持利瑪竇。這種爭論由1610年持續到1633年。God這個詞最後被確定為“天主”,因為它的使用不會破壊正統性和清晰性,利瑪竇從1583年開始使用這個詞,中國的基督教徒也一直沿用。然而,這樣一種妥協並不意味著“上帝”或“天”這個詞是不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倫哥巴地的書在1635-1641年被耶穌會副大主教弗朗西斯科·福爾多都(Francesco Furtodo,1589-1653)禁制,但卻保留在中國禮儀的反對者多明哥·弗爾南德斯·德·納瓦雷德(Domingo Fernandez de Navarrette,O. P. ,1618-1686)的《歷史性的條約》(Tratados históricos)這本書中。(88)雖然倫哥巴地的結論與利瑪竇的有所不同,但他最終接受了這位耶穌會士的政策和方法,並沒有作出反抗。這種誠實的異見最後終於獲得解決。這和亞豐索·瓦格諾尼(Alfonso Vagnoni,S. J. ,1586-1640)的情況相似,他是南京傳教團的主管,他在利瑪竇去世後背離他對非直接傳道的堅持。可能受了那些中國以外的,不相信數學和天文學是傳播基督教的聰明方法的人影響,他在該城市設立中國第一個公開教堂和進行禮拜活動,其鋪張令人覺得他有點不智。這些,再加上因他而起的對佛教僧侶的批評,引起了敵對情緒,而且很快就發展到危險的程度。一個新任禮部副官於1617年發起一場運動,結果禮部發出告示,禁止在中國宣揚和信奉基督教,(89)該法令在南京嚴厲執行。當時瓦格諾尼和塞門多兩位當地僅有的耶穌會士被逮捕;瓦格諾尼被判蹠刑,然後他和塞門多就被放在籠裡運到廣州,再驅逐出境。在短暫的流亡生活裡,除了做其它事情外,他就專注於中國古典著作的學習和文言能力的提高。他能夠很有技巧地書寫漢語,他寫的有關基督教義的著作是早期的耶穌會士最有效力作之中的一部份。
還有其它一些像瓦格諾尼的耶穌會士懷疑是否數學、天文學和其科學是傳揚該宗教信仰的適合工具。他們反對利瑪竇的西學方法。例如,日本大主教瓦倫丁·卡瓦略(Valentim Carvalho,1559-1630)和日本、中國巡察員安德烈·帕爾梅羅(André Palmeiro,569-1635)兩人都曾一度禁止這種做法,直到一些誤會得到澄清為止。(90)
1632年托砵僧傳教士的到來使情況又有了新的發展。這些傳教士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融合的兩個方面:生活方式和禮儀。在第一方面,他們批評耶穌會士的生活方式、教規、教義和傳教用語,例如,未能頒佈基督教法律、誡律、主持聖禮的方法不對頭,未有宣傳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耶穌會士們強調他的美德),穿著中國服飾,拒絕宣傳孔子在地獄的説法(可用三段論法證實,如傳教士納瓦雷德所嘗試的)。在第二方面,他們批評某些中國人遵守的禮儀,如拜祭去世不久的家人、祖先和孔子,還有祖先靈牌和刻著孔子名字的靈牌。曾有一段時間,禮儀的問題成了注意力的焦點。從那時起,就有“中國禮儀”(Chinese Rites,R大寫)這個詞出現。
但為甚麼托砵僧傳教士姍姍來遲? 因為於1585年1月28日,正是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兩年之後,教皇格列高是十三世在他的訓令(Brief Ex Pastorali Officio)中禁止其它分會進入中國,以避免分歧,允許耶穌會士試行文化調和的方法。(91)然而,該法令壽命並不長久,因為教皇斯克杜斯(Sixtus)五世在1586年11月15日將它廢止並允許聖方濟各會士到中國。(92)該法令的廢止得到這些教皇們的確認:克里特八世(1600年12月12日),保羅五世(1611年)和烏爾班八世。(93)因此,聖方濟各修士終於能在1632年進入中國。安東尼·德·聖瑪利亞·卡巴雷羅(Antó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 F. M.)和胡安·班第斯特·德·摩拉勒斯(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O. P.)於次年到達。這標誌著聖方濟各會士和耶穌會士因基於不同傳道方法而引起的爭端的開始。
雖然禮儀之爭不限於本文所描寫,但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雖然有各種變更,但它迫使耶穌會士用利瑪竇的文化融合方法,尤其是他謹慎和循序漸進的方法,來創造足夠的、在短期内達到成功所必備的要素。1692年,基督教最終可以在有害宗教的清單上除名,和像幾個世紀以前落地生根的佛教(源於印度)一樣,變成本土化。基督教可以立足要歸功於康熙皇帝的“寬大詔書”(94)(意譯,1692)和“一份關於中國禮儀習俗意義的宣言,根據這份宣言,耶穌會到目前為止仍然允許這些禮儀習俗,這是作為條件於公元1700年11月30日向康熙皇帝提供的。”(95)
利瑪竇原想一到北京就親自去見萬曆皇帝(r.1573-1620),以便直接獲得在中國傳播福音的許可,但當他獲准到北京居住時,他又覺得沒有必要,因為準許在北京居留意味著默許他和他同伴繼續生命的歷程和傳道的職責。但前提條件是耶穌會士不破壞那些寶貴的中國傳統習俗。他們將以此為準則,帶著同情和諒解,竭盡所能,作好準備,讓神的美德能活在那些他們所希望爭取的皈依者的心靈上。如前所述,傳教的重點是要完全放在質量上,而不是以皈依者數量多為榮。這一點是利瑪竇在寫給澳門的信中所陳述的,當時他被催促向皇帝請求明確授權。後來他説,當天子教徒在讀書人之中數量增加時,就有可能獲得傳教的許可,因為在中國沒有法律禁止傳教;他們應該等待,看看是否有必要獲得許可,直到真正有必要時才這樣做。約一百年之後,也就是17世紀的最後十年間,這種許可變得真的有必要,當時禮儀之爭端達到高潮。或者是因為這樣,他的繼承者覺得需要獲得“寬大詔書”和康熙的“聲明”。
雖然中國已經正式接受了利瑪竇的文化融合方法,歐洲卻在18世紀將之拋棄。(96)正是禮儀爭端期間歐洲人自己的行為暴露了利瑪竇文化融合方法中内在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最大弱點,這就是低效應的倫理道德體系。利瑪竇已經勾畫出一幅以基督教來完善儒家思想的樂觀圖畫。他是一個樂觀者,他相信人類的理性可以超越和克服種族、民族和語言偏見這些自我規限所產生的非理性。他遵循耶穌基督的命令:“去吧,去每一個有人的地方,令他們都成為我的信徒:以上帝的父子和聖靈的名義為他們洗禮,教他們服從我要你們做的每一件事,我任何時候都在你們身邊,直至天荒地老。”(97)縱然利瑪竇的文化調和方式有很多問題和缺點,現在是時候嘗試這一方式和留意耶穌會士比爾拉·太拉特·德·查爾甸(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忠告:“民族的時代已經過去,如果我們不想滅亡,就要摒棄過往的偏見,共同建設這個世界。”(98)
曾澤瑤譯
【註】
(1)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1689);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巴雷拉日記)(Rome,1961),頁83-86;C. Raymond Beazley的兩本著作:Price Henry the Navigator: The Hero of Portugal and of Modern Discovery,1394-1460 A. D.(航海家亨利王子:葡萄牙和現代發現的英雄,1394-1460 A. D.)(New York,1895)及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現代地理學的黎明),3 vols (London,1897-1960):Joaquim Bensaude 的三本著作:Lacunes et surprises de l'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maritimes,1e parties (Coimbra,1930), A cruzada do infante d. Henrique (Lisbon,1942),及Legendes allemandes sur I'histoire des decouvertes martitimes portugaises: réponse à M. Hermann Wagner, 2 vols.(Genva,1917-1920)。請同時參看Armando Cortesão的編譯本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托馬斯·比利斯的東方洛要和法蘭斯高·羅德利利格斯的書),2 vols. ,(London,1944);Adelhelm Jann,O. F. M. Cap.,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and Japan. Ihre Organisation und das portugiesische Patronat vom 15. bis ins 18. Jahrhundert (Paderborn,1915);António da Silva Rego,Ó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esbôço histórico(Lisbon,1940)。
(2)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頁84。
(3)同上,頁85。
(4)Jacqes,Gemet,A Histotry of Chinese Civlization,(中國文明史),J. R. Foster的譯本(Cambridge,England,1985)頁448-49。
(5)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頁85-86。其他國家都(以不同方式)委婉地使用有關國土擴張的口號。西班牙人用“黃金,榮耀和福音”;後來法國人用“LaMission Civilisatrice”:俄國人用“戰爭和貿易”:“白人的包袱”就起源於英國人:“命定擴張”在美國人中就十分流行;而在20世紀,納粹德國就創造了“生存空間”這個口號。
(6)Sebes,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頁85-86。
(7)同上,頁90-91。
(8)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頁85-86。Jan J. L. 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1949)。
(9)Sebes,Jesuits and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頁86。
(10)Prefce I for Sundays,Roman Missal,l Peter 2:9,elaborating from Exodus 19:6.
(11)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四傳註釋,Yenching Joumal of Chinese Studies(一本研究雜誌),論文系列之七(北京,1934),頁139。
(12)JohnD. Young,East-West Synthesis:Matteo Ricco and Confucianism (東西方交融:利瑪竇及儒家思想)(香港,1980),頁1-2。
(13)António da Silva Rego,Courso de missiologia(Lisbon,1956),頁361。
(14)Georg Schurhammer,S. J. 及Josef Wicki,S. J. ,eds., 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jus Scripta,nova editio,2 vols. Rome,1944-1945,2:16。請同時參看Georg Schurhammer,S. J., Fracis Xavier,His life,His Time(方濟各·沙勿略的生命及其時代),M. Josdph Costelloe,S. J. 的譯本,4 vols. (Rome,1973-1982)。
(15)Schurhammer及Wicki,Epistolae,2:373;Henry J. Co1eridge,S. J.,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聖方濟各的生活及書信),2 vols.(London,1912),2:241-42頁。
(16)Michael Cooper,S. J. Rodrigues the Intepreter. An EarlyJesuitinJapan and China(翻譯員羅德利格斯,早期日本中國的耶穌會士),(New York,1974),頁284-86。
(17)Young,East-West Synthesis(東西方交融),頁4-5。。
(18)Coleridge,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聖方濟各的生活及書信),頁2:369。
(19)同上,頁2:300-301。
(20)同上,頁2:338。
(21)Schurhammer及Wiki,Epistolae,2:373,Young,East-West Synthesis(東西方交融),頁5-6。
(22)Ludwig von Pastor,Geschichte de Päpste seit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16 vols. Rome,1948),(Freiburg im Breisgau,1891-1933),頁15:284-85。
(23)Schurhammer及Wiki,Epistolae,2:373;Josef Wicki,S. J;ed. DocumentaIndica,17 vols. Rome,1948,13:5-13;Young,East-West Synthesis(東西方交融),頁6-7。
(24)Pastor,Geschichte der Päpste,頁15:284-85。
(25)Sebes,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中俄涅爾琴斯克條約),頁39-42;Wiki,Documenta Indica,頁4:106-8,頁12:950-69。有關明代資料請參看Albert Chan,The Glory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明朝之盛衰)(Norman,1982)。
(26)Schurhammer及Wiki,Epistolae,頁2:483-88,497-501,513-15。
(27)Pasquale M. D'Elia,S. J. ,ed. Fonti Ricciane:Documenti Origind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e la Cina 1579-1615,3 vols.(Rome,1942-1949),頁1:139-40;Albert Herrmann,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中國歷史及商業地圖集),(Cambridge,1935),頁56,C3;PaulPelliot,“UnOuvrage sur les premiers temps de Macao,”T'oung Pao,31(1934-1935):71n.2;張維華的註釋,頁138。
(28)Chronicon Societatis Jesu,in Johannes Alphonsus de Polanco,S. J;Vita Ignatii Loiolae et Rerum Societais Jesu historia,6 vols. (Rome,1894-1898),4 (anno 1554):652,5 (anno 1555):頁715-23。
(29)Emmanuel da Costa,S. J. ,Rerum a Societate Jesu in Oriente gestarum ad annum usque a Deipara Virgine MDLXVIII,commentarius,trans. Giovanni Maffei,S. J.(Dillingen,1571),fols.107v-114v;Melchior NunesBarreto 1555年11月23日寫給在印度,葡萄牙和羅馬教友的信,Diversi avvisi particolari dall'Indie di Portogallo ricevuti dall'anno 1551fino al 1558(venice,1558),fol.271 v. 請同時參看Nunes Barreto在交趾寫給耶穌會會長的兩封信:(1)1558年1月8日,存於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es Iesu(羅馬耶穌會檔案,以下簡稱ARSI),Japonica et Sinica(日本和中國部分,以下簡稱Jap-Sin.),4:fols. 頁82-89;(2)1558年1月13日,ARSI,Jap-Sin. ,4:fols. 頁90-94。
(30)C. R. Boxer的編譯本,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6世紀的南中國)。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Fr. Gaspar da Cruz,O. P;Fr. Martin de Rada,O. E. S. A.(巴雷拉,達克羅斯,拉達的故事),1550-1575(London,1953),lix,頁122。同時參看Chronicon (1555) in Polanco, Vita ignatii,loiolae,5:723。
(31)1562年12月10日加哥寫給在交趾的神父及教友的信,ARSI,Jap-Sin,4:fols. 頁290-98v。
(32)1562年12月29日蒙特(從澳門)寫給羅馬耶穌會神父的信,ARSI,Jap-Sin,4:fols. 頁311-12r。
(33)佩雷斯(從澳門)寫給這些人的信:(1)一名在果亞的耶穌會士,1564年1月3日;(2)耶穌會主教Diegolaínez,1564年12月3日;(3)Luis Gonsálvez神父,1564年12月3日。同時參看持舍拉1564年12月3日寫給果亞耶穌會士的信。所有的信都可在ARSI,Jap.-Sin.5:fols.101,152ssr56r,161r-62v,164r-69r頁内找到。同上,果亞部份,38:fols. 頁284r,292r。
(34)ARSI,Jap.-Sin,6:fols. 頁86r-87v,1565年11月3日伊斯哥巴(從澳門)寫給特舍拉的信的意大利文譯本。請看Pasquale M. D'Elia,S. J.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e relaza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prima dell'arrivo di P. Matteo Ricci,S. J.(1582),”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6(1936):頁223-26。
(35)D'Elia,Fonti Ricciane,頁1:140。
(36)貝雷拉(從澳門)寫給波吉亞的信,1568年10月,ARSI,Jap-Sin,6:fols. 頁236r-40r143
(37)Wiki,Documenta Indica,頁8:580,烈拉必須和雷貝拉一同到澳門。
(38)Organtino Gnecchi-Soldo. S. J.1569年10月29日(從澳門)寫給Luis Madrid,S. J. 的信,ARSI,Jap-Sin,6:fols. 頁257-58。同時參看Joseph de Moidrey,S. J;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en Corée et au Japon 1370-1914。Variétés sinologiques,no.38(Zi-Ka-wei,1914),頁6.1555年1月卡内路被任委為尼西亞主教和埃塞俄比亞副主教。和主教一樣,他從未成功到達埃塞俄比亞。在6月份(ARSI,Jap-Sin,6:fols. 頁240),他到達澳門,作為中國、日本的主教,但不是澳門的主教,澳門教區是在1576年才建立的。參看D'Elia,Fonti Ricciane,1:153.5。在到達澳門後不久,卡內路試圖放棄主教職位並休養於耶穌會一間屋子內,但未能成功,直到1582年1月才能如願。他於1583年8月19日在澳門去世。請同時參看Catálogo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xistentes en el 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 por D. Pedro Torresy Lanzas y Francisco Navas del Valle,y precedido de una erudita historia general de Filipinas por el P. Pedro Pastells,S. J.8 vols.(Barcelona,1925-1933),2:CLIX。
(39)Giovanni Francesco Stefanoni,S. J.1574年10月6日(從日本Goto)寫的信,ARSI,Jap-Sin,7,I:fols. 頁241 r。
(40)1575年1 1月7日達高士德(從澳門)寫給主教Everard Mercurian神父的信,ARSI,Jap-Sin,7,II:fols. 頁291-92v。
(41)雷貝拉1575年10月18日(從里期本)寫給主教Everard Mercurian 神父的信,ARSI,Jap-Sin,7,I:fol. 頁287r。同時參看Moidery,Hiérachie catholique,頁6。
(42)Boxer,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6世紀南中國),頁19。
(43)1579年11月20日Francisco Chávez,S. J.(從馬六甲)寫的年報信,ARSI,果亞部份,38:fol. 頁177r。
(44)D'Elia,Fonti Ricciane,頁1:141。
(45)1581年10月25日澳門教區長Domingo Álvarez寫給主教神父的信,ARSI,Jap.-Sin;9,I;fol頁49r。
(46)D'Elia,Fonti Ricciane,1:142,頁156。
(47)1582年7月3日Alonso Sanchez(從澳門)寫給主教Everard Mercurian神父的信,ARSI,Jap-Sin,7,Ⅱ:fols. 頁291-92v。
(48)D'Elia,Fonti Ricciane,1:142,頁67。
(49)同上,頁1:142。
(50)同上。
(51)同上。
(52)Wiki,Documenta Indica,頁13:195-201。同時參看José Maria Braga的兩本著作,O primeiro accordo Luso-Chinês realizado por Leonel de Sousa em 1554(Macao,1939)及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西方開拓者及澳門的發現)(Macao,1949)。同時參看C. R. Boxer的兩部著作,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1550-1770 遠東貴族:澳門歷史和事實和聯想)(The Hague,1959),頁1-9,及The Great Ship from Amaca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從澳門來的巨船:1555-1640澳門與古代日本貿易)(Lisbon,1959),頁1-11。
(53)Wiki,Documenta Indica,頁7:504-6。
(54)有關范禮安的生平和工作,請看Josef Franz Schütte,S. J. 的三部作品:(1)Valignanos Missionsgrundsätze für Japan I Band. Von der Ernennung zum Visitator bis zum ersten Abschied von Japan(1573-1582);Ⅰ. Teil: Das Problem(1573-1580) (Rome,1951).Ⅱ. Teil: Die Losung (1580-1852)(Rome,1951-1958);(2)Introductio ad Historiam Societatis Jesu in Japonia 1549-1650(Rome,1968);(3)Die Wirksamkeit der Päpste für Japan im ersten Jahrundert der japanischen Kirchengeschichte(1549-1650).Versuch einer Zusammenfassung (Rome,1967).
(55)Henri Bernard-Maitre, S. J.,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aires du Zeiziéme Siécle,1514-1588(天津,1933),頁141。
(56)Arsi, Jap.-Sin.,9, I: fols. 頁149-150v; Wiki, Documenta Indica, 頁11:550-51,572-74。
(57)參看Alexandro Valignano,S. J. ,I1 cerimoniale per i missionari del Giappone,ed. Josef Franz Schütte,S. J.(Rome,1946)。
(58)Knud Lundbaek,“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儒家古典著作歐洲第一個譯本),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Bulletin 1(中國傳教研究〔1550-1800〕書刊,之一)(1979):頁1-11。有關羅明堅的資料,參看D'Elia,Fonti Ricciane,頁1:141-49,以及Louis Pfister,S. J. ,Noc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2 vols.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s.59 and 60(上海,1932-1934),頁1:15-21。
(59)這些耶穌會士為桑切斯及其同伴,桑切斯本人1582年7月2日(從澳門)寫給耶穌會大主教的報告,請看ARSI,Jap-Sin,9,I:fols. 頁87-93v。
(60)ARSI,Jap-Sin,9,I:fols. 頁149-50v。
(61)有關利瑪竇的資料,請參看D'Elia,Fonti Ricciane,1:CICXXXV;Pfister,Notices,1:22-42;Nicolas Trigault,S. J. ,ed;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1583-1610(16世紀中國:利瑪竇日記1583-1610)Louis Gallagher,S. J. 的譯本,(New York,1593);Pietro Tacchi Venturi,S. J.,ed;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S. J;2vols.(Macerata,1911-13)。從這裡開始,本文包含了本作者在“Matteo Ricci Chinois avec les Chinois”,Études,357(1982年10月):361-74中的資料。
(62)ARSI,Jap-Sin,9,I:fols. 頁112-13v。
(63)同上,fols. 頁112-3v。
(64)派出大使的想法一直是沙勿略及其繼承者在書信中的主題。參看Schurhammer及Wicki的Epistolae,頁2:358-64,453-63,468-75,483-88,497-501,513-16,516-21。同時參看Wicki,Documenta Indica,2:510-20;3:119-28,163-69,245-54,449-51;5:160-88,238-46,250-65,315-18,398-23,481-87,693-99,719-22,722-25,737-47,752-58;6:69-77,103-28,508-18,22-29,660-62;7:207-12,486-94;11:727-41;12:950-69。同時參看ARSI,Jap-Sin,4:fols.76-81v,90-94v,290-98v,311-12;5:fo ls.101r-v,152-56,161-62v,164-69;6:fols.93-99v,9,I:fols.58-61v,112-13v。羅明堅指出了外交使團和貿易使團的分別。他認為,以往的使團失敗是因為他們是貿易使團。他促請派遣外交使團。參看1581年11月12日羅明堅(從澳門)寫給主教Everard Mercurian神父的信,ARSI,Jap-Sin,fols. 頁58-61v。
(65)Wicki,Documenta Indica,頁4:160-88,673-714;7:207-12,486-94;9:661-69,696-708;10:662-83;13:1-134,134-319。ARSI,Jap-Sin,6:fols. 頁211r-v,234-35v,236-40;7:fols.241-43v,8I:fols.280-82v;9,I:fols.49-50v,130-32v。西班牙和葡萄牙為東印度群島問題的戰爭同樣引起關注。參看:《Wicki,Documenta Indica》,頁7:157-61;9:644-49,669-71;10:509-15。同時參看C. R. Boxer:《Portuguese and Spanish Rivalry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葡萄牙和西牙17世紀遠東之爭),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 and(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學報),第三部份(1946年12月):頁150-46,第四部份(1947年4月):頁91-105。
(66)ARSI,Jap-Sin,9,I:fols. 頁137-41v。
(67)Jacques Gernet,Chine et Christanisme. Aciton et reaction(Paris,1982),頁36,54,81-89。
(68)同上,頁16-17,同時參看四庫全書註目提要,(Imperial Catalog),24,第二部份。本作者有一文章簡評天主實義:《The Summary Review of Matteo Ricci's Tíen-chu shih-i in the Ssu K'u ch'ü-shu tsung-mu t'íyao》,(簡評四庫全書註目提要中利瑪竇的天主實義),A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53(1984):頁368-91。
(69)D'Elia,Fonti Ricciane,頁1:108-83。
(70)Tacchi Venturi,Opere storiche,頁2:209-9。Gernet,Chine et Chirstianisme,頁29。
(71)Emil Zürcher:《The 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in China》,(Nanking 1616-1621)(中國首次反基督運動,〔南京1616-1621〕),Acta Orientalia Neerlandica 1970年5月8至9日在來登召開的荷蘭東方學會50週年大會資料匯編,ed. P. W. Pestman(Leiden,1971),頁192-93。
(72)另一位耶穌會士Pedro Gómez在去日本的途中,把這種精神表達得很好,他寫道:“我都快50歲了,但我向神父坦白,我在重新學每一樣東西,就如我剛進這個界時一樣:我正在學習飲、食、臥、坐、穿衣、著鞋、待人接物:我在學習禮節、字母、語言和生活。顧主賜我孩兒身,賜我智慧,將我變作不懂説話的小孩。據我所知,那些準備去日本的人都必須放棄他們從歐洲帶來的衣飾和習慣,接受日本那一套,因而,我們不需要把日本人改變,但要改變我們自己來迎合他們,以便帶他們到我們的聖靈和信仰。”這是Gómez於1582年6月5日(從澳門)寫給耶穌會大主教的信,ARSI,Jap.-Sin;9,I:fols. 頁856-85v。
(73)後來,一些相信耶穌在聖體内僅是形象性存在的耶穌會傳教士嘗試用獨特的方法證明這一點。同時參看John W. Witek,S. J. ,Contra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J.(1665-1741)(中國和歐洲的觀念衝突:耶穌會士吉弗朗哥斯·科克特傳記〔1665-1741〕)(Rome,1982),頁143。-44,148-51,179-80,300-308,332-35。這對於抵銷歐洲人的民族優越感和認為自己是神的啟示的唯一接受者的優越感是很重要的。早期的耶穌會士堅持,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屬於白人種族。沙勿略於1552年1月29日在交趾寫的兩封信中強調了這一點:一封寫給依納爵·羅耀拉,另一封寫給耶穌會的其它成員。參看Schurhammer及Wicki,Epistolae,分別為頁2:29 l92,277。同時參看范禮安1577年12月8日寫於馬六甲的印度簡要。參看Wicki,Doncumenta Indica,頁13:5。後來其他人都追隨他們。
(74)Gernet,Chine et Christianisme,261-90頁。
(75)同上,頁198-230。
(76)參看利瑪竇交友論,1b如楊氏的East-West Synthesis(東西方交融)所引用,頁46。同時參看PasqualeM. D'Elia,S. J. 的兩篇文章:(1)“II Trattato sull'Amicizia. Primo Libro scritto in Cinese de Matteo Ricci,S. J.(1595).Testo Cinese. Traduzione antica(Ricci)e moderna (D'Elis). Fonti,Introduzione e Note,”Studia Missionalia 7(1952):425-515;(2)“Further 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Monumenta Serica 15(1956):頁356-77。
(77)利瑪竇,天子竇義,下卷,頁46-48,如楊氏的East-West Synthesis(東西方交融)頁44-45所引用。。
(78)同上,頁48。
(79)同上,頁44,68n.11 puju i-fo。
(80)同上,頁48。
(81)Jame Legge,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中國宗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比較)(New York,1881)頁53。Legge還説 :“中國人的‘祭’字比我們的sacrifice一詞意義要廣泛得多……它最廣泛的意義體現在:它是一種獻祭,人們通過它與靈界溝通”(頁66)。
(82)Zürcher,“First Anti-Christian Movement”(首次反基督運動),頁129-93。
(83)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s. v.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新天子教百科全書,“中國禮儀之爭”)(by FrancisA. Rouleau,S. J.)
(84)Antoine Beauvollier,S. J;“Éclaircissements〔sur la Controverse〕de la Chine 1702)”,存於巴黎巴耶穌會檔案的未出版手稿。Fond “Rites Chinois”(文章3,33-126)。有關這些資料,本作者感謝已故Francis A. Rouleau,S. J. 神父。
(85)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s. v.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新天子教百科全書,《中國禮儀之爭》)。同時參看Francesco Brancati (Brancato), S. J.(1607-1671), De Sinensium ritibus politicis acta seu responsio apologetica ad ER. P. Dominicum Navarette Ordinis Praedicatorum,2 vols.(Paris,1700),頁2:185。引用Johann Adam Schal von Bell, S. J.(1592-1666)的話,Brancati寫道:"Quamquam illud quod hactenus Patemitates Vestrae (patre Dominicani) secutae sunt, et magis probalile est et tutum. nostrum tamen porbabiliate non caret, atque omnino illud sequi convenit."Brancati又説:"Nemo ex nostra Societate umquam condemnavit practicam opinionem Patrum aliorum, nam bene nvimus nostram opinionem non esse demonstrationem, sed contineri intra limites opinionis probabilis. ”這些資料也是來源於Rouleau神父的檔案,這些檔案存於加洲三藩市大學中西文化歷史研究院內。
(86)Cooper,Rodgrigues the Interpreter(鄱譯員羅德利格斯),頁284-86。
(87)Gemet,Chine et Christianisme,頁19。倫哥巴地的書《Traité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
(88)Gemet,Chine et Christianisme,頁19。請注意,在傳教士被捕期間,在廣州召開一次會議(1669年11月29日)上,所有在中國的傳教士、耶穌會士及非耶穌會士,包括多明尼克修士納瓦雷德都同意了耶穌會的禮儀規則(Praxes)。這次拘捕是由於一次對傳教士的迫害行動所致,稱為“四攝政”迫害。這次行動由楊光先(1597-1669)於康熙年幼時發動。有關這次事件的資料,請參閲本作者於1977年10月6日發表的,但尚未出版的《Hi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Old China Mission,17th and 18th Centuries:An Attemptat Cu1tural Accommodation》(17,18世紀中國耶穌會士傳教歷史:文化調和的嘗試),頁14-15。該論文的節錄以“China'sJesuit Century”(中國耶穌會一世紀)為題在The(Wi1son Quartely)Winter 1987)發表,頁170-83。
(89)有關這次迫害,請參看Zurcher,“FirstAnti-Christian Movement”首次反基督運動,頁185-95。
(90)Gernet,Chine et Christianisme,頁34。
(91)Jann,Die katholistchen Missionen,125-26;Otto Mass,O. F. M. Die Wiedereröffnung der 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 in der Neuzeit (Münter,1926),頁77;George H. Dunne,S. J. ,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一代巨人:耶穌會士在中國明代最後幾十年間的故事)(NotreDame,1962),頁231。
(92)Mass,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頁77:Dunne,Generation of Giants(一代巨人),頁234。
(93)Mass,Franziskanermission in China,頁77;Dunne,Generation of Giants(一代巨人),頁234-35。
(94)“TheEdict of Toleration”or“Edictin Favor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寬大詔書”或“尊重天子教詔書”〔意譯〕),1692年3月17至20日。參看黃伯祿,S. J. 聖教奉褒,(上海,1904),頁115b-116b。
(95)兩份文本可在ARSI,Jap.-Sin;165:fols.188 et seq. 內找到。
(96)曾經有四次:(1)教皇克里門十一於1704年11月24日頒佈的訓令Cum Deus Optimus;(2)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在南京所作出的譴責;(3)教皇克門十一世在1715年3月19日的Ex illa die中同意Tournon的行動;(4)教皇賓尼迪克十四世在Ex quo singulari強烈譴責中國禮儀。
(97)馬太福音,頁28:19-20。
(98)"L'âge des nations est passé. II s'agit maintenant pour nous, si nous ne voulons pas périr, de secouer, les anciens préjugés, et de construire la Terre."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 J.,Oeuvres de Pierre Teilhare de Chardin. Vol.6, L'Énergie humaine(Paris,1962),頁46。
*Joseph Sebes,S.J.,喬治敦大學歷史學退休教授,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院“Monumenta Sinica”主編,發表過很多文章,其中著名的有《耶穌會與中俄尼布楚條約》(1689)《托馬斯·佩雷拉S.J.日記》,《東西方交融(East Meets West):耶穌會在中國,1582-1773》(由Charles E.Ronan,S.J.和Bonnie B.C.Oh編輯,芝加哥,羅耀拉大學,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