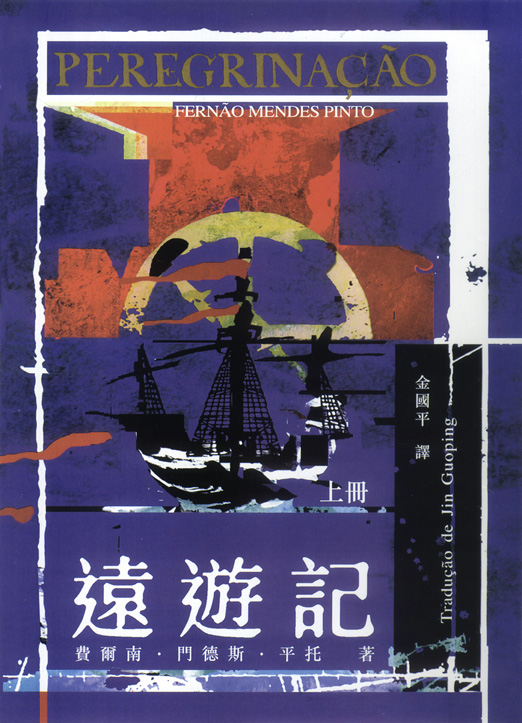
1999年6月澳門出版的平托《遠遊記》中譯本封面 澳門土生葡人畫家馬偉達官 (Victor Marreiros)設計
一
正德十六年(1521),中葡屯門之役及嘉靖二年(1523)茜草灣之役後,葡萄牙商人的主要貿易活動已轉移到閩浙海上,這應是不爭的事實。關於這一時期葡商在浙海活動的研究,論著者不可謂少,西賢從龍斯泰、徐薩斯、白樂嘉到博克塞均進行過有關研究,東方學者則有周景廉、張天澤、藤田豐八、方豪、張增信諸人結合中葡文獻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考證(1),特別是方豪先生先後五次撰文對葡人在寧波的活動作過極有説服力的考證(2),完全可以確定浙江寧波海面曾是16世紀中葉來華葡萄牙人的貿易據點之一。然而,我們發現大多研究者,特別是今天從事中葡關係史及海外貿易史研究的學者,在研究這一問題時,并沒有做史源的考證清理,即平托《遊記》中葡萄牙商人在Liampo貿易紀事之資料是否真實可信。很多人根本不顧這些,將平托《遊記》譯文輾轉抄引。雖然從龍斯泰起,大多數研究澳門歷史的西方學者都對平托《遊記》中的相關記錄表示信任,但仍有不少學者表示懷疑,法國漢學家高迪愛直斥平托之書為“妄言”;戴遂良則稱平托為“可憐的權威”;裴化行則平托之書表示極大的不信任,稱之為“小説式的記錄”;德人舒拉曼則稱其書為“謊造而不足置信”;英人康格里夫稱平托為“天大的騙子”;日人藤田豐八對其書基本不信,稱其為“誇張之言”;博克塞教授雖然徵引平托資料,但所持態度甚為小心謹慎。R. M. 洛瑞羅的編選葡文史料時,雖然也編選平托《遊記》,但他認為,平托對“葡萄牙人的Liampo市”的描寫所依據的資料來自於後來的澳門。(3)張天澤是對平托《遊記》評價最詳細者,他除了罵平托是一個“吹牛大王”外,還對他的Liampo紀事有一整體的評價:
在我們對門德斯·平托這一記敘作出任何歷史性評價之前,必須對其著作的性質有一個總的看法。在仔細閱讀了他的這部二百二十六章的著作,任何理解能力強的讀者都會說,這不過是一部長篇冒險故事罷了。門德斯·平托在亞洲度過幾年之後,把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冒險行為都作為自己的題材,這是因為他們最能使其國內的同胞想入非非。由於他感到興趣的主要是講令人著迷的故事。因此他并不關心實際上發生的是些甚麼。他所説的許多事情同已經肯定了的事實恰恰相反,而更多的是些無法查對的事。有許多稀奇古怪的人名和地名無從考證,這些名稱或許是在作者的腦子裡存在著。因此,我們顯然不能信以為真地從這樣一部份書籍中收集我們的資料。
此外,我們在任何中文記載或編年史內,以及任何嚴肅的葡文資料中,都未見過片言隻語或者甚至是隱隱約約地提到1542〔當為1548〕年前後在寧波在任何重要的外國殖民地,更不要說一場對外國人的大屠殺了。中國的歷史家或編年史家對一萬二千人遇害和鉅額財產被毀的這麼一場大屠殺竟會毫無記載,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儘管我們對平托作了上述評價,但若認為整部《遊記》純粹是小說,那也未免講得太過份了些。正如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在其敘述中國人搗殺葡萄牙人在泉州的一個殖民地的故事中,可以發現一些歷史真象。如果有飽學之士願意查明這部長篇冒險故事有多少真實性的話,那麼學術界將感激不盡。(4)
一方面是不斷地有學者在否認平托《遊記》作為歷史資料的可靠性,但仍然是不斷地有研究者對平托《遊記》之記錄不作任何辨析考證就大量徵用。我以為,這種現狀應該結束,要使用平托的資料,必須要首先完成對平托《遊記》資料進行系統清理,一定要清楚地分辨出平托所記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
本文不對平托整部作品展開研究,僅就平托《遊記》中關於葡萄牙商人在浙江Liampo(寧波)貿易活動的有關記錄進行一些考證。考證的對象亦不是平托所記葡人在寧波活動的故事情節和場景細節,而主要是:1)葡萄牙人是否如平托所說曾在Liampo建有一個貿易據點;2)這個貿易據點究竟有多大的規模,性質如何,是否與平托所言吻合;3)是否如平托所言,中國軍隊曾對Liampo(寧波)的葡萄牙人進行過一場大屠殺,屠殺人員數字是否可信。本文擬依據中文資料,其最重要依據是作為主要當事人之一,1548年下令明軍進攻Liampo(寧波府之雙嶼)港的朱紈所著之《甓餘雜集》中有關雙嶼港及佛郎機的記載,來對平托Liampo(寧波)紀事進行勘比考證,以求事實之真相。朱紈《甓餘雜集》中的有關資料前人雖亦有人徵引,但始終沒有一位學者對這部著作中關於雙嶼港及佛郎機極為豐富的資料進行系統清理,致使許多寶貴資料長期湮沒。當然更沒有學者將《甓餘雜集》中的雙嶼港及佛郎機資料與平托《遊記》中的Liampo紀事進行對比研究。本文希望通過這一最基礎的史源探索,力圖解決百餘年來的懸疑,即平托《遊記》中Liampo (寧波)紀事是否可信,進而證明朱紈《甓餘雜集》這部書在早期中葡關係史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以期引起東西方治澳門史及中葡關係史學者的重視。
二
平托《遊記》原文為葡文版,17世紀就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後又出版多種英文版本,20世紀70年代還出版過日文版,但迄今未見中文譯本。由於該作品篇幅太大,各家使用原葡文俱是選譯,關於Liampo(寧波)紀事亦是各自選擇一部份,下面主要以洛羅瑞、方豪、張天澤三種不同的選本中譯簡述平托《遊記》中的Liampo(寧波)紀事。
先看洛羅瑞編選《遊記》中的記載:
這樣航行了六天到達寧波的門户,即離當時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3里的兩個島嶼,那是他們在陸上建立的居民點,有兩千多所房屋,由市議員、王家法官和要塞長官治理,還有六七個司法聽差和其他官員,法庭書記官在公正書後面寫上:“我,某某人,本寧波市司法文書公證人,為我主國王效勞。”好像此地位於聖塔倫和里斯本之間一樣。此口氣充滿自信,而且得意洋洋,因為有些房屋價值達三四千克魯札多。後來,大大小小的房屋由於我們的過錯全部被中國人摧毀,沒有留下任何值得一看的東西。(……)
當地人與沿海航行的人們稱做寧波門户的兩個島中間有一條航道,寬度在火槍射程的兩倍以上,深二十至二十五英尋,一些地方有小海灣作良好的拋錨地。(……)安東尼奧·德·法里亞是在一個星期三的上午到達的。(……)隨著主教堂--聖母受孕教堂的鐘聲響起,此地另外還有六七座教堂,人們集合在一起討論那兩人(指梅姆·塔博爾達和安東尼奧·恩里克)帶來的消息。(……)
安東尼奧·德·法里亞進入港口,那裡的二十六艘大黑船和八十艘容克木船以及數目更多的班康船早已按順序排成兩行。(……)安東尼奧·德·法里亞上了這條蘭特伊亞船,在小號、笛號、定音鼓、高音笛、大鼓和在該港口的中國、馬來亞、昌巴、暹羅、婆羅洲、琉球等國人的其他樂器濱奏的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到達碼頭,這些人是懼怕海上眾多的海盜而依附葡萄牙人的。(……)他們從這裡抬著他沿一條很長的街道朝教堂走去。安東尼奧·德·法里亞要離開這裡的時候,(……)有許多人跟隨著,既有葡萄牙人,也有當地人,還有許多其他國家人,他們是為做生意聚集到這裡來的,因為這裡是當時人們知道的各地最優良、最富有的港口。(……)彌撒結束以後,寧波居民點(或者像我們的人所稱呼的寧波市)政府的四位主要人物來到安東尼奧·德·法里亞身旁,他們是馬特烏期·德·布里托、蘭薩羅特·佩雷拉、熱羅尼莫·多·雷戈和特里斯藤·德·加。這四個人把他圍住,在所有一千多葡萄牙人簇擁下來到他們住處前面的一個場院(……)(5)
再看方豪的選譯本:
吾人抵達Liampo諸港,港由對峙二小島構成,距彼時葡人貿易之地約三里Lieu。若輩曾於其地築館舍千餘,由市長、承審員、議員、司法官與其他七八種顧問或裁判員,負責治理。書記官每當宣判終了時,心向在下群眾宣稱:“余某某,Liampo法院文牘兼書記奉吾皇陛下云云(……)。”所有屋宇,共耗三四千杜加脱ducats金幣,始告完成。乃因吾人所犯罪惡,大小建築,盡為中國人付諸一炬。(……)當地居民及沿海船户咸呼兩島之間為Liampo之門户,其地有一運河,其寬度較arqubuse兩倍射程之距離尤大,深至四十公尺半。有海岸數處,最宜泊舟。又有風景優美三小溪,溪水味甘,源出高山,凡溪流所經之地,松柏、橡樹等小叢林,皆甚邃密。前安多尼·特·法利亞停留之地,蓋即在二島之間地。(……)
中國政府Chaem某,為本地巡撫,令海道出軍,發帆船三百艘小艇八十艘,舟中共六萬人,皆在十七日內集合者。海道與我國艦隊司令相若。上述大隊船艦乃專來襲擊此不幸之葡萄牙殖民地者。事變之經過,非葡人意料所及,而余亦不能認余之記述必有遺漏,此實出於學力不足,縱有敏銳之頭腦亦不克充份想像當時之情景。兹就余目睹者略述於下。此次上蒼所予可怖之懲戒,幾亙五小時之久。凶猛之敵人使Liampo境內一無遺存。凡為彼等所見者,一律破壞焚毀。此外復有基督徒一萬二千人被害,內葡萄牙籍者八百,俱在三十五艘小艇及四十二艘巨艦中焚斃者。金錠、胡椒、檀香、丁香、肉豆蔻莢與肉荳蔻子,及其他貨物,損失二百萬金。凡此種種災禍,皆由一貪鄙惡劣的葡萄牙人肆意妄為所致。(……)時1542年瑪爾定·亞風素·特·蘇薩任印度總督,呂·凡斯·貝勒拉·馬拉馬克任馬剌甲軍佐。(6)
張天澤的選譯本是:
寧波(Liampo)港由兩個對峙的島嶼所組成,相隔約兩里路。到1540年或1541年,葡萄牙人已在其地建造了一千多所房屋。其中有些房屋價值在三四千達卡以上。這是一個大約有三千人的殖民地,其中有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其餘是各國的基督教徒。葡萄牙人的貿易總額達三百萬葡元以上。絕大多數貿易是以來自日本的銀錠進行交換的,寧波的葡萄牙人在兩年前就與日本建立重要的通商關係了。
這個殖民地有它自己的政府,包括一名稽核,幾名高級市政長官(Vreadores),一名主管死者與孤兒的官員,幾名警官,一名市政廳書記員,若干名術隊督察官、賃借官,以及一個共和國的所應設置的其他各級官員,有四名公證人,他們的職責是起草契約、合同等;此外還有六名負責注冊事務的官員。在這些職位上工作的人,每人可得薪金三千達卡,不過,還有些職位的薪俸更高。有兩所醫院和一座慈善堂,每年要花用三萬達卡以上。僅市政廳的租金每年就要六千達卡。因此人們常説,這個殖民地是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所有殖民地的中最富、人口也最多的殖民地。其範圍之大,在整個亞洲無與倫比。所以,當書記員或秘書草擬公文時,他們總是寫下這樣的話:“吾王陛下的輝煌偉大、忠誠不渝的寧波鎮。”
這個繁榮的殖民地之所以注定要遭到毀滅,其主要原因在於某人的胡作非為。蘭沙羅特·佩雷伊拉是利馬港人,乃名門望族的體面人物。據說,他以幾千達卡借給幾個不可信賴的中國人。那些人自食其言,賴賬不過。他們失蹤了,蘭沙羅特·佩雷伊拉從此再也沒有聽取他們的任何消息。為了補償自己的損失,他糾集了十五名至二十名最惡劣的葡萄牙亡命之徒,在夜幕中襲擊一個距寧波兩里路的村莊。他們刧掠了十家或十二家農户,佔有妻子女兒,並且毫無道理地殺害了十三個人。這一暴行在附近鄉村里引起了百姓們的極大恐懼,大家都向某個高級官員鳴冤。這個官員將此案上報巡撫,請求為民除害,採取強硬手段來對付葡萄牙人,這些人的可惡行為已在其他地方激起極大憤慨。巡撫不遲疑地命令海道採取行動。海道指揮著一支由三百艘帆船、八十條舢板和六萬餘名水手組成的艦隊。十七天後,一切準備就緒,艦隊便猛襲這個難逃劫數的葡萄牙殖民地。按照敘述者門德斯·平托本人的說法,毀滅的情況非常恐怖,以至於他無法形容。儘管懲罰行動持續不到五個小時,寧波已蕩然無存,祇有空名了。這些殘酷的敵人焚燬了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東西,將一萬二千名基督教徒處死,其中八百名為葡萄牙人,他們是在三十五艘大船和四十二艘帆船中被活活燒死的。被毀財產總值估計達二百五十萬金葡元,其中半數是銀錠、胡椒、檀香木、丁香、肉荳蔻乾皮和胡桃,另外半數是其他各類的商品。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1542年。(7)
三人所引資料基本內容相同,但詳略及引述事實明顯有很大的差異,這可能是來自不同版本的緣故。三人均為卓有成就的澳門史研究專家,應該説,綜合他們三人引述平托《遊記》中有關Liampo 寧波紀事資料,基本上可以看到平托所記寧波之事的主要內容。
三
平托《遊記》之寧波紀事雖然遭受眾多人的攻擊,但多無實際內容。獨張天澤提出,平托之Liampo(寧波)紀事“沒有在任何中文記載或編年史內,以及任何嚴肅的葡文資料中”提及。這句話是要害,如果平托Liampo(寧波)之事確實在任何中文文獻和葡文文獻中都找不到記載的話,也就是説如果葡萄牙人在Liampo(寧波)的通商活動僅見於平托之書而得不到任何中葡資料佐證的話,那我們就祇能將第二節所述內容視作為平托臆造的一個冒險故事或者是不足置信的謊言。
看來事實并非如此。關於中文資料中的葡人在寧波之通商活動留待下節再談,我們先看看一些葡文資料的記載。
首先是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於1570年出版的《中國概説》記載了葡萄牙人在Liampo寧波)的活動,克魯斯是1556年到中國的。
這些在中國境外又隨同葡萄牙人航行的中國人在費爾南·德·安德拉闖了禍之後,就開始將葡人引去Liampo(寧波)做生意,因為那邊沒有圍起來的城鎮,而祇有沿海的許許多多大村落,人們很窮,他們對葡萄牙人之來很高興。……經過這樣的串通,葡人就開始在寧波諸島越冬了。他們在那裡安居樂業,唯一祇缺絞架和恥辱柱了。那些同葡人混在一起的中國人,也有些葡人,就開始放肆起來,大搶大偷,還傷殘人命,壞事幹得越來越多,受害者叫苦不迭,他們的聲音不光傳到了〔浙江〕省的大老爺耳中,而且也傳到皇帝那裡。皇帝馬上下令在福建省調集大批水師,將所有盜匪趕出沿海,尤其是寧波一帶。同時,所有商人包括葡人和中國人,都被列為盜匪。(8)
在另處,克魯斯還寫道:
另一個省是浙江,這個省有十四座城,包括寧波城,葡人也曾在那裡貿易,但現所有的活動已移至廣州。(9)
平托之書是他死後於1614年才出版,克魯斯完成《中國概説》時不可能見到平托之書。而他關於葡萄牙人在寧波活動的記錄,除了比不上平托的詳細外,其基本情況是一致的。所以,張天澤所稱在“嚴肅的葡文資料都未見過片言隻語或者甚至隱隱約約提到1542年前在寧波有任何外國殖民地”是不符合事實的。毫無疑問,克魯斯1570年出版的《中國概説》是一種極為嚴肅的早期葡文資料,他所記錄的葡人在寧波活動之消息來源於他在廣州見到的一個在閩浙經商被中國政府拘囚的葡萄牙商人,因此,其記錄應可信。
除克魯斯外,成書於1612年狄奧哥·杜·寇圖的《Decada Quinta da Asia》亦載:
1546年7月,馬六甲司令Diogo Doares派許多船到中國作貿易,葡萄牙人已開始在浙江寧波外海居留。(10)
曼里克教士於1649年成書的《東印度傳教路線》也有葡人在寧波的活動:
葡萄牙人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居民點是寧波市,此地在澳門以北200里格,其交往與貿易的規模之大,可以與印度的主要城市相比。但是,一場混亂使該城於1542年被毀。
寇圖所記可以肯定未參考平托之書。曼里克教士是1604年即派往東方,在果阿奧古斯西教團修道院任職,1628年往孟加拉王國,隨後在亞洲各地包括日本、菲律賓、越南、澳門等地活動,1643年才回到歐洲到達羅馬,1649年即出版了他的著作。(11)因此,我們認為曼里克教士很可能也沒有見過1614年出版的平托之書。
到20世紀初,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亦載:
在1528年,寧波市內已標志著“歡迎葡萄牙人來訪”蕃坊,而這個遺址直到上個世紀還可以在寧波內找到。(12)
上述著作均應是嚴肅的葡文著作,雖然記載葡人在Liampo(寧波)活動的事跡并不詳細,但葡人曾在Liampo(寧波)建立過一個貿易據點應該是很難否認的事實。亦證張天澤對平托《遊記》評判的失誤。
四
中文資料中是否有葡人在寧波(Liampo)活動的記載呢? 葡文資料中所反映的Liampo之事實,中文文獻中對應的應是“雙嶼”。這一點,方豪先生巳作了極令人信服的考證。雙嶼港位於寧波府霩 所對面的海上,離舟山城東南一百里,“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13)霩
所對面的海上,離舟山城東南一百里,“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13)霩 所雖是明廷駐軍之地,但與海相隔的雙嶼港還有相當距離,是衛所官兵難以控制的地方。港口地形險要,“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闊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14),是一個海上走私貿易的理想港灣。雙嶼屬寧波府,雙嶼又是由“東西兩山對峙”組成,可見,平托所言這“Liampo”之門戶,由兩個島嶼組成的港口即是雙嶼(15)。平托所記雙嶼港中有一航道,水深二十至二十五英尋,《指南正法》:“雙嶼港內流水甚急,洋內打水無底。”(16)平托記雙嶼港附近有“海岸數處,最宜泊舟”,《甓余雜集》卷四稱,雙嶼有“南港”、“北港”。(17)平托又稱港內泊有“二十六艘大黑船、八十艘空克木船及數目更多的班康船”,可見,平托所言此港甚大;而《甓餘雜集》稱雙嶼港“中間空闊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18)。平托所記雙嶼島上有山,并稱“小溪裡清涼的溪水從山頂流下”,前引《甓餘雜集》:“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19)可見,從地理形勢上看,平托所記并非虛言,由“兩個對峙的島嶼組成的Liampo港”應就是雙嶼港。
所雖是明廷駐軍之地,但與海相隔的雙嶼港還有相當距離,是衛所官兵難以控制的地方。港口地形險要,“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闊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14),是一個海上走私貿易的理想港灣。雙嶼屬寧波府,雙嶼又是由“東西兩山對峙”組成,可見,平托所言這“Liampo”之門戶,由兩個島嶼組成的港口即是雙嶼(15)。平托所記雙嶼港中有一航道,水深二十至二十五英尋,《指南正法》:“雙嶼港內流水甚急,洋內打水無底。”(16)平托記雙嶼港附近有“海岸數處,最宜泊舟”,《甓余雜集》卷四稱,雙嶼有“南港”、“北港”。(17)平托又稱港內泊有“二十六艘大黑船、八十艘空克木船及數目更多的班康船”,可見,平托所言此港甚大;而《甓餘雜集》稱雙嶼港“中間空闊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18)。平托所記雙嶼島上有山,并稱“小溪裡清涼的溪水從山頂流下”,前引《甓餘雜集》:“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19)可見,從地理形勢上看,平托所記并非虛言,由“兩個對峙的島嶼組成的Liampo港”應就是雙嶼港。
再看看雙嶼港是否有葡萄牙商人從事貿易。《明史·朱紈傳》載:
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人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20)
《日本一鑑》卷六(海市>:
嘉靖庚子繼之,許一(……)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21)
《甓餘雜集》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
柯喬等稟稱,佛郎機夷船先冼沖泊擔嶼,皆浙海雙嶼驅逐南下。(22)上述三條材料的明確表示佛郎機(葡萄牙)夷人確實在雙嶼港從事貿易。又鄧鍾《籌海重編》卷十:
日本原無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舶廣東之私澳,官税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自甲申歲(嘉靖三年,1524年)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取貨以隨貨,倩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勿得。西洋船原回私澳,東洋船遍佈海洋,而向之蕃舶悉變為寇舶矣。(23)
這裡“西洋原貢諸夷”及“西洋船”應含佛郎機,鄧鍾亦稱葡人在雙嶼貿易。《正氣堂集》卷七亦載:
廣東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羅、佛郎機諸番不遠。數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處番徒,勾引西南諸番前至浙江雙嶼港等處賣買,逃免廣東市舶之税。(24)
很清楚,各種史料均可證明,佛郎機夷人確實曾在雙嶼港即平托所言之Liampo之門戶的兩個島嶼之間進行貿易活動。
葡萄牙人何時開始去雙嶼港貿易,各種史料歧異甚大。平托書中亦未談及葡人最早去Liampo的時間,祇告訴我們,在1540或1541年,Liampo已成為葡人之一個頗具規模的貿易據點。據利類思《不得已辨》:
明弘治年間(1488-1505),西客遊廣東廣州、浙江寧波,往來貿易。(25)
利類思書成於康熙四年(1665),追記葡人來華之事明顯不確。葡人來華始於正德九年(1514),正德九年之前無葡人來華之事。很可能,利類思不明明朝皇帝年號順次,將正德誤為弘治。利類思為意大利人,1637年即到中國。他稱葡人曾在寧波貿易應未受平托書影響。克魯斯《中國概説》稱:
這些在中國境外又隨同葡萄牙人航行的中國人在費爾南·德·安德拉闖了禍之後,就開始將葡人引去Liampo做生意。(26)
案:此處克魯斯有誤,在中國闖禍的不是安德拉(Fernão de Andrade),而是其弟西蒙(Simão de Andrade)。西蒙闖禍是在1518-1519年間(27),“之後”則應是1519年之後,那就是説,克魯斯認為葡人去Liampo是在正德末嘉靖初。倘利類思之“弘治”為正德之誤的話,兩者記載距離不大。但前引寇圖之書則稱“1546年7月,(……)葡萄牙人已開始在浙江寧波外海居留”(28),與前二者差距甚大。
值得注意的是鄧鍾《籌海重編》的記載:“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泊廣東之私澳(……)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西洋船原回私澳。”(29)“西洋原貢諸夷”,16世紀後很明顯主要應指葡萄牙人。甲申歲為嘉靖三年(1524),“甲申歲凶,雙嶼貨壅,”則說明在1524年之前,葡萄牙人已開始在雙嶼貿易。這裡所記與克魯斯合。《日本一鑑》記載有很大的不同,認為嘉靖十九年葡人到雙嶼:“嘉靖庚子(十九年,1540)繼之,許一、許二、許三、許四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市雙嶼、大茅等港。”(30)主張嘉靖十九年還有胡宗憲《籌海圖編》、謝傑《虔臺倭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等。(31)《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八則主嘉靖二十二年(32),均比鄧鍾之嘉靖初要遲十幾年。《日本一鑑》還有一條材料亦應注意:
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鄧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獄,嘉靖丙戌(五年,1526),越獄逋下海,誘引番夷私市浙海雙嶼港。(33)
這裡雖然僅言“番夷”,而沒有指明是“佛郎機”,但這個“番夷”同鄧鍾所言“西洋諸夷”及俞大猷前言“西南諸蕃”一樣,其中應包含佛郎機。為甚麼《日本一鑑》稱嘉靖五年是引“番夷”私市雙嶼,而稱嘉靖十九年則是勾引“佛郎機國夷人”私市雙嶼呢? 我們的理解是,嘉靖五年時,祇是少數的佛郎機人同其他東南亞各國商人一起去雙嶼,故稱“番夷”,因為佛郎機人并不是最主要的,到嘉靖十九年時,則是大批的佛郎機人去雙嶼,故稱“佛郎機國夷人。”嘉靖五年亦還可視為嘉靖初,如不過於拘泥,《日本一鑑》所載與克魯斯亦大致相合。朱紈《甓餘雜集》卷二有一條材料:
前項賊船,蟠踞雙嶼港二十餘年(1528),招引各國番夷。(34)
“二十餘年”之前,亦應該是嘉靖初年。同書同卷還有記載:
海中地名大麥坑與雙嶼港兩山對峙,番賊盤踞二十餘年。(35)
“番賊”、“各國番夷”,其中應含佛郎機。可見,葡人在嘉靖初年確已開始來浙江雙嶼港貿易,但初來時人數較少,到嘉靖十九年後。因為日葡貿易的開展,大批葡萄牙人來到雙嶼。這同澳門開埠初期的形勢完全相同,據平托書載,1540或1541年時,雙嶼港已發展成三千人口、一千餘所房屋的港口城市。嘉靖十九年即1540年,試想,如果沒有十幾年時間的發展,作為寧波外海的一個荒島不可能發展到如此規模。因此。將葡萄牙人進入Liampo及雙嶼港的開港時間定在嘉靖初年是合理的。
五
我們再看看平托《遊記》中關於Liampo港規模的記載:
這是一個大約有三千人的殖民地,其中有葡萄牙人1,200名,其餘是各國基督教徒。這裡有葡萄牙人,也有當地人,還有許多其他國家人,他們是為做生意聚集到這裡來的,因為這裡是當時人們知道的各地最優良、最富有的港口。
安東尼奧·德·法里亞進入港口,那裡的二十六艘大黑船和八十艘容克木船以及數目更多的班康船早已按序排成兩行。(……)〔在〕該港口的中國、馬來亞、昌巴、暹羅、婆羅洲、琉球等國人的樂器演奏的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到達碼頭,這些人是懼怕海上眾多的海盜而依附葡萄牙人的。
在平托的筆下,Liampo港是一千人口,可以容納數百條船及擁有葡萄牙、中國、馬來亞、昌巴、暹羅、婆羅洲、琉球等多國商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口。這些記載是否可信,我們須在中文資料中尋找證明。
首先看看雙嶼的人口,《弇州史料》卷三<湖廣按察副使沈密傳>:
舶客許棟、王直等,於雙嶼港,擁萬眾,地方紳士,利其互市,陰與之通。(36)
稱雙嶼諸港有“萬眾”,雙嶼為其中之一,那平托稱1540年或1541年時Liampo港有人口三千,應不為誇大,與中文文獻合。又《甓餘雜集》卷三載:
(嘉靖二十七年)佛郎機夷人大船八隻,哨船一十隻經攻七都沙頭澳,人身俱黑,(……)近報佛郎機夷船眾及千餘,兩次沖泊大擔外嶼。(37)
“佛郎機夷船眾及千餘”,這千餘佛郎機夷又是“皆浙海雙嶼驅逐南下”(38),可證平托所言1540或1541年時Liampo港有葡萄牙人1,200人并非誇大,更非謊言。為了更詳細予以證明,下面我將《甓餘雜集》所載佛郎機人(或被佛郎機人收買為奴)有名字者羅列統計如下:
法里須(哈眉須國)、沙哩馬喇(滿喇加國)、嘛哩丁牛(咖呋哩國)、共帥羅放司(佛郎機、佛德全比利司(佛郎機)、鼻昔弔(佛郎機)、安朵二放司(佛郎機)、不禮舍識(佛郎機)、畢哆囉(佛郎機)、哆彌(佛郎機)、來奴(佛郎機)、哈的哩(番婦)、來童、琉個哆連、滿渡喇、浪沙囉的畢咧(佛郎機)、佛南波二(佛郎機)、兀亮哵咧(佛郎機)、胡馬丁、蘇滿;
白番十六人(以下姓名無法點斷,暫斷如下):
鵝必牛義 、不力疾、文會遮尾、饒利弗蘭
、不力疾、文會遮尾、饒利弗蘭 、滿咖喇哆尼、叱哩、細格十叭、不咧咖、石板、雷使彌祿、沙哩哵、方叔擺、軟衰哩
、滿咖喇哆尼、叱哩、細格十叭、不咧咖、石板、雷使彌祿、沙哩哵、方叔擺、軟衰哩 、喏哩
、喏哩 弗蘭、讓弗蘭卜的、喇卜的;
弗蘭、讓弗蘭卜的、喇卜的;
黑番四十六名:
亦石哆、聞弗、聞世世哥、饒哩姐、安哆彌、密須、調滔哥、三婆羅、沙哩 、味味、哆呢盧、煨須柔阿、哈眉須喏哩
、味味、哆呢盧、煨須柔阿、哈眉須喏哩 、
、 阿尼、亦篤呀十八、滿喇灣若哩
阿尼、亦篤呀十八、滿喇灣若哩 、吶師、必相可、喏唵多尼、軟尼卜哩、世世可、呵哥叭、蘆密相、味味二、嘹哥、咈哩
、吶師、必相可、喏唵多尼、軟尼卜哩、世世可、呵哥叭、蘆密相、味味二、嘹哥、咈哩 、咈剌滅
、咈剌滅 、哵
、哵 哩、聞海、阿喇十、明咖喇、沙蘭、馬沙喇、馬卜喇、沙列
哩、聞海、阿喇十、明咖喇、沙蘭、馬沙喇、馬卜喇、沙列 、聞來的哩、木撒阿、冬革十叭、唵哆尼、哪斯、革哩;
、聞來的哩、木撒阿、冬革十叭、唵哆尼、哪斯、革哩;
夷賊十五名:
呵哩、唵陀呢寺、呵哩低寺、喝斯班、陀彌、吉林、喝那斑、哩勿、呵多泥、佛郎頭、婆勾周、哪文、唵密寺、沙改通、呂那;
番賊十三名:
乜寺、低哩三、馬低寺、祁聿寺、多年牟唵多尼、噫朵乜突、佛藍寺、秘多羅秘寺、馬郎寺釋甲、葛臘寺、佛哪個、密吻郎、唵哪寺。上述人名均是從雙嶼撤退南下在閩浙海面被明朝官兵擒獲的佛郎機人或佛郎機人的黑奴(39),數量竟達120餘人。有名者達120餘人,佚名者還有多少呢? 如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賊船計有六十餘人,內有黑色及白面大鼻番賊七八人,番婆二口。”“十月初三日,擒解佛郎機、暹羅諸番夷賊一十六人。”(40)這類資料在《甓餘雜集》中俯拾皆是。從這些詳實的漢文資料完全可以證明,平托所記在Liampo港有1,200名葡萄牙人(其中包括相當部分黑奴)是很真實的記錄。1540年或1541年,正是日葡貿易開通不久之時(41),為了展拓對日的海上貿易,大量的葡萄牙商人聚集浙海寧波,以雙嶼港為貿易據點,展開大規模的對日通商。寧波向來即是日本貢舶貿易之處,由寧波至日本的航路亦極繁盛。(42)據C. R. 博克塞教受公佈的資料,全漢昇教授統計,16世紀末17世紀初,澳門對日貿易每年輸入約100萬兩白銀(43),以此反推,1540年或1541年時,平托所言Liampo港葡商的貿易總額達“300萬葡元以上”,也不應是謊言或“吹牛”,以雙嶼港葡商貿易的繁盛,平托之言應該可信。
再看看雙嶼港商人的國籍。《甓餘雜集》卷二:
雙嶼港係通番賊穴,向來無倭人過上國,至今船船俱帶各本國之人前來販番,尚有數百倭人在後來船內未到。(44)
同書卷三又載:
此皆內地叛賊,常年於南風迅發時月,糾引日本諸島、佛郎機、彭亨、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港內停泊。(45)
《正氣堂集》卷七亦載:
數年這〔之〕前,有徽州、浙江等處番徒,勾引西南諸蕃,前到浙江之雙嶼港等處賣買。(46)
雙嶼港除了華人與葡人外,暹羅人與日本人應是一大宗,從前引《甓餘雜集》內容反映的其他國家商人還有彭亨、馬六甲、哈眉須、咖呋哩等。可證平托稱Liampo港是一個多國商人通商貿易的國際港口也是可信的。
六
平托所記Liampo港城市的建築,稱有一千餘所房屋(洛羅瑞選本為兩千所房),島上有一條長的街道,六七座教堂,還有醫院、慈善堂等。前面既已證明雙嶼諸港是一座“擁有3,000”的城市,那麼具有3,000人人口的城市建有一千至兩千所房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
近數年來,(夷人)始入濠鏡澳,築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47)
這裡雖説的是澳門,澳門開埠十年左右,就已建起“千區”以上的房屋,其人口,葡文文獻稱1563年5,000人。雙嶼從開港到1540年時已近二十年,所以説建有一千餘所房屋應是可信的。中文文獻的材料也可見一些蛛絲螞跡。《虔臺倭纂》卷下:
鏜入(雙嶼)港,毀賊所建天妃宮及連房、巨艦,向為群丑巢穴者,盡平焉。(48)
“連房”,當指島上所建的房屋區。《甓餘雜集》卷二載:
典史張口帶兵入港巡邏,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餘間、寮屋二十餘間、遺棄船隻二十七隻,俱各焚燒盡絕,止留閣塢未完大船。(49)
我認為,此處所言之“天妃宮”當即應指宗教拜祭之場所,島上雖有華人海商,但不可能建十餘間天妃宮,其中大約有幾座天妃宮,其餘六七座應該是教堂。早期的教堂均是草棚搭蓋的建築結構,明軍也不知道教堂是甚麼,祇知是人們拜祭的地方,故泛稱“天妃宮”。這裡雖祇提“寮屋二十餘間”,應不是島上房屋建築的全部。再據《甓餘雜集》卷四載:
雙嶼港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達觀入港,登山凡踰三嶺,直見東洋中有寬平古路,四十餘日,寸草不生,賊徒佔之久,入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50)
這條“寬平古路”亦與平托所寫島上一條“很長的街道”相合。可見,平托關於島上之建設各項,亦大致可信。
關於Liampo港的行政建置,平托稱:
這個殖民地有它自己的政府,包括一名稽核,幾名高級市政長官,一名主管死者與孤兒的管員,幾名警官,一名市政廳書記員,若干名衛隊督察官、賃借官,以及一個共和國所應設置的其他各級官員。有四名公證人,他們的職責是起草契約合同等,此外還有六名負責注冊事務的官員。
平托所言,可獲克魯斯的證明:
葡人就開始在Liampo諸島越冬了,他們在那裡安居樂業,唯一祇缺絞架和恥辱柱了。(51)
也就是說Liampo港除開絞刑架和恥辱柱外,一切市政府機構全部建置完備。克魯斯之言可以證平托所言不虛。即以後來澳門開埠之初的建置亦可佐證。成書於1582年的佚名作者《市堡書》來源於葡萄牙官方對澳門的敘述資料:
這個居留地從未有過常駐在此的都督,祇有赴日船隊的隊長。(……)另外該地還有一位聽審官(Ouvidor),一位公文、司法與記錄書官,他也兼任為死者與孤兒開證明的文書官。(52)
可見,澳門開埠初期的市政機構比平托所記Liampo 港之市政機構還要簡單,但可反證,平托所記Liampo港之資料并非如洛瑞羅所言“大概是來自澳門資料”。
中文文獻有資料亦可資佐證。《甓餘雜集》卷六載:
積年為盜歇案,謀叛中國,伙合外夷,各有封號:喇噠、伙長、謀主、總管、千户、直庫、繚公、押綱等項各色。(53)
同書卷五載:
訪得長嶼等處慣通番國林恭(……)等,各號喇噠、總管、柁工、水梢等項名色。(……)見獲浪沙羅的嗶咧等,審稱矮王、小王、二王名色。(54)
同書卷二載:
生擒喇噠許六、賊封直庫一名陳四、千户一名楊文輝、香公一名李陸,押綱一名蘇鵬,賊伙四名(……)(55)
《筆山文集》卷一:
附海番徒,皆係赤立之民;裸身刺舟而已。有等號為坐山哪噠,身雖不行,專一主謀,賊出則給資本、糗糧、火藥、器械、船隻。或通有番貨,劫有財物,則駕船載酒米,潛通窩藏,坐地分臟。(56)
上述管理系統職名在文獻中一般用於華人海商集團,如“擒獲喇噠胡霖”(57),“岸上寫蘇哪噠告示”(58)“若長嶼喇噠林恭等往來接濟”。(59)據上引文獻之內容可知,“喇噠、伙長、謀主、總管、千戶、直庫、繚公、押綱等項名色”均是雙嶼港華人海商集團管理系統的職名。
奇怪的是,華人海商集團這一套海上管理系統亦見於暹羅,使人聯想,暹羅人使用這一套職名是否與雙嶼港這一國際港口有關? 前已言之,暹羅人亦是雙嶼港貿易的主要外商之一。(60)田生金《按粵疏稿》卷五<報暹羅國進貢疏>:
船主握良西蘇喇進烏木五百斤,大總管握中權進……,二總管握西末、握忠九二名共進……,大伙長蘇慕堂進……,二伙長伍千塘進……,大哪打握申皮雪進……,二哪打握良酸、握悶王撥叭二名共進……,財副握良陳、握唐束二名共進……,干事西臘進……,機察乃棍、乃吼二名共進……,執庫隘西、喇隘、長燕、唐蠟九四名共進……,押工喇必、耶乃、別鎮、唐中權、唐束、隘孫六名共進……,千副干唐、真堂、隘昆、隘添、隘論、隘唐六共進……,舵工厚樂,遂明、惟信、敬濱四名共進蘇木四百斤。(61)
這些在《暹羅館譯語》之<人物門>中亦可見。但我們從這些讀音仍可看出,暹羅這一套職官名仍來自中國之海盜兼海商集團。如“押江(即押綱)”,《譯語》讀作“押崗”;“千富(即千戶)”,《譯語》讀作“千賀”;“財富”,《譯語》讀作“搠忽”;“干事”,《譯語》讀作“敢細”;“機察”,《譯語》仍讀作“機察”;“總管”,《譯語》讀作“宗合娃”。(62)上述讀音可以看出來源於粵語,大致可推斷,廣東籍海商將這一套海上管理系統之職名帶進暹羅,暹羅國後亦襲用。上疏中的“握”姓,為暹羅任官者之通姓,暹語為“大”的意思。(63)可見,任上述職者均為暹羅國人,且是暹羅國內之官員。又據張燮《東西洋考》卷九載:
海舶舶主為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合併徏巢。亞此則財富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為直庫;上檣桅者為阿班,司椗者有頭椗、二椗;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為舵工,亦二更替;其司針者名火長。(64)
很明顯,這是一套完整的海上舶船航行管理系統。當舶船泊岸登陸後,這一套系統仍然是對港口管理行之有效的行政組織。雙嶼港的海商集團應是使用這一套行政組織對雙嶼港進行管理。
費解的是“喇噠”一詞,喇噠一詞在明代嘉靖至萬曆間史書中屢見不鮮,一般均用於海盜首領之號,如“喇噠胡霖”“喇噠柯岳”“喇噠林恭”“賊首自稱天王大刺噠周月波”(65),但還有“大哪打握坤皮雪進”“二哪打握良酸、握悶王撥叭”(66)。可見,“喇噠”一詞不僅用於華人,亦用於暹羅人,不僅用於海盜首領,亦用於暹羅國官員,且被他們自己認可。日本前輩學者藤田豐八提出:“(喇噠)係外國與本國商人之中間者,為後世Compardor(買辦)之濫觴。是故由此名號所興之時代推之,或為Compardor之力亦未可知。Compardor為葡語,固無論矣”。(67)藤田氏稱“喇噠”是外國與本國商人之中間者應有一定道理。《甓餘雜集》卷六稱:
縱容土俗,哪噠通番,屢受報水分銀不啻幾百;交通佛郎機夷賊入境,聽賄買路砂金遂已及千。(68)
前引“長峙等處慣通番國林恭……鄭總管即板尾三等各號為喇噠總管、柁工、水梢等項名色。”可見,“喇噠”一詞確稱“外國與本國商人之中間者”之意。然萬曆間廣東市政使蔡汝賢《東夷圖説·佛郎機》載:
(佛朗機)又與滿剌加互市爭哄,恨其困執哪噠,歸訴治兵,突至滿剌加,大被殺,整以滿載而歸。(69)
黃衷《海語》卷上<滿剌加>亦載:
正德間,佛郎機之舶互市爭利而哄,夷王執其哪噠而囚之,佛郎機人歸訴於其主。(70)
據張禮千之《馬六甲史》,當時拘捕的是“搜集貨物、未執軍械之葡萄牙人亞勞佐(Ruy de Araujo)等二十餘名。”(71)
《東西洋考》卷三<大泥>:
初,漳人張某為哪督,哪督者,大酋之號也。(72)以此觀之,喇噠一詞原始語源當為馬來語,意為酋長、首領。而馬來人將葡萄牙船隊的商人首領亦稱作“喇噠”。然查《澳門記略》之<澳譯>,內有“喇噠令”一詞,意為“賊”。(73)今葡文ladrão亦是賊的意思,raptar則是偷盜、劫掠的意思。此語在東南亞國及東南沿海華人傳之既久,遂普遍接受,變為他們的一種尊稱。查《暹羅館譯語》,“喇噠”一詞譯音“剌達”,可見是外來詞,非暹語,被暹羅官方襲用。
華人海商集團海上管理系統的最高首領稱“喇噠”,恐怕是倣葡人之制。葡萄牙人商隊在遠東貿易的臨時據點往往都是由大商人組成駐地管理機構對當地進行市政管理。平托書中所言受Liampo葡萄牙人盛大歡迎的安東尼奧·德·法里亞即是當時的貿易船隊之大商人,由四位葡萄牙人組成的Liampo 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亦是大商人。(74)可以發現,華人海商集團海上管理系統在雙嶼港與葡人之市政管理亦有相近的地方,且多受葡人影響。
應說明的是,平托所言,這一套行政管理體系完全屬於葡萄牙人,還説Liampo市政府四位主要人物是葡人:馬特烏斯·德·布里托、蘭薩羅特·佩雷拉、熱羅尼莫·多·雷戈和特里斯藤·德·加。我認為,這應是反映1540或1541年以後的情況。因為,雙嶼開埠之初,葡萄牙商人在雙嶼港并不佔主導地位,佔主導地位的應是中國之海寇。前引《日本一鑑》稱,福建鄧獠於嘉靖五年(1526)即引番夷在雙嶼港貿易并稱“投託合澳之人盧黃四等”(75),很明顯,開埠之初,雙嶼港的管治權應控制在中國海盜手中。即是在1540年,許氏兄弟海盜集團入居雙嶼港,仍控制著雙嶼港的管治權。《名山藏·王享記》:
(王直)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為帥,引倭結巢霩 之雙嶼港。(76)
之雙嶼港。(76)
《虔臺倭纂》卷下:
雙嶼港,(……)賊李光頭、許棟所屯也,由庚子至戊申盤躆者九年,營房戰艦,無所不具。(77)
《海寇議》一書稱:
徽州許二住雙嶼港,此海上宿寇最稱強者。(78)
《甓餘雜集》卷二:
張四維擒獲雙嶼港賊首李光頭船內接濟酒米賊徒。(79)
思得雙嶼港,係日本等國通番巢穴,欲投未獲徽州賊許二等做地主。(80)
這些材料很清楚的説明,在雙嶼港還有另一個中心,即中國海盜集團中心,其首領即是許二(棟)與李光頭。許二集團是嘉靖十九年進入雙嶼港,葡萄牙人大批進人雙嶼港亦是嘉靖十九年以後,所以説“由庚子至戊申盤躆者有九年”(81),是指許氏兄弟及李光頭海盜集團佔據雙嶼的時間,而“庚子至戊申”是1540-1548年,正是葡萄牙商人大批進入雙嶼港及大規模拓展雙嶼港貿易的全部時間。因此,雙嶼港從1540-1548年時始終存在著兩個中心,一個是許氏兄弟海盜集團,一個是葡萄牙的商人集團,這兩者又相互利用,互為表裡,在一定程上結成一體。然而,對華人來説,他們所熟悉的就是中國海盜集團,而對葡萄牙人來説,他們所知道的也就是葡萄牙商人集團。這就是中國文獻及平托之書中各自報導雙嶼港的兩個側面。
七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平托關於中國軍隊進攻Liampo港屠殺外國商人的記載。先看引起這場屠殺的原因。平托稱,是因為葡商佩雷拉(Liampo港政府的主要人物之一)借錢給華人,而華人賴賬不還。於是,佩雷拉帶了幾十名葡萄牙人劫掠Liampo 附近的村莊,霸佔農戶妻女,并殺害13名無辜的平民,這暴行引起了中國官方的報復。平托所言,也能從中文資料找到證明。《甓餘雜集》卷二:
佛郎機十人與伊一十三人,(……)將胡椒、銀子換采布、紬緞,買賣往來日本、漳州、寧波之間,(……)在雙嶼,被不知名客人撐小南船載面〔麪〕一石送入番船,說有綿布、綿紬、湖絲,騙去銀三百兩,坐等不來。又寧波人林老魁先與番人將銀二百兩買緞子、綿布、綿紬,將男留在番船,騙去銀一十八兩。又有不知名寧波寧人哄稱有湖絲十擔,欲賣與番人,騙去銀七百兩;六擔欲賣與日本人,騙去銀三百兩。(82)
同書卷五載:
先得夷船扦掛紙貼,內開各貨未完,不得開洋;如各商不來完賬,欲去浯嶼等語。所謂完賬者,即倭夷稽天哄騙資本之説。(83)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亦載: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辄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斯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輾不肯償。(……)番人迫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84)
與平托書所記基本一致。雖然平托所言,將明朝軍隊進攻雙嶼僅歸結到葡人佩雷拉的一次偶爾發生的暴行并不全面,但這一事件是引發雙嶼屠港的導火線應是無疑的。
明軍進攻雙嶼,據平托書是一支由六萬人、三百艘帆船及八十條舢板組成的艦隊,下達命令是一名巡撫,指揮者為海道副使。關於進攻兵船之數,平托書似有誇大,據《甓餘雜集》卷二記載,海道副使柯喬“選取福清慣戰兵夫一千餘名船三十隻”,又“選取松陽等縣慣戰鄉兵一千名”(85)歸都指揮盧鏜調用。實際上進攻雙嶼港的明朝軍隊祇有二千餘人,兵船三十艘。巡撫是朱紈,朱紈當時的職務是“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及福建地方”(86),海道副使是柯喬。除士兵及兵船數有誇大之外,其餘基本相合。
關於雙嶼之戰屠殺之數目,平托書稱,殺死12,000名基督教徒,其中800名為葡萄牙人,焚燬大船35艘、帆船42艘。據《名山藏》及《天下郡國利病書》載,這次戰役“俘斬溺死者數百”。(87)據《甓餘雜集》卷二之詳細記載:
四月初二,攻殺番賊,落水不計其數,斬獲首級二顆,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賊犯林爛四等五十三名,奪獲本船一隻。(四月初六)將雙嶼賊建天妃宮十餘間、寮屋二十餘間、遺棄大小船二十七隻,俱各焚燒盡絕。(……)打破大賊船二隻,沉水賊徒死者不計其數。隨有賊徒草撇船一隻、叭喇唬船二隻前來迎敵,賊船被箭傷,落水爬水亦不計其數。(……)斬獲首級一顆,生擒黑番(共三名)、喇噠許六,賊封直庫一名陳四,千户一名楊文輝,香公一名李陸,押綱一名蘇鵬,賊伙四名。(88)
雖然有三處“不計其數”,但根據斬獲首級及生擒人數及上文公佈明軍公佈的傷亡人數三十六名來看,雙嶼之戰,不可能殺死海盜及外商達12,000人。我認為,平托所記殺死基督教徒12,000人(其中800葡人)之數當是1,200人的誤記,張天澤亦認為是1,200人之誤(89)。前面平托所言,Liampo人口總數是3000人,後面怎麼可能殺死Liampo港12,000人呢? 如果是1200人,則前後所載不矛盾。再看《甓餘雜集》卷三:
近報佛郎機夷船眾及千餘,兩次沖泊大擔外嶼。(90)
同書卷五又載:
佛郎機夷船先次沖泊擔嶼,皆浙海驅逐南下。(91)
“浙海驅逐南下”當即被明軍從雙嶼港趕出來的佛郎機人。一個三千人的Liampo港,被明軍殺死1,200人,還剩約二千人。這一“千餘佛郎機夷”,再加上“許棟……從雙嶼港突出,逃到南麂、大擔嶼等處,往來停泊”(92)之華人海商集團之人數,許棟有多少人? “勝與許棟陸續招集先獲陳四、胡霖,今獲謝洪盛、徐二浦、進旺、千種等并不記姓名千餘人”(93),總數也就是3,000人。
至於雙嶼之戰平托稱葡人死亡800人,這一數據不太確切。查《甓餘雜集》所記雙嶼之戰,斬獲人中并無一確切佛郎機人,信言“攻殺番賊,落水不計其數”(94)。在俘獲人中,亦僅三名黑番係佛郎機買來的黑奴。(95)雙嶼港攻破後,逃至閩海的佛郎機人尚有“千餘”,如再加上死去的八百,那雙嶼港在當時的佛郎機人數應有兩千。這個數據偏大,據葡文資料,至1563年,澳門開埠十年,人口總數5,000人,內有葡人僅900人;(96)即使到17世紀澳門人口發展到三、四萬時(97),而真正的葡萄牙人也祗有850人。(98)所以,我們估計在1548年左右,Liampo港不可能聚居有兩千真正的葡萄牙人。前面所言1,200名葡萄牙人應該是包括相當一部份黑奴的。(99)雙嶼之戰,平托稱葡人死八百,應該是誇大之言,從《甓餘雜集》報導的詳細資料可以看出,雙嶼之戰葡人死亡人數未見明確報導,而在閩海一系列戰役中葡人死亡及被捕人數明顯比雙嶼多:
本月二十日,兵船發走馬溪(……)將夷王船二隻、哨船一隻、叭喇唬船四隻圍住。賊夷對敵不過,除銃鏢矢石落水及連船飄沉不計外,生擒佛郎機國王三名(……)白番(……)共十六名,黑番鬼(……)四十六名,李光頭(……)等一百十二名,番賊婦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斬獲番賊首級三十三顆,通計擒斬二百三十九名口顆。(……)(七月)初四日寅時,賊船二十六隻與夷船合 ,共四十餘隻,官兵張文昊(……)等奮勇衝鋒,擒獲夷賊呵哩(……)一十六名,海賊陳本榮(……)四十七名,斬獲夷首級三顆。(……)閔溶等兵船擒獲夷賊胡馬丁、蘇滿二名。(……)王麟兵船擒獲喇噠胡霖(……)一十二名,殺死夷賊一名(……)其餘燒沉彭坑國大船一隻、哨馬船二隻、佛郎機中船一隻。(……)十七日,(……)李典等兵船破敵,傷殺番賊不計。(……)十八日夜,(……)射死番船放銃手二名,各兵船衝破夷船一隻,沉水渰死不計,擒獲番賊乜寺(……)共一十三名口,喇噠柯岳(……)共三十名口。二十日又有佛郎機國王船續到,勢益猖獗。(……)到任半年,擒賊已踰數百。(100)
,共四十餘隻,官兵張文昊(……)等奮勇衝鋒,擒獲夷賊呵哩(……)一十六名,海賊陳本榮(……)四十七名,斬獲夷首級三顆。(……)閔溶等兵船擒獲夷賊胡馬丁、蘇滿二名。(……)王麟兵船擒獲喇噠胡霖(……)一十二名,殺死夷賊一名(……)其餘燒沉彭坑國大船一隻、哨馬船二隻、佛郎機中船一隻。(……)十七日,(……)李典等兵船破敵,傷殺番賊不計。(……)十八日夜,(……)射死番船放銃手二名,各兵船衝破夷船一隻,沉水渰死不計,擒獲番賊乜寺(……)共一十三名口,喇噠柯岳(……)共三十名口。二十日又有佛郎機國王船續到,勢益猖獗。(……)到任半年,擒賊已踰數百。(100)
可見,雙嶼之戰後,雙嶼港逃出來的海盜及佛郎機人又多次與明軍發生戰鬥,其中溺死、戰死者不計其數,僅被抓獲者就“已踰數百”。可證,平托書所言Liampo港殺死葡人800人之數據應是從雙嶼到走馬溪這一系列戰役中死亡之數的混記。(101)走馬溪之役後,“又有佛郎機國船續到,勢益猖獗”,完全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葡萄牙人在閩浙海上活動人數之多,勢力之大。亦可旁證,這一系列戰役中,葡人死亡800人并非不可能的事,當然這些葡人還應包括相當部份黑奴。前面列舉的俘獲有名字者就有百餘人,其中亦有部份葡人捕後被斬首示眾。透過上述資料及其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平托關於雙嶼港之戰的記錄應該説是基本可信的,但這些記錄不應該是他自己親身經歷,很可能是得自從雙嶼港、走馬溪逃出來的葡商之口。最後還必須指出一點,平托將明軍進攻Liampo港的時間記錄為1542年,此當誤記。根據各種中文文獻的確鑿記載,此事發生在明嘉靖二十七年(102),即1548年。
八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如果以當時的中文文獻特別是朱紈所著的《甓餘雜集》中的有關雙嶼及佛郎機人的記載與平托《遊記》中Liampo紀事比勘的話,即可發現,平托《遊記》中反映歷史事件的主幹內容均與中文記載相合。16世紀中葉,中國浙江寧波外海的Liampo(雙嶼)港曾是葡萄牙人同中國海商及其他各國海商共同開發的一頗具規模與頗為繁榮的國際貿易港。平托所揭示的這一事實,是可獲得中文文獻驗證的,決非誇大或謊言。當然,我們并不排斥平托在講敘這一事實時某些細節的誇大及個別情節的杜撰,但從Liampo紀事的主要內容而言,應該是可以相信的。
【註】
(1)龍斯泰(A. Ljungtedt)《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徐薩斯(Mone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白樂嘉(J. M. Braga)《西方的開拓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博克塞(C. R. Boxer)《South China in the Sixtenth Century》、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藤田豐八《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方豪《十六世紀浙江國際貿易港Liampo考》及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均涉及本文提出的問題。
(2)方豪先生《十六世紀浙江國際貿易港Liampo考》初名《明嘉靖間葡人在寧波被屠問題》,發表於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新北辰》第三卷第五期;第一次修訂發表於《中外文化交通史論》,改名為“嘉靖間葡萄牙人在寧波被屠問題”;第二次修正發表於民國三十三年《復旦學報》第一卷第一期,改名“十六世紀我國通商港Liampo位置考”;第三次修正載民國三十七年出版之《方豪文錄》,改名為《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Liampo考》;第四次修訂改今名,於民國五十七年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頁91-121。
(3)(法)高迪愛(H. Cordier)《中國全史》第四冊,Loyde,1911;戴遂良(L. Wieger)《史料集》p.2035,Sienshien,1930;裴化行(H. Bernard)《十六世紀天主教在華傳教志》,中譯本頁51,商務印務館,1936年;(德)舒拉曼(Schurhammer)<平托及其遊記>,載《大亞細亞》雜志,1927年第三冊,Leipzig出版;康格里夫(W. Congreve英國喜劇作家)《為了愛情而愛》第二幕第一場,轉引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頁95,中華書局,1988年;藤田豐八<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博克塞(C. R. Boxer)《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ntroduction 1,p. xxiii;洛瑞羅(R. M. Loureiro)《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集》p.138,載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三十一期,1997年。
(4)(89)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頁89-90,中華書局1988年。
(5)(74)(葡)洛瑞羅(R. M. Loureiro)所用《遊記》為里斯本官印局1988年葡文版,文載第66-70章,頁187-202;中文由范維信譯,載《文化雜誌》第三十一期,1997年。
(6)方豪所用《遊記》為A Propos des Voyages Aventureux de Fernão-Mendez Pinto,Notes de A. J. H. Charignon,Recueillies et Complétées par Mlle M. Médard,ch. LXVI,LXVII-LXX,pp.124-126,北平,北堂印書館,1936年。
(7)張天澤用《遊記》版本為1931年波爾圖版,見《遊記》第二二一章pp.122-124。
(8)(26)(51)(葡)克魯斯(Gaspar da Cruz)《中國概説》第二十三章,巴塞羅斯,波爾都卡倫塞出版社,1937年版,中譯本載《文化雜誌》第三十一期,1997年。
(9)同上書第五章。
(10)(28)(葡)寇圖(Diogo do Couto)《Decada Quinta da Asia》,LivroⅢ,Cap,頁262-263,里斯本,1612年。
(11)(葡)曼里克(Sebastião Manrque)《東印度傳教路線》第二卷頁144-145,里斯本,1946年西班牙文版,中譯載《文化雜誌》第三十一期,1997年。
(12)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頁16,澳門,1926年。
(13)天啟《舟山志》卷二<山川>。
(14)(17)(18)(19)(50)(明)朱紈《甓餘雜集》卷四<雙嶼填港工完事>,天津圖書館藏明朱質刻本。
(15)張增信認為雙嶼即今舟山島西南灣內的“盤峙”與“長峙”二島,彼此左右對峙,形成大門。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頁237,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1988年。
(16)《指南正法》,見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之乙種,中華書局,1961年版。
(20)《明史》卷二○五<朱紈傳>。
(21)(30)(33)(75)(明)鄭舜功《日本鑑》卷六《海市》,民國二十八年影印本。
(22)(38)(57)(65)(83)(91)(100)(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
(23)(29)(明)鄧鍾《籌海重編》卷十<經略>二。
(24)(46)(明)俞大猷《正氣堂集》卷七<論海勢宜知海防宜密書>。
(25)(意)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不得已辨》,載《天主教東傳文獻》第一冊頁318,臺北學生書店,1965年。
(27)(葡)巴羅斯(João de Barros)《Do Asia Decada 3》,轉引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77年。
(31)(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五<浙江倭變記>、謝傑《虔臺倭纂》卷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十一冊《浙江》上。
(32)(明)馮應京輯《皇明經世實用編》卷八<海防>,明萬曆刊本。
(34)(49)(55)(79)(88)(94)(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二<捷報擒斬元凶為平巢穴以靖海道事>。
(35)(85)(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二<瞭報海洋船隻事>。
(36)(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卷二<湖廣按察副使沈密傳>,明崇禎刊本。
(37)(90)(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二<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
(39)上述人名見於朱紈《甓餘雜集》卷二<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卷四<三報海洋捷音事>、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等。文中明確指出為“佛郎機”者有十人,其白番十六人亦就是佛郎機。其中夷賊十五名及番賊十三名,余亦懷疑為佛郎機人,其名多以“寺”為尾音,葡人名多以“S”音結尾,如《甓餘雜集》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共帥羅放司,年二十二歲,佛德全比利司,年三十三歲(……)俱佛郎機國人。”俱以“司(S)”音結尾。故疑夷賊“唵陀呢寺”當即葡名Andres之譯;番賊“馬低寺”,當即葡名“Mendes”之譯;夷賊“唵密寺”當即葡名“Amys”之譯;“葛臘寺”當即葡名“Couros(Coros)”之譯;至於四十六名黑番,當即葡人之黑奴,故亦多視為佛郎機人。《甓餘雜集》卷二<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明載:黑番鬼三名均是被佛郎機買來;同書卷三<亟處失事官員以安地方事>則稱:“佛郎機夷人大船八隻、哨船一十隻徑攻七都沙頭澳,人身俱黑。”可見這些屬於葡人的黑奴均被視為“佛郎機”。
(40)(明)《甓餘雜集》卷九<公移>三。
(41)(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稱,1539年三位葡人抵達日本一座島嶼,1542年,葡萄牙開始通過寧波與日本通商。日本文獻《採覽異言》稱“西蕃之來自北國(波爾杜瓦爾),始天文十年(1541)辛丑秋七月焉,有海船一隻,直到豐后國神宮浦,其所駕者二百八十人。”又《籌海圖編》卷五<浙江倭變記>:“(嘉靖)十九年(1540),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1540年時,日本人已大量聚集浙海,與葡人貿易,1541年時,葡萄牙商船已到達日本,日葡貿易正式開通。
(42)參見(日)木宮彥泰《日中文化交流史》第四章《明朝末年中日間的交通》頁616,商務印書館,1980年。
(43)(英)博克塞(C. R. 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全漢昇《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載《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
(44)(80)(82)(95)(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二<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45)(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二<海洋賊船出沒事>。
(47)(明)龐尚鵬《百可亭摘稿》卷一<撫處濠鏡澳夷疏>。
(48)(77)(81)(明)謝傑《虔台倭纂》卷下,萬曆二十三年刊本影印本。
(52)(葡)佚名《市堡書》,《文化雜誌》第31期,1997年。
(53)(明)朱紈《甓餘雜集》卷六<軍令軍法以安地方事>。
(54)(明)朱紈《甓餘雜集》卷五<申論議處夷賊以明典型以消禍患事>。所謂矮王、小王、二王,據文稱均為“佛郎機國王”、“麻六甲王子、王孫、國王嫡弟”等,實際上是當時明軍想邀功而謊報的軍情。這一點在克魯斯《中國概說》第二十四章中予以揭露:“水師指揮官,亦即Lutici(盧都司:盧鏜),對此役旗開得勝、躊躇滿志。他接著將一些同葡人一起被俘的華人嚴刑拷打。他設法誘使四個相貌比別人長得好看的葡人自稱為麻剌甲國王。他終於同他們串通好了,因為他答應給他們優待(……)讓他們穿戴上麻六甲國王的長袍和帽子,以偽亂真,使自己的勝利顯得更輝煌,(……)在老百姓面前沽名釣譽,在皇帝面前邀功請賞。(……)為了遮人耳目,騙局不至於被揭穿,他就對那些同葡人一起被俘的華人下毒手,將其中一些人殺掉,并決定將其餘的人亦置於死地。”後案發,朱紈、柯喬、盧鏜等均被牽涉革職,朱紈自殺。
(56)(明)崔涯《筆山文集》卷一,明萬曆刊本頁34。
(58)(明)朱紈《甓餘雜集》卷四<海賊登岸殺戮軍民事>。
(59)(明)王士騏《皇明馭倭錄》卷五嘉靖二十八年紀事,萬曆刻本影印本頁8。
(60)雙嶼港之暹邏商在《甓餘雜集》中還有多處記錄,卷三<海洋賊船出沒事>:“內地叛賊(……)糾引(……)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港內停泊。”卷四《三報海洋捷音事》:“擒……暹羅夷利引、利舍、利璽三名。”卷四<五報海洋捷音事>:“生擒暹羅國番一名蒲玭(……)生擒暹羅國番寇一名撇鐵。”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又有三桅大船一隻、二桅中船二隻,用五色布帆掛起‘暹羅国’三字,人古雷海洋。”
(61)(66)(明)田生金《按粵疏稿》卷五<報暹羅國進貢疏>,粵雅堂翻刻本。
(62)(明)佚名《暹羅國譯語》不分卷<人物門>,清抄本影印本。
(63)陳學霖<暹羅入明貢使“謝文彬事件”剖析>,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編《史藪》第二卷頁152,1996年及《暹羅館譯語》。
(64)(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7)(日)藤田豐八<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載《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
(68)(明)朱紈《甓餘雜集》卷六<謝恩事>,卷二<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亦有:“福清等縣通番喇噠,見獲林、爛四等”。
(69)(明)蔡汝賢《東夷圖像東夷圖説》不分卷之<佛郎機>,明萬曆刻本。
(70)(明)黃衷《海語》卷上<滿剌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1)張禮千《馬六甲史》第一章<馬六甲王國>頁108,商務印書館,1929年。
(72)(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三<大泥>。
(73)(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
(76)(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日本諸夷》,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8年。
(78)(明)萬表《海寇議》前編頁2,明嘉靖金聲玉振集本影印本。
(84)(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二十八,四庫存目叢書頁23。
(86)(明)沈越《皇明嘉隆聞見錄》卷七嘉靖二十六年紀事,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影印本。
(87)(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日本諸夷》及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十一冊<浙江>上。
(92)(93)(明)朱紈《甓餘雜集》卷四<三報海洋捷音事>。
(96)(法)裴化行(H. Bernard)《十六世紀天主教中國傳教誌》,商務印書館,1936年。
(97)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之<日漸茁壯的華人地方教會>,打印本,頁9。
(98)(葡)博卡羅(A. Bocarro)《1635年的澳門》,載C. R. 博克塞《十七世紀的澳門》頁14-35,香港,1984年。
(99)《甓餘雜集》卷四<三報海洋捷音事>:“生擒黑番鬼共帥羅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安朵二、不禮舍識、畢哆囉、來奴八名。”同書石卷同疏章又稱:“共帥羅放司(……)佛全比利司(……)俱佛郎機人。”可見,當時人們是將葡人的黑奴亦稱之為佛郎機的,故多數文獻稱佛郎機有黑白二種,見《澳門記略·澳蕃篇》。
(101)燼管平托《遊記》第二二一章仍提到1549年有近500葡萄牙人被殺之事。實際上從浙海到閩海一系列與明軍的戰鬥中,佛郎機人共死去800人大致可信,但這裡面主要是“黑番”。平托直到晚年才完成這部作品,靠回憶記錄的歷史事實,將時間與數據記混是完全可能的。
(102)(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五<浙江倭變記>,謝傑《虔臺倭纂》卷下,王鳴鶴《登壇必究》卷二十九<火器>、鄭舜功《日本一鑑》卷六<海市>及<甓餘雜集>多篇。
*湯開建,廣州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