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圖: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上層中央神龕中之耶穌銅像〕
〔上圖: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上層中央神龕中之耶穌銅像〕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長崎,研究它的歷史。眾所周知,這一歷史從面向澳門開始。為接待來自澳門的船舶并為其提供安全的停泊地,長崎港於1570年開放。我經常從長崎去澳門朝聖。在大三巴牌坊的倩影下,在內港喧囂的生活中或在大炮臺的城牆邊,我從大海彼岸重溫長崎的歷史。
我應約寫那段歷史。主要寫兩點:聖保祿學院與其所代表的一切和作為基督世紀期間日本教會之首的長崎。短短幾頁難以寫下那麼多歷史。因此我決定少量地挑選一些章節、象徵和一些至今仍維繫着我們但有時又視而不見的紐帶。
那是在1627年:長崎敎會已經英勇地頂住了十三年之久的殘酷迫害,但是在加美新統治者水野川地(Mizuno Kawachi)的鐵腕下,現在變得支離破碎。這個德川家光的忠實工具實行恐怖統治,其主要目的是鎮壓敎會的領袖。十字街(Crus-machi)監獄關滿了傳敎士。剩下的基督徒音那(Otona),若奧·町田草加(João Machida Soka)和托梅·後藤宗印(Thome Goto Soin)連同他們的家人一起被押往江戶受審;入敎的大名小西行長Konishi Yukinaga)和高山右近(Takayama Ukon)家族的一批武士被流放到澳門。他們乘路易斯·帕埃斯·帕切科(Luis Paez Pacheco)的貨船抵達。但是,監獄的折磨,艱難的航程和氣候的變化使他們虛弱的身體難以承受。抵達後沒幾個月,所有的這些人都離開了人世。
被流放的武士有:迪奧戈·日比谷(Diogo Hibiya Ryokei)的孫子萊奧·小西彌左衛門(Leo Konishi Yazaemon),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曾在他家建立避難所;八代(Yatsushiro)城堡首領迪奧戈·道后美作(Diogo Mimasaka)的兒子哈科韋·小西忠二郎(Jacobe Konishi Chujiro);托梅·小西源家門(Thome Konishi Geniemon)和本托·左太夫(Bento Sadayu),後者來自高山右近家族,與殉敎者迪奧戈·加賀山勇人(Diogo Kagayama Hayato)的侄女結婚。他們都是長崎仁慈公會的會員,身著該會的會服安息在聖保祿學院附近的聖母敎堂。(1)這一事件有幾分高潮,也像我在此要介紹的歷史象徵。聖保祿學院及其敎堂通過友誼和文化交流的美好歷史以及血的紐帶與日本敎會聯結在一起。所有其他活動都在“仁慈公會”的精神氛圍中蓬勃開展。
三個以聖保祿命名的學院就像耶穌會傳敎士在亞洲艱難跋涉途中的里程碑,它們分別位於果阿、澳門和長崎。第一個在果阿的聖保祿學院約於1540年聖方濟各·沙勿略抵達印度時建成。今年我們慶祝澳門聖保祿學院成立四百週年。長崎的聖保祿學院始於1597年,但其前身成立於近二十年前。它是由范禮安(Fr. 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於1580年在府內(大分市的舊稱)開辦的;1590-1597年,它作為敎育中心在天草的川內浦(Kawachinoura)鼎盛一時,在二十六名聖徒殉敎後,遷往長崎。在迪奧戈·德·梅斯基塔(Diogo de Mesquita)神父的領導下,這所學院在那裡作為文化和宗敎中心進入全盛時期,一直到1641年。那年11月,梅斯基塔神父被迫害致死,學院也被取締。
除了成立的日期外,生活和工作在那裡的人們是澳門和長崎兩個學院之間的真正紐帶。由於無法在這裡介紹所有事件,我想引介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并讓他們來講話。
天昭時代的四位使者
他們的名字在日本家喻戶曉:曼修·伊藤(Mancio Ito)、米蓋爾·千千石(Miguel Chijiwa)、馬丁·原(Martin Hara)和胡利安·中浦(Julian Nakaura),以及他們的同伴若熱·德洛約拉(Jorge de Loyola)和康斯坦蒂諾·多拉多(Constantino Dourado),他們都是日本人。在耶穌會遠東巡閲使范禮安神父的啟示下,三名九州島入敎的大名--豐后的弗朗西斯科·雄友(Francisco Otomo Sorin)、有馬的普羅塔修·有馬晴信(Protasio Arima Harunobu)和大村的貝爾托拉梅烏·尾村秀康(Bertholameu Omura Sumitada)一決定派一個使團去葡萄牙王國并去朝見敎皇。他們挑選了四名在有馬修道院學習的13-15歲的男孩作為使者。這個起初毫不重要的使團在歐洲卻引起極大的興趣,成為17和17世紀日本和南歐人民之間文化聯繫的象徵。現代有關這個使團的文學作品不斷增加,這顯示上述現象不是無緣無故的。(2)
那些使節來澳門兩次:1582年3月9日至12月31日去歐洲的時候和1588年至1590年6月23日返回日本途中。1582年他們住在耶穌會會院。他們都是孩子,沒事時就學習拉丁文和葡文。但他們第二次來澳門時,已不是修院的學生,而是以使節身份見過公爵、國王和敎皇的年輕人。他們被羅馬元老院授予“羅馬公民”的稱號并被敎皇西克斯圖斯(Sixtus)五世封為“聖彼得騎士”。
由於這些原因,他們被安排住在專為他們準備的屬於聖保祿學院的一棟房子裡,與耶穌會的住所分開,但共走一個大門。這時形勢迫使他們在澳門滯留兩年,他們的活動如實記載在澳門耶穌會士的信件裡。主要的記錄者是洛倫佐·梅希亞神父(Lorenço Mexia),他曾是范禮安的秘書,1582年同那些使者乘坐伊格納西奧·德·利馬(Ignacio de Lima)的船從長崎來到澳門。我們從梅希亞神父樸實的信中選擇幾段。首先是他們重逢時的興奮:
巡閲使7月18日抵達這裡,帶來16名本會成員和日本貴族。感謝上帝,所有人的身體都很好。我們感到十分高興和欣慰,因為已經等待他們一年多了。貴族們被安排在我們院內的一座房子裡,為他們配備了上好的傢俱。他們在那裡住下,有時來我們的餐廳吃飯。他們善於利用時間,遵守梅斯基塔神父的安排,神父總在他們那邊。他們像入教者一樣經常去懺悔并領受聖餐。我想他們慢慢會成為教徒。(3)
返回的興奮情緒被豐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在日本開始迫害(天主敎)的消息所削弱。由於隨同范禮安來的耶穌會士很多,也出現一些住房和食品問題。

</figcaption></figure>
<figure><img src=) 聖方濟各·沙勿略寫給印度耶穌會神父麥斯特·卡斯帕·巴違沙爾·卡格和多明我·加瓦洛請他們到日本的手書(1546年11月5日)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聖方濟各·沙勿略寫給印度耶穌會神父麥斯特·卡斯帕·巴違沙爾·卡格和多明我·加瓦洛請他們到日本的手書(1546年11月5日)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巡閲使和日本貴族來時带來其他許多人,今年這座房子全住滿了,有一百多人。雖然巡閲使提供一半的開支,還是難以滿足需要。澳門很小,已婚的葡人不過200人,他們已經維持著一所醫院和四十四名個痳瘋病人,一所仁慈堂和那些在監獄的人,以及除我們自己之外的三個托缽修會,即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和奧斯定會。此外,收入很少,僅靠一條船每年販運絲綢去日本,再带回白銀。除了這條船運回的東西外,他們沒有其他來源。因此我們給他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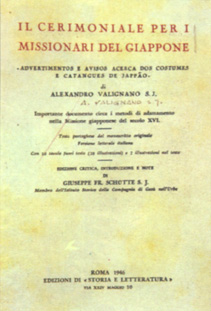 范禮安著作:《日本傳敎士之敎規》封頁(羅馬·1546)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范禮安著作:《日本傳敎士之敎規》封頁(羅馬·1546)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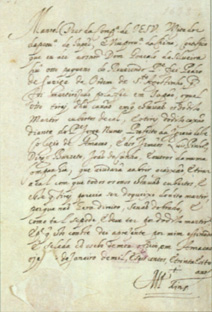 陽瑪諾(1638年1月6日)於日本寫的證明書手稿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陽瑪諾(1638年1月6日)於日本寫的證明書手稿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問題還不僅僅限於耶穌會和使者。講述過使者們因不能在當年返回日本而產生的失望後,梅希亞幽默地評論道:
日本貴族們也都垂頭喪氣,但他們并不浪費一分鐘,總是忙於學習拉丁文、音樂等東西。他們真不錯,從不添麻煩。祇是巡閲使給暴君帶的馬給添了許多亂子,這些馬總在房門口,但看在巡閲使的好意上我們就忍受了。
可憐的看門兄弟! 那兩匹阿拉伯良種馬是堂·杜阿爾特·德梅內塞斯在果阿提供給使者的,從果阿運到科欽,又從那裡經馬六甲運到澳門。其中一匹死於澳門,另一匹到了長崎,從那裡又去了京都,牠以其高傲的步態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最後竟在葡萄牙馬術師的指揮下,跳躍起舞。這場表演贏得了豐臣秀吉的歡心。使者曼修在儀式中當翻譯。“從聖保祿學院的大門到大光左馬(Taikosama)的馬廄”可作為給這匹名馬立傳的題目。(6)
但不是一切事情都有問題和麻煩。梅希亞自己向我們講述了四位使者1589年1月1日的表演。這次音樂會大概是在聖保祿學院的餐廳聚餐慶祝耶穌會的節日後舉行的。
旅途中他們(四位使者)沒有荒廢時間,而是學習彈奏各種樂器。割禮節那天他們作了表演,使我們大飽耳福,他們一人彈豎琴,一人彈擊弦古鋼琴,另外兩人拉小提琴。若熱·德洛約拉兄弟也作了表演,比旅途中學習時有了很大進步。(7)
如果我們記起使者們在葡萄牙的最後幾個月一邊等待離開的船隻一邊在里斯本最好的老師指導下學習音樂,我們就可想象到在那場音樂會中當演奏葡萄牙樂曲時,澳門老傳敎士們的心中如何勾起思鄉的情調。使者們在澳門的活動不僅限於學習音樂,他們寫信感謝歐洲的一些重要人物,以加強友好聯繫,為我們留下了重要的歷史文獻。他們在旅途中寫的日記和記錄為范禮安寫作關於這個使團的對話錄提供了資料。此書被孟三德(Duarte de Sande)神父譯成高雅的拉丁文。後來,梅希亞神父在里斯本購置了一臺印刷機,在若熱·德洛約拉、康斯坦蒂諾·多拉多和年輕的阿戈斯蒂尼奧(Agostinho)的幫助下在澳門出版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書籍。梅希亞説:
今年在這裡印刷了博尼法西奧(Bonifacio)的兩本書。關於日本貴族旅行的《對話錄》正在印刷。我們希望所有這些工作能對日本的修道院有所幫助。(8)
作為一位忠實的秘書,梅希亞告訴了我們范禮安的目的:所有印刷活動都是為了培養日本耶穌會士、傳道員和其他助手。這是范禮安最重視的工作之一,就像我們將後面看到的,它把聖保祿學院更有力地與日本敎會聯繫在一起。但就像總要發生的一樣,這項重要工作需要作出更痛苦的犧性;這次的遇難者是若熱·德洛約拉敎友。他離開葡萄牙時已經患病,艱難的航行又加重了他的病情。在澳門潮濕的環境裡工作耗盡了他最後的體力。他於1589年9月16日去世。這次他的同伴米蓋爾·千千石作了記述:
一個月前,上帝召喚我們的老伙伴若熱·德洛約拉兄弟去安息了。他患上了肺結核,吐血,最後死於中國。他的去世像他的工作一樣給人以啟迪,由於這個原因及我們希望他去日本佈道,做出傑出的貢獻,我們對他的去世深感悲痛。(9)
1589年3月,熱羅尼莫·佩雷拉的船在長崎渡過冬天後抵達澳門。據梅希亞説,一千多人乘該船抵達。他們因害怕豐臣秀吉而離開長崎。豐臣秀吉禁止基督敎後又奪取了長崎,并將長崎併入他直接管轄的領地。
一下來了那麼多難民引發了一場瘟疫,造成許多人死亡,其中有耶穌會士普雷內斯蒂諾神父(Prenestino)。他也是坐那條船來的,準備在澳門敎孩子們葡文語法。可能因為那場混亂,船長熱羅尼莫·佩雷拉從他的船上跳入內港渾濁的水中自殺。這是范禮安神父和他的人那年沒能去成日本的主要原因。1590年6月23日,期待已久的出發終於實現。那天,范禮安在聖母敎堂舉行彌撒,然後一大群傳敎士和那四位使者從聖保祿學院去內港登上安東尼奧·達科斯塔的船。在一些旅客的抱怨聲中,那匹阿拉伯馬在船上找到了位置。
使者中的三個人以後幾年又返回澳門,有的作為學生,有的作為流亡者,但那段歷史屬於不同的章節。不過范禮安神父已想好培養日本耶穌會士的新計劃。這個計劃將導致澳門和日本之間海上來往的增加,并將加強聖保祿學院和日本敎會的聯繫。
在此,我們可以補充一些天昭時代的使者和聖保祿學院之間的聯繫。范禮安將阿拉伯馬交給豐臣秀吉并為那四位已成為天草耶穌會見習修士的使者祝福後,於1593年從長崎返回澳門。他像他的老伙伴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一樣利用這段時間。弗洛伊斯在聖保祿兩年期間,不僅為他的《日本歷史》的最後一章搜集了資料,而且還撰寫了關於四位使者出使的著名論文,後來幾乎所有關於這個使團的書籍和文章都以這篇論文為基礎。(10)儘管年邁多病,弗洛伊斯決定返回他所熱愛的長崎聖保祿學院。他於1595年抵達,正好趕上寫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1597年2月5日,日本二十六位聖徒在西阪山(Nishizaka)被釘死在十字架上。3月15日,弗洛伊斯在他的《殉敎記》的最後一頁簽上名。三個月後的7月6日,他在聖保祿學院自己的居室裡逝世,被埋葬在附近的耶穌會士墓地。1997年我們將紀念殉敎者和弗洛伊斯逝世四百週年。
聖保祿學院在范禮安日本敎省計劃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范禮安看來,培養當地的神職人員和日本耶穌會士是日本敎會發展的基礎。有馬和安士的修道院,府內學院,修士見習所,印刷機等所有這些都產生於這一思路。現在,使團的成功和對敎會的迫害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計劃。范禮安不是一個遇到問題被人反對(無論大小)就退縮的人,他要周密考慮,開辟新的途徑前進。
除了已指出的兩個情況下,又出現了新的形勢。因為范禮安離開期間,樂觀的加斯帕爾·科埃略(Gaspar Coelho)神父接收了一大批日本人加入耶穌會,修道院裡充滿了希望成為耶穌會“兄弟”的年輕人。那是個好消息,但蘊藏的危險:必須用真正的天主敎敎義和純粹的耶穌會精神培養那些年輕的日本人。然而,在豐田秀吉的走狗們經常巡視的危險條件下,這能在川內浦那個遙遠的村莊實現嗎?
1591年7月25日(四年前的這一天,豐田秀吉曾向科埃略神父發出驅逐令),四位使者被招收進天草的修士見習所。幾個月後,被迫靜候豐田秀吉就已故印度總督梅內塞斯的使團作出答覆的范禮安提出了他的新計劃:送一批日本“兄弟”去羅馬,但這次不是作為使者而是作為耶穌會的學者。在羅馬,他們將學習一切為培養日本耶穌會未來領導人所需要的東西。曼修的信不僅告知了這個大新聞,而且還提到了一些已被指定的人的名字,他的弟弟儒斯托·伊藤(Justo Ito)是其中之一。(11)
在反對派遣年輕的耶穌會士去羅馬的傳敎士中,有一個曾是修士見習所的敎師,名叫佩德羅·拉蒙(Pedro Ramon)。在迫害的打擊下,他於1587年從生月(Ikitsuki)寫了一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強烈批評范禮安的所有想法,尤其是派遣使傳的計劃。在那封信中,拉蒙向會長阿瓜維瓦(Aquaviva)神父介紹了不顧迫害仍要在日本保留敎育機構的烏托邦計劃。按照這個計劃,所有的敎育機構都設在一個城堡裡。但是連拉蒙也承認,問題不在於興建城堡,而是如何讓它維持下去。現在,當范禮安放棄派人去羅馬的計劃時,佩德羅·拉蒙表示讚賞,但他在話裡流露出對范禮安的憎惡:“看來上帝給了他從未有過的靈感。”(12)對派人去澳門一事,我們不知道拉蒙的意見,但這次范禮安是正確的。那時沒有比澳門更好的地方,而且讓日本人與外國人生活在同一個社團內是建立日本敎省的重大步驟。
范禮安於1593年返回澳門後,這一計劃開始被執行。在第一批人中我們發現有兩個傑出人物的名字:一位是被賜福的塞瓦斯蒂安·木村(Sebastian Kimura),他的祖父是武士,1550年曾在平戶庇護過聖方濟各·沙勿略;另一位是路易斯·尼亞巴拉(Luis Niabara)。1601年他們回日本時,路易斯·塞爾克拉(Luis Cerqueira)主敎在新聖母敎堂任命他們為敎士。1662年木村殉敎。尼亞巴拉是英雄的傳敎士,其使徒活動甚至超過了被賜福的木村。1615年他試圖返回日本時因船隻失事遇難。
1601年秋天,參加過木村和尼亞巴拉的聖職授予儀式後,另一批人前往澳門。他們中有曼修·伊藤和胡利安·中浦兩位使者。他們在聖保祿學院學習了三年神學。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其他日本人,如馬丁·式見(Martin Shikimi)和曼修·平林(Mancio Hirabayashi)。在他們的歐洲同伴中有若奧·阿達米(João Adami)、霍安·B.索拉(Joan B. Zola)、本托·費爾南德斯(Bento Fernandez)、若奧·達科斯塔(João da Costa)和克利斯托旺·費雷拉(Christovão Ferreira)。他們是那些將在德川幕府迫害敎會的頭二十年裡在日本承擔重任的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成為殉敎者。
作為那些年在澳門建立的友誼的例證,我們有本托·費爾南德斯和保羅·齋藤(Paul Saito)兩位神父遇害的歷史。兩人都在西阪山上遭受了“坑”刑;但是劊子手們對齋藤神父做得特別過份,幾個小時後把快要死的他拖進附近一個小屋。過了幾小時他還沒死,等的不耐煩的劊子手們焦急地問他:“你甚麼時候死啊?”齋藤神父回答説:“我在等我的同伴。”兩天後本托神父死在坑裡時,那些走狗們又去看躺在小屋裡的齋藤神父,發現他剛剛死去。這件事在澳門1634年舉行的審理中得到證實。他們遇害的日期是1633年10月2日。(13)
但是讓我們再回到聖保祿學院。中浦和他的同伴們來到澳門時,發現自己十分熟悉的敎堂已於前一年11月被大火全部燒燬。重建規劃正在年輕的意大利傳敎士卡洛·斯皮諾拉(Carlo Spinola)的領導下進行。他在去日本的途中,大火發生前幾個月到達澳門。聖保祿學院院長曼努埃爾·迪亞斯(Manuel Dias)請斯皮諾拉這位優秀的數學家設計新敎堂。1601年,副大主敎任命斯皮諾拉為日本敎省駐澳門的檢察員,以便讓他完成這項工作。但斯皮諾拉沒有看到工程的完成。他於1602年7月抵達日世。但是,伊藤、中浦和他們的同伴們參加了1603年聖誕節前夜舉行的盛大的新敎堂啟用儀式。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日本歸來的范禮安也出席了儀式。從現在起,這位老人主要關注在中國的傳敎事業。他於1606年1月20日在聖保祿學院去世。但是,他沒有忘記培養日本耶穌會士這個他最珍愛的想法。臨去世前三天,他忍著巨大的疾病折磨,口述了一份可稱為其最後願望的文件。在這份文件中,我們能發現他對派遣日本敎友去聖保祿學院這一計劃的思想和願望:
我總認為,派遣盡可能多的日本學生來這個學院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可使他們在科學和德行方面取得進步,同時可使他們趕上歐洲的那些人。感謝上帝的仁慈,迄今一切事情都很成功。因此,我請求副大主敎盡可能派更多的日本學生來這個學院。他們將在這裡逗留四至五年,學習德行和科學。即使我們一些神父和敎友們反對,這件事也應該繼續進行。(14)
范禮安至死不渝堅持自己的想法,他的計劃持續到1614年(日本)禁敎而中斷。
從日本流亡
德川家康於1614年1月發佈的法令使聖保祿學院和日本敎會之間的關係有了一個新的特點。那年11月,若奧·達庫尼亞的船抵達澳門,帶來62名耶穌會士。在這些流亡者中有馬丁·原和康斯坦蒂諾·多拉多,以及喬瓦尼·科拉(尼科勞)Giovanni Cola(Nicolão)畫室的一班“畫家兄弟”。和這些傳敎士一起來的還有不少“獨行者”。
這些耶穌會士中的許多人試圖重返日本并獲得成功,在那裡秘密傳敎。但那些身體不好或年邁的人,以及那些因其地位被長崎當局熟悉的人祇能在澳門渡過餘生。其中一人是馬丁·原,精通葡文,容易適應聖保祿學院的生活。他後來被稱為馬丁·多坎波(Martin do Campo),像在長崎一樣,他和好朋友若奧·羅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 Tsuçu)一起合作,後者前些年因各種理由被驅逐出長崎。(15)康斯坦蒂諾·多拉多最後實現了成為神父的夢想并被任命為澳門修道院的院長,他擔任這個職務一直到1620年去世。那班隨尼科勞大師來的畫家兄弟們忙於裝修聖母敎堂。從1603年起,哈科韋·丹羽(Jacobe Niwa)一直在從事這項工作。這是日本耶穌會士感謝聖保祿學院的標誌。
那些流亡的獨行者的歷史對於我們來説尤為有趣。他們在聖保祿學院的社團內組成一個小團體。他們都説不好葡文,除了繼續他們的學習外在澳門也沒有特別的工作。不止一個老傳敎士批評瓦倫廷·卡瓦略(Valentin Carvalho)副大主敎從日本帶出的獨行者太多,用馬特烏斯·德科羅斯的話説,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很好的傳敎員”。日本兄弟尼科勞·桂庵福良(Nicolão Keian Fukunaga)是這群人的負責人,由於卡瓦略性格嚴厲,他受了不少苦。卡瓦略對獨行者們説,他們沒有用了,永遠不會被吸收入耶穌會。這在獨行者和日本兄弟中引起一些騷動,其中一些人返回日本,另一些人去了馬尼拉并在那裡成為其他修會的成員,最後還有一些人去了羅馬,以實現他們加入耶穌會的心願。
如果我們注意一下那些獨行者走過的道路,我們就能明白卡瓦略所犯的大錯誤。在那些去長崎的人中,有五個人在冰見變為隱士,并在那裡幫助被迫害的敎徒,直至他們自己也被關進大村的監獄。在那裡,斯皮諾拉神父當過兩年多見習修士的老師,經副大主敎的允許吸收他們入會,他們都在1622年9月10日的大屠殺中殉敎。斯皮諾拉和五位獨行者-隱士都是耶穌會中被賜過福的人。加入其他修會的有聖文森特·鹽冢(St. Vincente Shiozuka)、聖托馬斯·西(St. Thomas Nishi和傑出的托馬斯·德聖阿古斯丁·金鍔(Thomas de San Agustin Kintsuba)。去羅馬的人有佩德羅·城部家須(Pedro Kibe Kasui)、米蓋爾·米諾埃斯(Miguel Minoes)和曼修·小西(Mancio Konishi)。這些名字現在屬於全世界的敎會,但他們與聖保祿學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曾在那裡生活,遭受磨難,并決定了實現他們志向的道路。(16)
對那些返回日本的耶穌會士來説,聖保祿學院既是避難所,又是衝向犧牲的基地。那群獨行者解散時,尼科勞·桂庵兄弟也重返了日本。他出生在琵琶湖畔的一個武士家庭,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大村灣周圍沒有敎堂的小村莊裡渡過的。耶穌會士名錄中祇提到一件有關他的事:“他佈道。”“他用日文佈道講得非常好。”最後又補充道:“他因宣講基督敎義而死。”1633年7月29日,他在西阪的刑塲被施以“坑”刑。他是第一個受這種刑罰的傳敎士。一連三天,他頭朝下吊在一個狹窄的坑裡。即使這樣,他仍向劊子手們佈道。1634年在澳門開始審理記錄下那些細節後,以這一句話結束:“他死於7月31日的聖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節,舉行盛大彌撒之際。”那個盛大的彌撒當然是在聖保祿學院敎堂舉行的。(17)
大多數無法返回日本的傳敎士死於澳門。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澳門做了很好的工作,例如佩德羅·莫雷洪神父(Pedro Morejon)曾擔任聖保祿學院院長多年,為推動給那些殉敎者賜福做了突出貢獻。那些年,聖母敎堂變為來自日本的耶穌會士的萬神殿。敎堂1603年落成時,在此之前死於澳門的耶穌會士的聖骨,從賈耐勞(Melchior Carneiro)主敎開始,都被移放到敎堂;其中有洛約拉兄弟的聖骨。那年第一個被埋葬的耶穌會士是年輕的日本敎友阿戈斯蒂尼奧。
閲讀埋葬在聖保祿學院的日本耶穌會士名單,如同浪漫地回顧那個年代日本敎會的歷史。我不想在此介紹全部名單,僅回顧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耶穌會士。(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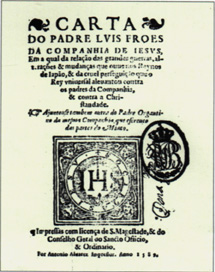
耶穌會士路易斯·福萊斯的《日本書信集》(1589)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藏
范禮安列於名單的第一位。他被埋葬在主祭壇的內殿裡,朝向福音一邊,略低於三位主敎:謙卑、對窮人充滿愛心的賈耐勞主敎,他曾任命日本最偉大的傳敎士之一路易斯·德阿爾梅達(Luís de Almeida)為敎士;路易斯·塞爾克拉主敎,他是唯一一位有機會在日本敎區生活過的主敎,并在那裡進行了出色的工作;以及迪奧戈·瓦倫特主敎,他從未到過日本,但把工作委托給代理主敎。
范禮安去世那年,日本傳敎團的神學家佩德羅·德拉克魯斯也死於聖保祿學院。接著去世的是另一個意大利人巴范濟(Francisco Pasio)神父,他曾任日本敎省的大主敎和巡閲使,禁敎令發佈前就流亡到澳門。1614年,曾為使者們的同伴、排印工、有馬修道院學監和澳門修道院院長的唐斯坦蒂諾·多拉多去世。佩德羅·竹庵(Pedro Chikuan)於1622年逝世,他的歷史我們從1567年科斯梅·德托雷斯神父在口之津給他洗禮那天的開始有所瞭解。作為耶穌會會友,他在天草學院工作,在那裡學習了印刷術,成為耶穌會出版社的主要人員。1623年,阿豐索·德盧塞納神父也安息了。他在大村擔任修院院長和敎區神父二十多年,是大村大名秀康(Sumitada)一家的好朋友。在澳門期間,他撰寫了回憶錄,這是關於大村敎會的一份珍貴記錄。
1626年,日本敎會的藝術大師喬瓦尼·科拉(尼科勞)去世。他從果阿抵達澳門時,范禮安神父和使者們正在去羅馬的途中。1583年他到日本,先在有馬,後去天草和長崎學院。他的藝術作品包羅萬象,從印刷聖畫用的小巧銅雕,到巨型的油畫、樂器、竹管樂器、樓鐘和墓碑。1992年和1993年,在長崎那所古老學院附近的街道上,工人們在挖掘中發現了1601年被大火燒燬的遺址。每個房間裡都發現了尼科勞畫中典型的帶有十字花型的屋頂瓦片。最為重要的,是他培養了第一批把日本靈感與新的歐洲技巧融為一體的畫家,聖母敎堂就是其藝術的見證。尼科勞埋葬在耶穌祭壇前面;他的弟子曼修、田出夫(Tadeo)、佩德羅·竹庵(Pedro Chikuan)和哈科韋都埋葬在聖彌額爾(St. Michael)的祭壇前面,不知是有意還是偶然。難道保存至今的聖彌額爾的油畫象是他們之中某人的作品嗎?有誰知道,現在仍保存在羅馬哥蘇敎堂的那幅表現1622年殉敎事件的著名油畫,又是哪個日本藝術家的大作呢?
但是,那幅表現所有1640年前殉敎的耶穌會士的油畫則屬於另一代畫家,因為尼科勞的最後一個弟子丹羽逝世於1638年,1627年。曾在日本任見習修士老師的塞爾索·康法洛內羅(Celso Confaloneiro)逝世。囿於成見,他曾反對給日本的耶穌會士授予聖職,他對范禮安的決定有強大的影響力。兩年後,馬丁也在澳門逝世,安葬在聖方濟各·沙勿略小堂通往內殿的拱門一邊。1633年若奧·羅德里格斯結束了他漫長而多產的一生。他個人本身就是聖保祿學院和長崎歷史上的一章。還有其他許多人,但我在此用莫雷洪的名字結束這個名單。他於1639年12月11日逝世,安葬在內殿,靠近帕爾梅里奧巡閱使的墳墓。1600年至1614年,莫雷洪是京都敎會的領導人,弗羅伊斯和奧爾甘蒂諾的稱職的接班人。流亡時期,他被認為是外國傳敎士中最熟悉日本敎會事務的專家。從1614年到他逝世期間,除了去世界周遊之外,他都在澳門為日本敎會及其殉敎者們工作。
那些年,澳門不僅是流亡的傳敎士和敎友的避難所,而且也是那些在日本工作和逝世的英雄們的象徵和希望;有時甚至是一種誘惑,例如,對本托·費爾南德斯神父就是如此。
本托是善於適應日本生活方式的傳敎士之一。這個巴爾巴人的兒子中等身材,膚色黝黑,容易被當作日本人。他工作努力,不怕地下生活的危險,飽經精神黑夜的磨難。他從自己所愛的日本中部被調到長崎,他認為很不公平。他覺得上司們不信任他。失望中他給自己的知己努諾·馬斯卡雷尼亞斯(Nuno Mascarenhas)寫信説:“我寫信給澳門的巡閲使,請他出於仁慈允許我去澳門,在那裡隱居在一個小屋裡,不見任何人,思考我的解脱,因為我已厭倦了日本……。”(19)
此信的落款日期是1622年3月4日。當然,本托沒有返回澳門,而是繼續工作了十一年,直至1633年在長崎光榮殉敎。
日本殉敎者在聖保祿學院的聖骨
聖保祿學院對於日本敎會,像杜埃學院對於當時的英國敎會一樣,是使徒和殉敎者的溫床。那些在日本犧牲者的聖骨不斷地被送到澳門保存。
在長崎殉道者博物館,有一份莫雷洪神父寫的文件,并蓋有聖保祿學院院長的印章。文件的日期是1630年10月5日,這是莫雷洪把保羅·三木(Paul Miki)、約翰·后藤(John of Goto)和詹姆斯·幾齋(James Kisai)這三位耶穌會聖徒的一些聖骨送往菲律賓耶穌會的證明。在文件的下端,馬尼拉大主敎胡安·德布埃拉斯神父(Juan de Bueras)於1632年7月3日證明那些聖骨已經收到。
三位聖徒的遺骨可能是由魯伊·門德斯·德菲格雷多的“聖安東尼奧”號船帶到澳門的。從這艘停泊在長崎港中心的船上,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二十六位聖徒殉敎的所有畫面。1597年秋天“聖安東尼奧”號返回澳門,船上的旅客中有日本主敎佩德羅·馬丁斯和一些被逐出日本的方濟各會士。給二十六位殉敎者賜福時(1627),從澳門向羅馬、里斯本和馬尼拉送去一些聖骨,但大部份仍留在聖保祿敎堂。1614年被驅逐的耶穌會士抵達澳門時,他們在塞朗·達庫尼亞的船上帶來另一批寶物:到那時為止在日本各地被殺害的其他殉敎者的聖骨。那些殉敎者不是耶穌會士,但他們都是日本敎會的兒子,都用自己的鮮血證明了自己所接受的信仰,他們中的大部份人是來自澳門的傳敎士。由於有馬的敎會運作到1612年,長崎的敎會運作到1614年,所以在其它地區遇難的殉敎者的聖骨被安放在有馬和長崎,從1612年起,所有的聖骨被安放在“萬聖之家”花園內建築的一座小敎堂裡。不久,這座小敎堂就成為朝聖中心。傳敎士們把聖骨從那裡帶到澳門,同其它聖骨一起安放在聖方濟各·沙勿略小敎堂的祭壇上。
殉敎者們來自豐后(1587)、八代(1603-1609)、萩和山口(1605);加斯帕爾·左馬(Gaspar Sama)及全家來自平戶的生月(1609),還有許多殉敎者來自有馬(1612-1613)。
幾年後,廣島殉敎者弗朗西斯科·外山(Francisco Toyama)、葡萄牙商人多明戈斯·若熱(Domingos Jorge)和小倉的殉道者迪奧戈·加賀山勇人(Diogo Kagayama Hayato)的聖骨也運來安放在一起。所有這些聖骨都在1742年被蒙但也(José Montanha)神父列入清單,1806年,澳門主敎盧斯·沙辛(Luz Chacim)為這些聖骨做了證明。1835年聖保祿學院被大火燒燬,從火中搶救出來的聖骨被轉往多個地方,最後安放在現在的路環聖方濟各聖堂。
三年前,為了盡可能鑒別出那些聖骨,我同長崎大學的松下敬之(Takayuki Matsushita)敎授從長崎趕到澳門。沙辛主敎寫的清單,有關日本迫害敎會的文件(其中許多是在塞爾克拉主敎領導下寫的)和醫學鑒定提供的年代,幫助我們鑒別出一些頭骨。對於我來説,在路環相伴日本敎會英雄們的聖骨渡過的時光是一次寶貴的經歷。我仿佛看到馬格達萊娜修女(Magdalena)和迭戈·林田(Diego Hayashida)兄弟在我的前面走向有馬河畔的刑場,聽到他們的母親瑪爾塔·林田(Marta Hayashida)鼓勵他們的呼聲:“我的孩子們,抬起眼睛看那藍天! ”我深深地感謝澳門,她至今仍滿懷愛心保存著那些寶物。
但是,大多數殉道甚麼都未留下。由於殘酷的迫害昇級,殉敎者們的屍體被燒為灰燼,拋入大海。最後一位使者胡利安·中浦就受到這種遭遇,長崎灣就是他美麗的墳墓。
然而,有些事情迫害者阻止不了。澳門-長崎貿易一直持續到1639年,每年葡萄牙商船都把當年殉敎者的消息帶到澳門。如果殉敎者在這個城市很有名,澳門就舉行隆重的儀式悼念。鐘聲四處迴蕩,有時(例如塞瓦斯蒂安·維埃拉神父殉敎的消息傳到澳門後)甚至舉行鬥牛。(20)
先由莫雷洪神父,後由安東尼奧·卡爾丁(António Cardim)神父推動的新活動,從那時開始:請敎會就部份殉敎者的賜福問題進行審理。例如,我們在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就可以看到1633年和1634年那些殉敎者的審理情況。這次審理非常重要,不僅在於它關係到那些殉敎者,而且因為它反映出澳門和長崎的關係,在最後幾年許多有趣的事情。
在長崎,當德川家光將軍命令填海造出島(Dejima)時(1634),葡萄牙人在長崎的生活日益艱難。所有生活在長崎的葡人被迫搬入一個街區,晚上關閉街門。從那時起,大量葡人開始移居澳門。1633年11月和1634年,很多出生在長崎的年輕葡人或在長崎生活過多年的葡人乘洛波·薩爾門托·德卡瓦略的船來到澳門。他們能講流利的日語,并親眼目睹了殉道者們遭受拷打和殺害的情景。他們在審理時出庭作證,其證詞為我們保留了殉道者們最後時刻的形象。由於這些審理,一些殉道者被賜了福,我們希望其他人在不久的將來也能被賜福。
長崎的仁慈公會
在路環敎堂供奉的聖骨清單中,包括哈科韋·小西忠二郎的名字。這位於1627年流亡澳門的武士,身著仁慈公會的會服,安息在聖保祿敎堂。這件會服是團結長崎和澳門居民友好精神的象徵,在“長崎文化”形成中具有持久的影響力。
澳門的仁慈堂是賈耐勞主敎在1569年創建的。仁慈公會由偉大的傳敎士路易斯·阿爾梅達傳入日本。阿爾梅達30歲前是商人和外科醫生,後來許多年是耶穌會敎友,晚年成為敎士。1557年他在府內(今大分市)建立了一所小醫院。這所醫院是按照仁慈堂的規章組織起來的。日本人民承認阿爾梅達的這一貢獻,現在大分市最好的醫院之一叫“路易斯·德阿爾梅達醫院”。
仁慈堂又從府內發展到界市(Sakai),當地富商迪奧戈·日比谷梁啟(Diogo Hibiya Ryokei)資助建立了另一所小醫院。界市的儒斯蒂諾·卡薩里亞(Justino Kasariya)一家搬到新建的長崎市,并於1583年在長崎創建了仁慈公會。這是一個與長崎第一個五十年有關的美麗故事。長崎居民和來自澳門的葡萄牙人為公會的工作一起合作。長崎學院的耶穌會士是隨軍敎士。規章同澳門的一樣,長崎的會員從澳門定購會服。主會堂位於科森(Kozen)大街,石階從那裡通向中島河(Nakashima),我們稱之為“仁慈石階”。現在,那裡有一座小紀念碑紀念這一歷史。(21)
1591年,莫爾·羅克·德梅洛(Mor Roque de Melo)船長自己出資為痳瘋病人建立了一所醫院。這所醫院名為“聖拉匝祿·比奧因”,位於長崎郊區的宇和町(Uwa-machi)。他把醫院委托給仁慈堂,後者管理醫院至1614年。那年,聖拉匝祿醫院被毀,在其原址上興建了寶蓮寺(Honren-ji)。當所有的敎堂和基督敎機構被統治者長谷川(Hasegawa Sahyoe)摧毀時,祇有仁慈堂的主會堂和其敎堂繼續保留,1619年才被拆毀。但即使在那以後,仁慈堂的工作仍在繼續。
普遍禁敎之前,仁慈堂已經在京都和有馬站穩腳跟。在京都的仁慈堂,我們有一份重要文件,上面蓋有仁慈公會的印章,簽有不少成員的名字(1617)。其中一人叫若奧·橋木(João Hashimoto Tahyoe)。在有馬市(今北有馬鎮),仁慈公會在城南有一座小敎堂,靠近穿過馬河的大道。這在1590年有關加斯帕爾·科埃略神父葬禮的敘述中十分清楚。科埃略逝世於上總,但他的遺體被埋葬在學院敎堂附近,有馬家族城堡的腳下。他們用船將遺體從口之津運走,在仁慈公會的敎堂渡過一夜,次日遊行隊伍從那裡走向學院的敎堂。許多仁慈公會的會員從長崎趕來參加儀式;他們都穿著會服,有些人甚至按照日本的習慣,剃光頭發表示自己的悲痛。(22)
然而,那段歷史最美麗的一頁可能是由長崎仁慈公會的最後一位“供應商”米蓋爾·藥屋(Miguel Kusuriya)寫成的。米蓋爾住在科森町(Kozen-machi),早在1618年就出現在長崎的歷史書裡,當時他去探望關押在十字街監獄的耶穌會敎友萊昂納多。那個地方現在被市政廳的建築佔用。在監獄裡寫的一封信中,萊昂納多感謝米蓋爾去探望他,并給他帶去衣服和其它禮物。(23)
從那天起,米蓋爾成為長崎的“樂善好施者”,他冒著生命危險,每天幫助那些處於困苦之中的人們,直到1633年7月28日殉難。那年正是長崎仁慈公會創建50週年。米蓋爾的主要工作是在葡萄牙和日本商人中間收集善款,用這些錢幫助殉敎者的子女和遺孀,以及其他窮人。這些都寫在他的死刑判決書上,在他從監獄走向西阪山時當面做了宣佈。米蓋爾高唱著<萬眾讚美基督>的聖歌,踏著那條老路的石階拾級而上,最後被活活燒死。
所有這些細節都是從他朋友們的證詞中摘錄的,他的朋友們在澳門進行的審理中出庭作證,其中也有曾幫助過他的葡萄牙人。(24)
從賈耐勞主敎到米蓋爾,經過路易斯·德阿爾梅達、儒斯蒂諾·卡薩里亞和羅克·德海洛的努力和生命的考驗,依靠澳門聖保祿學院和長崎聖保祿學院所有傳敎士的幫助,以及商船上的人們和長崎市民的合作,日本敎會和澳門敎會團結在同一種友愛的傳統之上。長崎的流亡者身著仁慈公會的會服安葬在澳門聖保祿敎堂是適宜的。
楊平譯

聖餅盒(鑲貝漆器9×11cm) 日本神奈川Tokei敎堂藏

聖方濟各·沙勿略像(紙品彩畫6×49cm)
日本長崎南蠻藝術館藏
【註】
(1)佩德羅·莫雷洪:《1627年的日本殉道者名單》,墨西哥,1631年,羅馬耶穌會檔案,Jap Sin 63,249卷。
(2)祇有部份書目:《16世紀歐洲有關日本第一個赴歐使團的出版物》,阿德里亞娜·博斯卡洛(Adriana Boscaro)著,萊頓,1973年。《Anno 1585,Milano Inconta il Gioppone》,米蘭商會,米蘭,1990年。《Shin Shiryo,Tensho Shonen Shisetsu》,結城梁吾(Yuuki Ryoogo)著,東京,1990年;《Tensho Shonen Shisetsu,Shiryo to Kenkyu》,長崎,1992年。
(3)耶穌會士洛倫佐·梅希亞,澳門,1588年11月22日,Jap Sin 11 I,頁18。其中有大量關於聖保祿學院歷史的資料。
(4)同上,1589年6月8日,Jap Sin 11 I,頁73。
同上,1589年10月8日,Jap Sin 11 II,頁181。
(6)結城梁吾:《Tensho Shonen Shisetsu,Shiryo to Kenkyu》,頁106-111。
(7)梅希亞,1589年1月8日,Jap Sin 11 I,頁46。
(8)同上,1589年10月8日,Jap Sin 11 II,頁181。
(9)米蓋爾·千千石:澳門,1589年10月2日,Jap Sin 11 Ⅱ,頁173。
(10)阿布蘭謝斯·平托、岡本吉友、亨利·伯納德:《路易斯·弗羅伊斯,1582-1585年間日本在歐洲的第一位使節,東京索非亞大學,1942年。
(11)曼修·依藤:天草,1592年4月14日,Jap Sin 11 II,290卷。
(12)耶穌會士佩德羅·拉蒙,1592年4月4日,Jap Sin 11 II,322-323卷。<物有其名,上帝亦然>,阿爾瓦雷斯-塔拉德里斯(Alvarez-Taladriz)著,大阪外國語大學學報,1977。“Shiryo to Kenkyu”,結城梁吾著,頁198。
(13)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耶穌會使團22,第三冊5,頁366-385。
(14)Jap Sin 14 IIA,頁229-30。耶穌會士迭戈·結成:《九州大名的四位使者返日之後》,澳門文化司署,1990年。
(15)關於馬丁·原合作編寫若奧·羅德里格斯的“歷史”,參閱若奧·羅德里格斯神父所著《日本敎會主敎未公佈過的歷史》,大發現歷史國際大會,紀要,第五卷第一部,里斯本,1961年。
(16)迭戈·帕切科:“Suzuta no Shujin”(卡洛·斯皮諾拉寫自獄中的信件),長崎,1967年。
(17)羅馬耶穌會檔案,Jap Sin 18 II,220-221卷,“紀念1632年9月至1633年10月22日殉敎的聖徒”。
(18)海外歷史檔案,里斯本,手抄古籍1659:<關於埋葬在該敎堂的本會會員>。
(19)本托·費爾南德斯,1622年3月4日,Jap Sin 35,頁165-166。
(20)曼努埃爾·達卡馬拉·德諾羅尼亞,澳門,1635年6月5日,Jap Sin 29 I,頁123-124。結城梁吾:<出島的誕生>,《Nagasaki Danso》第70期,長崎,1985。
(21)迭戈·帕切科:<基督世紀的長崎敎會>,《西班牙東方學者協會會刊》,馬德里,1977年,頁60-62。
(22)路易斯·弗羅伊斯:《日本歷史》,第五卷,頁218。
(23)萊昂納多·木村,長崎,1619年10月25日,Jap Sin 34 I,178-179卷。
(24)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耶穌會使團22,第三冊4,ff291、299v、317……
*Diego Yuuki,1922年出生於西班牙塞維利亞,耶穌會士,1948年赴日本,後進哥倫比亞波哥大Javeriana大學修神學,1962年起任長崎殉道者博物館館長,1978年加入日本國籍。--本文係1994年11月28日-12月1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週年紀念(1594-1994)“宗敎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