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意即:無論在歷史、地理、藝術、哲學、文學及風俗習慣等方面“有關中國之研究”。
“漢學家”即“漢學專家”。
《中國文化評論》一書(1912年,澳門莫拉伊斯·帕雅書局出版)的序言足以證明庇山耶對中國文化具有深厚的造詣。詩人抨擊了腐敗、淫逸、罪惡及懲罰,文字如同鐺鐺巨鑼,擲地有聲,毫不留情。
庇山耶諳熟中國歷史,有史實可以加以佐證。應莫拉伊斯總督之邀,庇山耶曾在商業學校任教。該校於1903年10月7日併入澳門中學。這意味著對其勝任此職能力的承認。
正因為他精通中國歷史,所以才在上述序言中承認,中華民國的成立為中國人民開闢了新的天地,將他們從幾千年的一片昏夢中喚醒,令民眾開始憎恨往昔,並使其在不遠的將來,經過嚴重的危機後,像日本一樣,把中國變成強國,為削弱歐洲的經濟利益及政治特權,建立亞洲的霸權而做出努力。庇山耶在四分之三世紀前做出的預見,今天正在成為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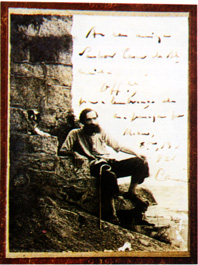 庇山耶在澳門立頓山莊(1921年)
庇山耶在澳門立頓山莊(1921年)
至於他對中國藝術的瞭解,祇要看看1915年2月7日出版的《進步月刊》上的一則邀請便可想而知的了。請柬如下:
澳門總督及其夫人唐娜·貝爾塔·德·吉斯特羅·馬亞十分榮幸地邀請諸位朋友於今日下午16時前往澳督府參觀庇山耶博士收藏的中國文物珍品展覽。
這位不得志的總督卡洛斯·馬亞是位情趣高雅、文化博深的人士。如果這些展品毫無價值的話,他是絕對不會舉行這一展覽的。
庇山耶關於“中國美學”的演講是無懈可擊的。他在這方面的高深知識使所有的嫉能妒賢者緘口不言。
賽巴斯蒂昂·達·科斯達在《新原野》1926年4月29日早上聲稱庇山耶並非藝術品的“出色鑒賞家”,因此,在其購入藝術品時,常為人所“騙”,還説祇要同庇山耶略談一席“中國東西”便可知其這方面的知識貧乏,“根本不能與文第士的淵博知識及若熱的鑒賞力同日而語”。
也許庇山耶的確不能嚴格地確定一個陶罐、一件青銅藝術品或一副蘇六朋畫是否屬於出讓者所聲稱的那個年代。有史以來,許多為世人所珍愛的古老藝術品有許多真假難辨的膺品。有時這些仿製品不是為了假冒,而是出於對這作品藝術價值的高度欣賞而為之。庇山耶所關心的是色彩的華美、外型及裝飾。他是以藝術家的眼光而不是以收藏家的眼光去欣賞這些珍品的和諧整體的。
阿爾貝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於1912年夏末在澳門拜訪了庇山耶。在記敍這次會晤的一篇短文(載里斯本1942年第二期《大西洋》雜誌)中,他生動地向我們記述了詩人如何為其講解他家裡擺滿了廳堂走廊的數不勝數的藝術珍品,如瓷器、玉器、瑪瑙件、大理石製品,銀器及其它豐富藏品的精華所在,美中不足及其象徵意義。阿爾貝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認為這部份藏品在葡萄牙可以説是絕無僅有的。庇山耶親手熱情編寫的<庇山耶捐贈國家藝術博物館·中國藝術藏品目錄>(這些藝術藏品曾經當時最負盛名的一位中國文物專家的仔細鑒定)可使我們對庇山耶贈送“綠窗博物館”(譯者注:國立藝術博物館位於“綠窗街”,故有“綠窗博物館”之稱。)的文物略見一斑。該博物館的藝術負責人拒絕了這些贈品,將其“發配”到了科英布拉。現存於一處根本沒有展覽和保存條件的地方。
 庇山耶的澳門夫人銀鷹女士
取自《葡萄牙雜誌》(Revista de Portugal),1940年11月
庇山耶的澳門夫人銀鷹女士
取自《葡萄牙雜誌》(Revista de Portugal),1940年11月
 庇山耶及其後人合葬墓碑(澳門舊西洋墳場)
庇山耶及其後人合葬墓碑(澳門舊西洋墳場)
無可置疑,庇山耶曾攻讀中國文學及語言。1915年3月13日庇山耶曾在“軍事俱樂部”做過以<中國文學>為題的講演。在該文中,他簡明扼要地介紹了中國詩歌的特點和譯事之難。他認為中國詩歌的翻譯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但庇山耶是否具有漢語口頭及書面語的知識來從事從漢語到葡萄牙語的翻譯?
説庇山耶講的漢語華人根本聽不懂者不乏其人,重復此論者亦不乏其人。口出此言者實乃不服庇山耶過人的聰慧,更有甚者,否認庇山耶是詩人。僅以文第士為例。此人乃一失意詩人,著有《道家哲學選析》一書。在此書中,對已成古人的庇山耶竭盡抨擊之能事……
初抵澳門,庇山耶便考慮到不管為誰充當律師,都必須學習廣東話。所有在澳門定居的宗主國人氏在同華人的日常接觸中都學會了這種語言。
庇山耶在開業時,聘請了一位翻譯。此人同時為其兜攬顧客。此乃當地的習俗。此外還請了一華籍文人教他中文。他祇掌握了三千五百個左右的漢字,因為鴉片給他的快樂遠遠勝過死記這些“象形字”所需的令人精疲力盡的功夫。然而,他仍然繼續跟他的情婦學習漢語。他們生有一子。他家中前前後後的女人,一些是他情婦的親戚,另外一些是女傭。從他們身上他學到了不少漢語,之後又求學於若熱。
安東尼奧·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永遠不會忘記1916年3月19日庇山耶最後一次返回澳門的情形。在碼頭上,庇山耶告別了前來送行的友人,混進了中國旅客人群中,華人見這一滿面鬍鬚的歐洲人操著一口當地話,吃驚不淺(見1967年9月7日《國民日報》)。
阿爾貝爾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在上述訪問中寫道:“庇山耶在華人中是位倍受尊敬的知名人物,在街頭巷尾,華人總是圍住他,用那古老的方言同其交流……”這一情景乃詩人的朋友親眼所見。他們二人曾結伴暢遊澳門關閘,賈梅士洞、南灣、街市、番攤、方言戲院、華人或澳門人的住宅區,無一遺漏……”
賽巴斯蒂昂·達·科斯達在上述發表於1926年4月29日號《新原野》上的文章記述説,在其家為其備鴉片時,“庇山耶一直與其情人熱烈地用中文交談”。
在華人環境中生活多年後,加上華人文士的補習,同四鄰及古董商人的經常接觸,無可置疑。庇山耶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可能有時發音不甚準、詞匯有限,後來在“老友及恩師”若熱的補習下,大有長進。
庇山耶有翻譯中國文學及哲學作品的能力嗎?
就其本人的漢語水平而論,即便在字典的幫助下也是不可能的。其理由庇山耶本人已有談及。
 庇山耶在澳門與一位中國文人磋商譯事
根據1967年9月7日澳門《國民日報》(Diário Popular)所載Dr. António Osório de Castro的照片複製
庇山耶在澳門與一位中國文人磋商譯事
根據1967年9月7日澳門《國民日報》(Diário Popular)所載Dr. António Osório de Castro的照片複製
在上述庇山耶本人編寫的有關中國文學的略述中他談到,在中國,真正的全國性語言,維繫中華民族團結的主要力量是書面語而非口語。 “無論是再具體或再抽象的概念,中國人都有其相應的書面表達方式。每個詞有不同的聲調,每一聲調表達一個不同的意思。鑒於漢字象形的特點,光靠耳聽不能確定其書寫形式,祇有用眼閲讀才能看懂。
每個詞有一表意成份。“……人或星辰,動物或植物,茅屋,車輛等等……”
現在我們僅以“明”字為例。“明”意即光芒或光亮。該字由兩個成份構成,日+月=明。
除了上述困難外,還有其它一些難點,如:日常用語中的書面體及口語體同高雅語中的書面體及口語體有差別:高雅語常使用比喻、神話及歷史典故;在講話時,涉及自己時還要用謙詞,“稱對方則要使用最好的形容詞。”(見莫拉伊斯·帕雅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評論》頁50。)絕不可講“皇后死了”,應説“皇后殂落”;問某人年齡時應該問“今年貴庚? ”或“青春幾何”;如問有幾個孩子得到的答複是,“五個豚兒”等等。在<哀歌>的序中,庇山耶明確地闡述了譯事之難,開門見山地指出:“從句子上來講,(即便理解了每個單詞所表達的準確意義)因沒有限定句法結構的語法規則,每個句子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釋。”翻譯漢語文雅體的書面語還要難上加難。
儘管如此,庇山耶還是從漢語譯成了葡萄牙語一些東西,至少有三封信、兩篇短文及八首詩。上述三封信是一案件卷宗的一部份,1910年為被海盜掠去的兒童家長的代理人孔斯坦西奧·若澤·達·席爾瓦律師的要求而譯。那些孩子們被海盜從石岐的一座村落俘去,帶至路環島。他們要求支付三萬五千澳門圓的贖金,否則將處死這些可憐的孩子並洗劫他們所住的三個村莊。這三封信迫使澳門政府發兵直搗匪巢,解救了所有人質。(請見1960年7月10日號《澳門消息報》)
兩篇短文中具有道家思想的<張果老>首次發表於露伊·桑特爾沫著《中國--一個充滿痛苦的國度》一書(作者真名為布利托·德·納西門托),時任司法部駐澳門代表。這一譯文本收入1949年編輯的一集子中。那集子名稱就欠妥。《中國(論文及譯文)庇山耶著》許多人認為這是詩人的“遺作”,實則不然,詩人與此書的編輯毫不相干。令人遺憾的是在庇山耶誕辰百週年紀念章上刻上了<滴漏>和<中國>,似乎這兩部都是其作品。
<秋聲賦>發表於1918年1月13號的《亞特蘭大》雜誌上。中國詩歌祇譯了<輓歌>。
在莫拉伊斯·帕雅書局出版的該書的頁53上,庇山耶在譯<輓歌>的前兩年,就對華人習文之艱難寄予了莫大關注。華人必須逐字逐字地記住至少五千個不同單詞的寫法才能看懂和書寫家書。在此順便提一下,沒有五千左右的詞匯是不可能閲讀報紙的。
在<輓歌>的序中,祇有3,500個詞匯量的庇山耶解釋了他是如何從事詩歌翻譯的。在一華人文士的指導下,他盡量逐字翻譯每首詩。由那人用廣東話唸給他聽,然後由他用拉丁字母拼寫,從全部樂感中抽出其主題及象徵意義,即“可譯部份--名詞成份或想象部份”,從其特有的詩歌格律和樂感將這些漢詩譯成了無韻詩。

漢學家若熱肖像
原作為*Fausto Sampaio的碳筆畫此圖係用中國水墨(毛筆)在已損的舊稿上重繪而成
在同序中庇山耶聲明,他曾將譯文交給“摯友,我所敬重的大師若澤·維森特·若熱先生審閲,他為我的論文進行了數處修改,使之更接近於原文。他還做了大部份增釋。若無這些增釋,即便譯文再準確無誤,也是難以全面理解的。他還將文中斜體字的廣東方言發音譯成了北京話。”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若熱對譯文的潤色是必不可缺的,倘若無庇山耶賦與譯文的詩魂,譯詩肯定平淡無奇。
至於三封信件和翻譯問題,鑒於信的作者屬於較低的社會階層,不可能使用很文雅的文體,自然庇山耶的中文水平足以將其譯為葡萄牙語,儘管可能有人予以協助,也許是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師,即前面已涉及的那位華人文士。
至於散文的翻譯,可以推測,他得到“恩師”的指教才得以完成譯文,因為這些文字太難譯。
的確,庇山耶是若熱家中的常客,與大家親密無間,如同家人。他常在那著名漢學家藏書豐富的辦公室中渡過漫長時光,潛心攻讀漢語。一個是老師,一個是學生。
若熱仍然在世的後人中,祇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孫女可以作為庇山耶和若熱共習漢語的見證人。若熱的小女若澤·瑪利婭還記得常常在父親家中見到庇山耶。庇山耶常在他家中留用午餐,其餘都不記得了,因為當時她仍很年幼。一見到庇山耶那副怪模樣,她就嚇得鑽到床底下去。恩莉克塔是庇山耶在中學任教時的學生。她對庇山耶與其父的交往、共進的便餐、有關中國的交談尤其是涉及中國畫及瓷器的交談,仍記憶猶新(若熱擁有十萬件中國藝術藏品……)。正因為恩莉克塔的緣故,我才萌發了對庇山耶的興趣。她吟誦庇山耶的許多詩句,是她為我研究庇山耶的作品及其生平提供了許多素材。若熱的孫女,瑪利婭·杜·塞烏著有一份十分出色的關於庇山耶的文章(載於《講座》雜誌1967年第30期)也生動地追述了這段往事。
從1935年起,我們曾同若熱先生朝夕相處到1948年11月22日他在里斯本與世長辭為止。在這段共同生活時期聽其講述的往事足以使我們做出如下結論:庇山耶對漢語的整體結構有高深的理論知識,相當嫻熟地掌握了一般性口語,至於書面體,他學會了相當一部份的漢字,但不足以單獨地在不依靠他人潤色的狀況下從事漢語文言的翻譯工作。<輓歌>的翻譯可為一例。其它散文體的譯文和一些不下落不明的譯文均在此例。
這一結論不適用於《國文教科書》。這是一冊學生用書。其第三冊上與若熱一同署名的還有庇山耶。若熱曾任華務廳長,上海領事館副領事銜翻譯官,葡萄牙駐清朝北京公使館秘書翻譯官,“其辦事能力頗受欣賞,多次獲得嘉獎”(見1968年11月10日若澤·德·卡爾瓦略·雷革在《澳門消息報》上發表的文章)而被選為代表葡萄牙參加1909年光緒皇帝葬禮的外交官做秘書。他翻譯並注釋了供澳門學校教授漢語用的《新課本》。既然他已翻譯了該書的前二冊、自然不需庇山耶協助去完成第三冊的翻譯。

庇山耶像(油畫)
Pedro Barreiros* 作
*Pedro Barreiros,葡萄牙著名畫家,係著名漢學若熱(Jose Vicente Jorge)的孫子。
安東尼奧·迪亞斯·米格爾在其關於庇山耶的別樹一格的文章中,以“内行”人士提供的可靠情況為依據斷言説:
<輓歌>的譯文猶如孔雀羽毛。這一説法是不公正的,完全出自誹謗庇山耶者之口。一些嫉能妒賢者、不得志的詩人曾否認庇山耶作為葡萄牙文學史上真正而唯一象徵主義詩人的地位。可以説,庇山耶乃歐洲文壇上最偉大的象徵主義作家之一,此乃芭芭拉·斯巴齊之語(請見《庇山耶作品中的象徵主義》,簡明文本,1982,阿馬多拉出版)。
的確,<輓歌>的葡譯文是在上述情況下完成的,這一點已為若澤的話所證實。
庇山耶在《國文教科書》中的作用僅局限於協助若熱進行編輯。若熱邊譯邊聽庇山耶講解他不認識的生詞,從句子中找出一些有意義的話,例如:鵲噪吉,鴉聒凶。
實際上,若熱利用此書來擴大庇山耶的漢語知識。上課時,庇山耶專心聽講,收獲甚大。因此,老師出於友誼將其列為作者之一。據若熱講,這對詩人來講是則莫大的榮譽。瑪利婭·若澤·德·蘭開德著(1984年里斯本國立出版社/鑄幣局出版)的那本珍貴的集子頁82中收錄的庇山耶給唐娜·安娜·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的獻辭中,詩人稱這一教科書的翻譯為“一種初步的賞試。從書的特點來講,譯得更好,方能為古老的祖國爭光。”太欠謙虛了,似乎他真是作者之一的口吻,這完全是與其有些自我崇拜的做法相吻合。1954年10月20日,阿爾曼多·文杜拉向我們重複了他在1952年8月2日《世紀畫報》上寫過的一段話:這些“衝勁”使其沿著兵器庫街和金街夜遊,返回旅館時“停下腳步”吟頌他自己的詩句。那朗誦聲如同大提琴的回聲在凌晨的寧靜中回蕩……然而他邊唱邊問:“今後賈梅士何在? 安特羅何在? ”
庇山耶祇不過是想“騙騙”他的女友,使其相信他的中文水平可以與他人共同撰寫著作。
按照原稿全文發表<輓歌>並由北京外國語大學葡萄牙語教研室金國平先生增注,的確是件值得贊揚的工作。本人榮幸地撰此小文,以饗讀者。
誠然,這充滿了庇山耶詩歌魅力的譯文祇能為精通中葡兩種文字的人對照與初次發表時一模一樣的雙語本來加以欣賞。
如果庇山耶認為應該發表中葡雙語版,保留日期地點及獻辭的話,那麼,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在《發現》雜誌中刊登的面目全非的《輓歌》則是件大錯特錯的事情。這一版本未收著名的序,未收注釋,甚至連內文都未注明,實令所有文學道德標準之法典所不容。
安東尼奧·瓦爾德瑪爾(在載於1967年9月7日《消息日報》上的一則文章中)猛烈抨擊了這種不僅對<輓歌>而且對<滴漏>一而再再而三的刪節。在1982年9月30日登在《消息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自詡為庇山耶權威”,宛如庇山耶的法定繼承人一般。同樣,我們所尊敬的一位友人彼得·達·席爾維拉先生--庇山耶作品最熱誠的欣賞者之一也譴責了這種“節略”(參見科英布拉出版1969年4月號《頂點》雜誌)。阿爾弗雷得·馬爾卡利得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載於《人》雜誌11-12期合刊)揭露並鞭笞了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的毫無道理的“疏忽”。
至於那些被“刪去”的<獻辭>祇有在1969年版的《滴漏》一書頁537-538之中收了進去。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的“解釋”不足為憑。説什麼,獻辭中涉及的人,除了慕拉士以外,“沒有任何人做過任何幫助詩人實現其計劃的工作或有助於廣泛出版其作品的事情。此乃其生命最後時期的一大責任”。這種説法是不公正的。如果庇山耶真想發表作品的話,出版費、印刷商都不成問題。
從另一方面來講,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的這一“解釋”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僅從獻詞中提到的卡洛斯·阿馬羅為例,在那書數處尤其是在頁22上對詩人的這位友人大加贊揚。
對中文的節略也毫無道理。可以用影印版的辦法來解決我們的印刷所中沒有中文模子和排字工的問題。
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最關注的是搶先發表庇山耶的詩。實際上,大部份詩在到達他手上之前,都已刊行過了……
庇山耶及其優美的詩歌應被置於最重要的地位,這遠遠重要於由個人的虛榮而引起的毫無意義的爭論。這一點完全適用於藝術家的作品,其天才可以使其“擺脱消亡這一法則”。
但一切迄今為止已刊行的有關庇山耶作品的研究及欣賞的嚴肅的文章都是值得稱道的,都必須永遠為人們所掛懐。在本文結束之前,我們必須公正地承認,若昂·德·卡斯特羅·奧索里奧儘管有其欠缺之處,但為瞭解和傳播庇山耶的作品及其生平,以及喚起人們對這位偉大詩人的興趣方面做出了鉅大的貢獻。
(1966年11月1日於里斯本)
謹向為我們提供《進步》週刊的單尼路先生及熱情協助我們編輯庇山耶《輓歌》的國立出版局瑪爾格麗塔·聖托斯女士致以深沉的謝意。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感謝啟發我們進行這一工作的國立圖書館彼得·達·席爾維拉先生及在澳門文化學會出版部“幕後”辛勤工作的魏祖澤先生。
譯者金國平
1989年3月29日於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