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雜誌》經過9年的努力才慢慢實現著初衷。一期又一期,我們從收集到的多種原材料中逐漸汲取養份。每一期的完成都像是一場戰鬥,幾乎是自我消耗的探險:掙扎於暗礁險灘,規避著定界極限。由於作品偶然性因素的限制,經常要原地踏步。那些慣常性的阻力總是與計劃的美好意願作對。
承蒙讀者善意而熱情的批評,令我們依然不斷進步。《文化雜誌》因此才能逐步接近著它初始設計的理想藍圖。現在,這個藍圖的地平線已出現於我們的視野中了。
這篇前言不想作辯護,不想作證明,更不想乞求仁慈。我們在任何人面前均不會這樣。這篇拙文不是暗示任何苦痛的暗影,不是顯示不滿,因我們拒絕任何供訴式的說明,拒絕主觀情緒的表露。我們在實際行動上有一種超越個人私利的設想,所有個人的苦惱都在作品更高級的營造中消解了。因此,我們的工作總是在基於為代理人、著作者和文化界人仕提供謙卑服務的天職上而進行的。
我們祇是想合情合理而迎合時宜地留下記錄,並確認我們編輯原則和一種可付諸實踐的未來趨向,念念不忘我們從一開始就釐定的永恒職責,思索實現這個職責的可行性。
這是一片澄明之地,感受著精神的靈氣。這是通向自由之地,無論那自由貨真價實抑或見仁見智,我們過去不會、將來更不會步入論爭的沙場。
然而,我們想要澄清的是,我們的宗旨從一開始就排斥那種被稱作“官僚文化”的特質。抗拒個人主義的直覺性,抗拒枯燥乏味和炫耀博學的天花亂墜,抗拒儼然而空洞的宏篇鉅製的虛假壯麗,抗拒與人類和自然的真實境況毫不沾邊的空想主義——我們是在時空的範疇裏記述著文化。我們要將自己置於一種設身處地的文化境遇之中。
我們是在東方並依賴東方的葡萄牙人,生活著,勞作著,同時夢想著“中國”。我們對未來的責任,是以我們對這塊土地和過去的根本性責任為前提的。
我們對古老的葡萄牙民族負有責任,正由於她給我們留下了海上探險生涯,結識了遠東的國度和人民。
我們對這種歷史運動之目的性的思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要像阿爾加塞爾·基比爾(Alcácer Quibir)面對黃昏的黯澹那樣宣佈:“逝去吧,但請慢慢兒來。”因為在澳門,我們體驗著被加強的因緣而認識到,我們之所以是葡萄牙人,因為我們是世界公民;我們之所以是世界公民,因為我們是葡萄牙人。
我們對偉大的盧濟塔尼亞人的祖國負有責任,這是語言上的空間,是生氣勃勃的泱泱大國的神聖園地。
我們對拉丁世界負有責任,這是葡萄牙品性包涵的“博愛之魂”的源泉,這個世界的遺產由於葡萄牙人的努力而留存至當今一代。
這表示我們對澳門開始負有責任。——澳門,這是加強認同性的小小單元,是求同存異的條件,是自主性和偉大中華的小小投影。她對中國的職責和價值將直接與她賦有的特性聯繫起來。
而面對中國,我們已在世紀之河的變遷中簽訂了一紙用血緣、精神和兄弟一般互助情誼寫就的契約。
因為這一切,並以示範的名義,我們將那些空疏的淵博爭辯擱置一邊,那些爭辯將如許動聽的“東西方關係”化為空頭言論,卻既不能界定更不能瞭解彼此所使用的“關係”一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之,在儘可能為文化交流作實際貢獻的意義上,我們通過《文化雜誌》,致力於展示20世紀末葡萄牙文化運動中中國學研究的一部份情況,並以葡萄牙民族的方式,展示其在葡萄牙國民和拉丁世界品性中的作用。
澳門,那種被確認的文化橋樑的功能,在歷史上,在履行天職的意義上,越是可以利用,越是名副其實,就越能在國際上擴展其文化服務的效能。
因此,我們將會更加致力於為每一期《文化雜誌》賦予專門的使命。本雜誌始終以葡文、中文和英文同時發行。現在,根據信息傳播、擴充和分配的原則,我們將通過“國際信息交流網絡”(Internet)加速邁向國際化的步伐。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1995年夏季,我們對文化司署在9年前開展的這一文化舉措的潛力充滿信心,並確信在未來的歲月裏,本刊將辦得更加出色。
《文化雜誌》總編輯
官龍耀 (Luís Sá Cunha) 敬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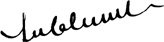
1995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