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鈴,原名馮錦釗,1915年出生於澳門,後赴上海昇學,師從戲劇家李健吾。1937年11月上海淪陷,租界淪為四面無援的“孤島”。這種“孤島”的狀態一直維持到1941年12月,因此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這段時間,也被稱為上海的 “孤島時期”。雖說“孤島”,當時上海文藝界卻並不孤獨,一群以戲劇家和雜文家為主的文藝界人士仍在租界進行文學活動,聲援抗戰,如唐弢、李健吾、柯靈、歐陽予倩、王統照等。劉以鬯、黃裳、華鈴等人也冒起於孤島時期的文壇。(1)華鈴和文友吳岩創辦《文藝》旬刊,寫詩譯詩,並自費出版《向日葵》(1938)、《玫瑰》(1938)、《牽牛花》(1939)、《滿天星》(1940)等四本詩集。(2)雖然另有兩本詩集《勿忘儂》和《曇花》未付梓,華鈴的詩名已足以蜚聲孤島,被鄭振鐸稱為“時代的號角”(3)。40年代,華鈴輾轉桂林、上海、重慶等地,40年代末落葉歸根,定居終老於出生地澳門,1992年故。(4) 中國大陸也出版了華鈴的兩本詩文集:《火花集》(1989)和《華鈴詩文集》(1994)。(5) 對於研究澳門文學的學者來說,華鈴也並非陌生的名字。1994年《澳門現代詩刊》推出華鈴專輯,收錄其十四首詩,還有李健吾、顧仲彝、程逸等人的評論或紀念文章。該期雜誌主編把華鈴譽為“本澳最早而最具代表性的詩人”。(6)

華鈴像(取自《華鈴詩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
鄭煒明在〈80年代澳門的文學作品〉(1995)將華鈴的詩集《向日葵》、《玫瑰》、《牽牛花》、《滿天星》和《火花集》列為“澳門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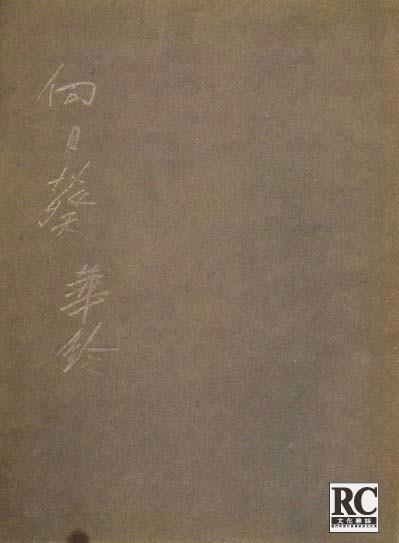
《向日葵》 封面 (1938)

《玫瑰》 封面 (1938)
詩詩集”(7)。其後鄭煒明在〈澳門中文新詩史略〉(1996) 中,則將華鈴帶入70年代的論述:“我們或可蠻有把握地說三十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壇的華鈴(馮華鈴) 大約自四十年代末起長期隱居澳門,至這個時期他又再次迸發出熱情的詩興了。”(8) 華鈴生於澳門,在澳門接受小學教育,後赴上海昇學。(9) 華鈴在上海時期主要書寫個人情事和家國情懷,的確和澳門沒有太大關係。呂志鵬在其專著《澳門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2011)中援引鄭煒明提供的史料,“將40年代華鈴的詩暫不列作澳門文學作品”(10)。呂志鵬將關於華鈴的段落放在〈50年代澳門新詩的發展〉一節,細讀幾首華鈴寫於50年代的詩。朱壽桐對華鈴的定位,和鄭煒明、呂志鵬兩位澳門本土的論者不同。他在〈略談澳門新詩研究的學術路徑〉(2012) 中直接把華鈴30、40年代的作品列入澳門文學的一部分:“澳門新詩自1930年代初現端倪,那是因為有華鈴這樣的傑出詩人以及較有影響的詩集 [⋯⋯] 可視為澳門新詩最初獲得的殊榮。”但是朱壽桐卻沒有說明論點的依據。(11) 筆者通讀幾本華鈴的詩集,祇發現詩人在30、40年代祇寫過一首關於澳門的詩:〈獻詩 —— 為新生的“藝聯”而作〉(1941)。據華鈴所註,詩人回澳參與藝聯劇團的演出,擔任幕後伴奏,有感而作,其中第三、四節寫到澳門人的淒苦的生活現實:“如今這兒死水灣頭,/腥臭的魚攤畔”,“博取粟米頭”。(12)
鄭煒明的《澳門文學史》(2012) 也沒有把華鈴納入民國時期的論述,其小結為:“大概要至民國,始漸有本土化的及土生土長的作家,形成群落,在澳門文壇落地生根,漸次開花結果。”(13) 在《澳門文學史》中改寫自〈澳門中文新詩史略〉的部分,關於華鈴的論述仍被納入70年代的段落。(14) 鄭煒明的做法和他對區域文學的觀點有一定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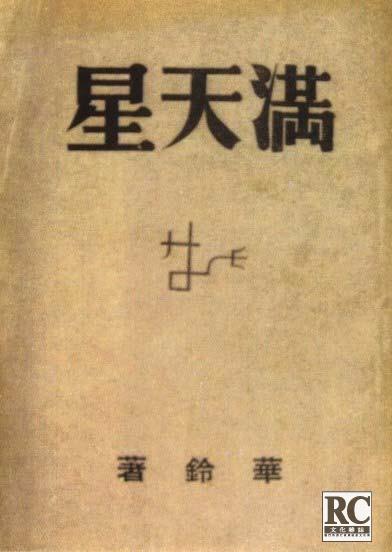
《滿天星》 封面 (1940)

《火花集》 封面 (1989)
第一,凡是內容與某區域有關的文學作品,不論其作者的種族、國籍、居住地、寫作語言和作者發表地,都可算是該區域的文學。
第二,任何作家在某區域通常居住及生活時有所感而後寫的任何作品,都可以算是該區域的文學。
第三,一個作家若其文化身份獲得判定為歸屬於某區域的,則其作品就是該區域的文學。(15)
孤島時期的華鈴,其創作與澳門無關,顯然不符合第一點。華鈴在這個時期也不在澳門通常居住及生活,也不符合第二點。至於第三點,華鈴的文化身份較為複雜,其歸屬的判定受到各方論述的影響。
華鈴活躍於孤島時期的上海,40年代末在澳門定居後寡刊,而改革開放後國內文藝和學術界人士編輯“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時,把華鈴的《火花集》收編。陳青生在其文學史學術專著《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1995) 中也把華鈴、王統照、楊剛等稱為“孤島詩人”,寫到關於華鈴的段落,對澳門隻字未提。(16) 因此,國內文藝和學術界傾向於把華鈴劃歸孤島時期的詩人。《火花集》的編者欽鴻在〈編後記〉中寫道:
作者在三四十年代的舊中國,是一個進步的詩人。定居澳門以來,還始終關注着祖國的繁榮和興盛。[⋯⋯] 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編委會把他的詩集納入計劃 [⋯⋯] 這不僅使作者本人快慰於心,廣大讀者也將欣欣然地矚目以待吧?(17)
華鈴“進步詩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從思想政治的角度來講,也比較符合國內文藝界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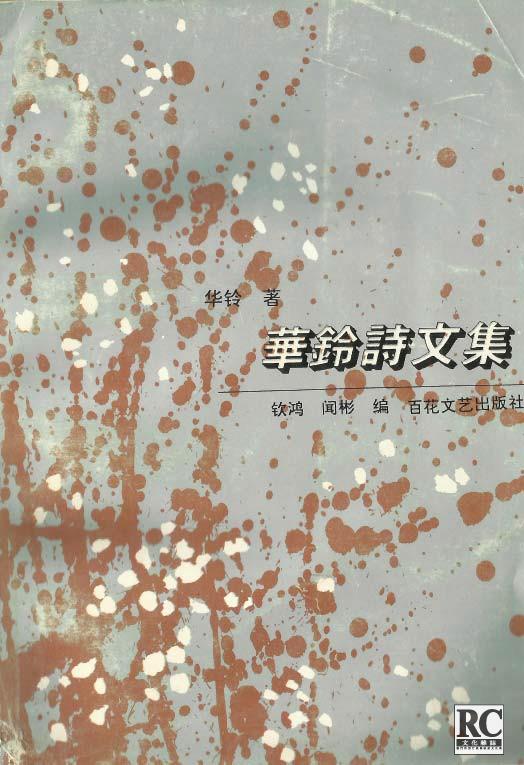
《華鈴詩文集》(1994)封面
鈴的印象。(18) 若說詩藝流派,孫玉石則將華鈴四部詩集《牽牛花》、《向日葵》、《曇花》、《勿忘儂》中的作品看成“象徵派、現代派”的作品。(19)澳門本土學者呂志鵬的觀點和孫玉石相似:“華鈴的詩活像現代派成熟的作品。”(20)呂志鵬其後分析華鈴50年代的作品,將其上接英國浪漫主義的詩論,但沒有進一步鑒別華鈴如何在其詩中磋商現代派的影響和浪漫主義的成份,尤為可惜。(21)華鈴文化身份上的轉變遠沒有詩藝評價方面的承接來得順利。對此,華鈴本人的看法非常值得關注。欽鴻在《華鈴詩文集》(1994) 的〈編後記〉中寫道:
[華鈴] 作為一個愛國詩人,他生前最大的願望,莫過於在大陸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期冀與大陸讀者心靈的交流,還是希望得到大陸文藝學術界的承認。八十年代中期,當《火花集》的出版遇到困難時,不少朋友提出改在香港出版的建議,他卻一一婉辭,堅持要在大陸出版。(22)
誠然,欽鴻的文字中原意識濃重,序跋中的個人情感和意識形態也不符合文學批評所要求的客觀立場和態度,但是這段文字在某種程度上也從側面反映了華鈴的想法。華鈴在他撰寫的自傳中,澳門祇是他出生(“生於澳”)和工作的地方(“澳門自創以錄音教學的英專”),而側重孤島時期的經驗(“詩情激昂,反映時代,反映抗戰,為孤島文學作出了貢獻”) 以及他與大陸文藝界人士之間的交往 (包括李健吾、查良釗、孫大雨、歐陽文彬等等)。(23) 似乎華鈴並不認同“澳門作家”或“澳門詩人”的文化身份。呂志鵬曾提出問題:“為何華鈴會被我們忽視?”隨後他引用程逸的文字作答:“一是近數十年之出版界不重視新詩;二是華鈴不喜鑽營,不愛自吹,祇是專心創作,近似一位隱者高士,加上長期居住澳門,與香港文化圈既無聯繫,與國內文化人之交往亦不宜渲染宣傳。”(24) 除此之外,華鈴的隱沒恐怕還和他的自我文化定位有關。綜覽澳門學術界、大陸文藝界以及華鈴自己的論述,華鈴的文化身份確實較為曖昧。無論華鈴的文化身份如何,要研究華鈴,就絕不能忽視他孤島時期的詩作。華鈴孤島時期的作品如何發展成澳門時期的作品,這個跨越詩人整個寫作生涯的問題超出了本文的範圍,需要另文再議。本文的目的在於為以後的華鈴研究打下基礎,在前人對華鈴作品的評價上略添一筆,亦為以後研究華鈴的學者提供隻言片語。
許光銳在其文章〈華鈴底道路〉(1946)中把華鈴的詩歌創作分成三個階段:一、1940年以前,以〈無情的美女〉(1938) 為代表作,大部分淺薄輕佻,賣弄小聰明,但也有〈牽牛花〉之類嚴肅的作品;二、1940-1945年,以〈給葉芝〉(1940) 為代表作,融入詩人的個性,逐漸擺脫西方詩歌在形式方面的影響;三、1946年以後,以〈可真是時候了〉(1946) 為代表作,脫離藝術,自由奔放。(25) 這種階段性的區分,雖然略顯粗淺,但是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在30和40年代,華鈴的詩歌與藝術的距離似乎越來越大。華鈴在孤島時期的創作雖然還未形成獨特穩定的風格,卻偶有上乘佳作,主題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書寫個人情事,不乏譏諷與機智,甚至具有象徵主義色彩;二、政治抒情的朗誦詩,朗朗上口,平白如話。許光銳舉〈無情的美女〉為例子,實是舉出了華鈴詩中“淺薄輕佻”的一面,該詩其中一節如是:“啊,有了;我着實不夠聰明,/我不是可以天天十片‘阿司匹林’/造成個漂亮的心臟病?/我大可以說了:‘我為你心病!’”(26) 這一節詩內容輕佻自不必說,它的半全夾雜的尾韻“明”、“林”、“病”、“病”更是典型逗趣打油詩為韻而韻的惡趣,毫無可取之處。但是,華鈴書寫個人情事的詩也不乏佳作,如〈愛情像一條絲棉被〉(1939):
愛情像一條絲棉被。
輕輕地把你裹着時,
是溫,
是柔。
(天啊!)
你偏覺:
多少還有點兒寒栗。
你說道:
不夠不夠,還差得遠!
你鑽,你捲,你捲,你鑽;
喜孜孜地,不斷自纏;
轉來,
轉去。
(蛹成)
你樂了:
稱心滿意,開始尋夢。
是噩夢?!
滿頭、滿身、滿被,大汗。
你賴:要的,原是輕快。
你着涼、感冒,發高燒。
外感
傳裡。
(妙哉)
你得了:
一個漂亮的心臟病。
大夫說:
你吃多了,阿司匹林。
詩人用第一句“愛情像一條絲棉被”帶出貫穿整首詩的比喻,即以“棉被”喻“愛情”。如果一個比喻統攝一首詩,同時又是這首詩內容和形式的核心,在英文詩學和修辭學上被稱為“conceit”,通常譯作“奇喻”或“巧喻”。(27)詩行長短相宜,在視覺上營造人與絲棉被纏結的形象,整首詩中間的擴喻“蛹成”一語中的,可謂點睛之筆。整首詩短詩行居多,祇有二三字;較長詩行中也不超過八個字,除了第一行是一個完整的句子之外,其餘較長的詩行也是由片語組成,整首詩讀起來有焦急跳躍的節奏,一如詩人動情之下的心跳,呼應詩情。〈愛情像一條絲棉被〉到了第三節,跳躍的節奏到達高潮,結尾則顯露詩人的機智(wit)。前兩節讓詩人心跳加快、心緒不寧的愛情,不過是一種由藥物阿司匹林引起的生理反應。詩人的機智,將整首詩逆轉,變成一首諷刺愛情的詩,突出詩人在整首詩的節奏和謀篇佈局上所花的心思,遠非許光銳所說的“淺薄輕佻”之作。
第二節的上半段有性的暗示, “ 鑽” 、“捲”、“纏”、“轉”四個動詞具有微妙的差別的動詞,性的意象不難想見,最後歸納為同是意象隱喻“蛹成”。“蛹”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不同的意象,例如荀子〈蠶賦〉“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以蛹喻母,亦有保護之意 (28);蔡邕〈短人賦〉 “繭中蛹兮蠶蠕蝢”,蛹的意象被利用來嘲笑侏儒 (29);韓愈在〈會合聯句〉有“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蛹微小而茫遠,卻不乏生機。(30) 若以中國傳統文化中“蛹”的意象來比讀華鈴詩句中的“蛹成”似乎較為牽強。華鈴出身暨南大學外文系,鍾愛英詩,翻譯浪漫主義詩歌,若將華鈴詩句中的“蛹”與性的關係與西方文學文本作平行比讀,“蛹成”的意象似乎別有洞天。“蛹”,即“chrysalis”或“cocoon”,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就在其長詩〈阿特拉斯山的女巫〉(“The Witchof Atlas”)中用“chrysalis”形容女巫身邊的賀墨芙羅黛蒂 (Hermaphroditus)。(31) 古希臘神話中的賀墨芙羅黛蒂是賀墨斯 (Hermes) 和阿芙羅黛蒂 (Aphrodite),是男女同性的半人神。古羅馬詩人奧維德 (Ovid) 在《變形記》第四卷 (Metamorphoses,Book IV) 中寫到,英俊的賀墨芙羅黛蒂和寧芙 (nymph) 薩爾瑪西斯 (Salmacis) 通過性愛合為一體。(32)“nymph”的辭源可以上溯至拉丁語中的“nympha”,而“nympha”正是指“chrysalis”,即“蛹”。(33)
雖然華鈴出身外文系,對西方文學有所涉獵,也未必廣博如上述互文解讀。對於華鈴來說,“蛹”或許祇是兩人在棉被中互纏的意象罷了,又或許他在讀外文系時,曾讀過雪萊的詩,進而移花接木。筆者由現代文學評論的互文觀念 (intertextuality) 對華鈴“蛹”的意象加以闡發,也未必需要墨守文學評論中以作者為中心的成規 (authorly reading)。這正好說明一個問題,詩人有意或無意引用、借鑒或模倣西方詩歌的形式、修辭或意象的時候,他的作品往往與西方詩歌的傳統接軌。將“蛹”的意象往智性 (intellectuality) 而非感性 (sensibility) 的方向解讀,是一種近似解讀英國17世紀初的玄學派詩歌 (metaphysical poetry) 的方法。華鈴的詩〈愛情像一條絲棉被〉在修辭方面的確具有玄學派詩歌的一鱗半爪,但其隱喻和意象的密度仍有不足。玄學派詩人如堂恩(John Donne)、赫伯特 (George Herbert) 和華金 (Henry Vaughan) 等等,往往用 “奇喻”來統攝全詩,利用淵博的知識與靈覺的機智將艱澀的比喻不斷引申,探索哲學、愛情、宗教等命題。玄學派詩歌重智性而輕感性的特質,很受現代主義詩人和詩歌評論家艾略特 (T.S.Eliot) 的推重。艾略特在〈玄學派詩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一文中也相應提出“疏離感性”(disa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 的理論,並借機進一步闡發現代主義詩歌的精神:
詩人也並非一定要對哲學或者其它學科產生興趣。我們祇能這樣說,在當今的文化體系中,詩人的作品必須是晦澀的。我們的文化體系中豐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剝削詩人精緻的感性,必然產生多元和複雜的結果。詩人必須愈來愈博學,愈來愈晦澀,愈來愈間接,才能在必要時將意義易置於語言之中。(34)
“易置”正是華鈴詩中“蛹”的意象的一大特點。如上文所述,“蛹”的意象與性愛之間的關聯,在中國文化中似乎並無表現,而晦澀地存在於西方詩歌中。它被移植到現代漢語詩歌中,本身就是一種語言與意義的易置,也是〈愛情像一條絲棉被〉這首詩最接近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地方。
此外,華鈴的〈愛情像一條絲棉被〉也頗符合30年代現代派詩歌的特點。施蟄存總結現代派詩歌的四個特點為:“1) 不用韻。2) 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齊。3) 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語。4) 詩意不能一讀即瞭解。”(35) 華鈴的這首詩具有前面三個特點,而至於第四個特點則機智有餘而晦澀不足。施蟄存30年代在上海主編《現代》雜誌,主推受英美意象派詩歌影響的“意象抒情詩”,在當時的詩壇引起巨震。雖然《現代》於1935年停刊,但是若說1930年已經在上海開始創作新詩的華鈴沒有讀過《現代》,根本是難以置信的。誠然,孤島時期的華鈴畢竟年輕,沒有形成成熟穩定的詩風,有時候甚至惡趣頻生,如〈無情的美女〉;有時候靈光一閃,揮筆寫下帶有現代派詩歌特點的佳作,如〈牽牛花〉:.
我是朵牽牛花,
看去像隻鈴,
祇是不會響。
我是個啞的鈴。
我果真是隻鈴,
又高高的掛在花棚了,
那我一定要響,
饒舌的,——
“叮嚀叮嚀!”不管甚麽風。
我祇是隻啞的鈴,
假如我是梵啞鈴,
那我又可以響了。
我嘴巴生在甚麽地方?
你不用管!
我就是會唱!
唱得不同凡響!
我是隻鈴了,——
小巧而又震耳的銅鈴,
一天到晚我就“叮嚀叮嚀!”
不過,
教堂樓頂的大鐘也嫌無聊吧?——
我過的又是多沒趣的生涯!
我是隻梵啞鈴了,
我是
柏加里尼‧沙拉沙提的梵啞鈴!——
我就是空前絕後大天才的魂靈;
唉,我主人如今也死了一百幾十年了,
我怎不,又悶得發慌!
我祇是朵牽牛花,——
啞的鈴
渺小的花之鈴。
我不能隨風作響——
“叮嚀叮嚀!”
我也沒有主人偉大的靈魂好仗藉
發出美妙的聲音。
我祇是朵牽牛花,——
啞的鈴
我不會響,
我沒有聲音。
然而渺小的,
我卻有我的生命!
我快活,
我有我的顏色!
你看這蜂,這蝶,
還有,紅尾巴的蜻蜓!
我不說,
我一樣是鈴,
所以不響
為的是不擾你清聽。
我不否認,
它們的存在——
“叮嚀叮嚀!”
我不說,枝頭的百靈,
籬下的蟋蟀,
就是我的聲音;
我跟梵啞鈴一樣好,
我也有我的聖風尼。
我還將告訴你
渺小的我
也許還保不到明天。
祇不過
這不是說我的生命!
既有
野火燒不盡的原上艸,
何來我如此脆弱的魂靈?!
銅鈴
銹了,
梵啞鈴
擱起了
還封滿塵!
你
歲歲還將見我,
牽牛花
啞的鈴,
一樣鮮明
依樣不作聲;
搖搖擺擺的,
在籬間,
幽徑。
我是麻雀的朋友;
我是村姑的花球。
我有我的顏色!
我有我的生命,魂靈!
我
牽牛花,
花之鈴,
渺小的,
一隻啞的鈴。(36)
華鈴再次用到奇喻修辭,自比“牽牛花”,其後整首詩圍繞着“牽牛花”的隱喻不斷擴展。這首詩的前半部分,即前六節,利用各種“牽牛花”的比喻,來探討如何發出聲音,亦即“響”的問題。第一節的喻體為“啞的鈴”,“牽牛花”形狀似“鈴”,花不會響,因此是“啞的鈴”;第二節的喻體為“鈴”,“牽牛花”有發出聲音的慾望 (“那我一定要響”),假設自己是高掛花棚的“鈴”;第三節的喻體為“梵啞鈴”(即小提琴“violin”的音譯),牽牛花從前兩節因“牽牛花”與“啞的鈴”形似而產生的比喻,過渡到因“啞的鈴”與“梵啞鈴”聲似而產生的比喻。“牽牛花”假設自己是“梵啞鈴”,這樣就能放聲歌唱,就能“唱得不同凡響”;第四節的喻體是“銅鈴”,呼應第二節的喻體“鈴”。此時“牽牛花”變成“銅鈴”,卻對自己產生懷疑(“我過的是多麼沒趣的生涯!”),因為它所發出的是缺乏藝術性的聲音;第五節的喻體是“梵啞鈴”,呼應第三節同一個喻體。此時“牽牛花”甚至變成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帕加里尼 (Niccolò Paganini) 的小提琴,主人已往,“悶得發慌”;第六節回到最初的喻體“啞的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不能“隨風作響”。前四節的隱喻皆為象徵性隱喻(symbolic metaphor),第五節到達高潮時華鈴用到的隱喻則是具體性隱喻(concrete metaphor)。這六節詩的情緒隨着每一節對“響”的不同態度而跌宕起伏:“牽牛花”從第一節不能發聲,到第二節一定要發聲,到第三節如果可以發聲,再到第四節發出沒有藝術性的聲音,再到第五節發出充滿藝術性的聲音,再回到第六節還是不能發聲。修辭的變化與詩情的起伏引領詩的節奏,正是施蟄存所提出的現代派詩歌音樂性的特點:“以詩意或情緒的抑揚頓挫為詩的音樂性。”(37)
這首詩的後半部分,可以被看作“牽牛花”自我認識的過程,對生命意義的探索。“牽牛花”在第七節認識到自己的渺小,認識到自己並不能發出物理意義上的聲音,也認識到自己的顏色與生命;第八節,“牽牛花”說自己“不響”,卻不否認響聲的存在,依然“叮嚀叮嚀!”,結合第七節來解讀,“牽牛花”並非發出的物理意義上的聲音,而是生命的聲音;第九節,“牽牛花”借“百靈”和“蟋蟀”發聲,也有自己的藝術性,也有自己的“聖風尼”(即交響樂symphony);第十節,“牽牛花”認識到自己生命的短暫與燦爛,以“脆弱的魂靈”對照前半部分第五節“天才的魂靈”,並以“原上艸”暗示重生;第十一節給出“牽牛花”探索自我的答案,“銅鈴/銹了”呼應第四節,“梵啞鈴/擱起了”呼應第五節,這兩種會響的“鈴”已廢,而“牽牛花”這隻“啞的鈴”卻歲歲重生,“依樣不作聲/搖搖擺擺的,/在籬間,/幽徑”;最後一節回歸喻體“啞的鈴”,既呼應第七節“牽牛花”的顏色和生命,也解開第一節對“不響”的困惑。後半部分前面幾節情感上較為平穩,在第十節到達情緒的高潮,在最後兩節回到歷經掙扎後的幽思與覺悟。“牽牛花”是整首詩的核心意象,將詩人起伏的詩情和精神的寄託具象化 (reification),進而昇華為一個象徵 (symbol),象徵孤島的生命之音。詩人在孤島以詩發出生命之音,不難看出詩人對時局的感懷。30年代末,抗戰不順,在孤島沉鬱的氣氛中,詩人以“牽牛花”自喻,響應孤島外的抗戰,以堅毅的生命之音抒發孤島不沉之志。華鈴正是這朵孤島上的牽牛花。
整首詩對尾韻的經營非常明顯。“鈴”、“嚀”、“靈”、“命”、“蜓”、“聽”、“明”、“徑”、“鈴”在行尾的重複出現,形成比較明顯而不規則尾韻“ing”。詩的前半部分,還有“響”、“方”、“唱”、“慌”形成另一組不規則尾韻“ang”,而這一組尾韻則沒有出現在後半部分。不規則尾韻“ang”在上下兩部分的差異,對應“牽牛花”在上下兩部分對“響”的不同態度。“牽牛花”在上半部分希望“響”,因此有尾韻“ang”;而“牽牛花”在下半部分則不再執着,因此沒有尾韻“ang”。此外,〈牽牛花〉的音樂性還在於其具有類似藝術歌曲的結構,上下部分各有鬆散而明顯的主歌部分(頭五節)和副歌部分(尾一節),80年代作曲家羅忠鎔將這首詩改編成女高音獨唱的藝術歌曲也不足為怪。(38)藝術歌曲與新詩的結合,在20世紀中國也是較為常見的現象。藝術歌曲往往短小精緻,因此羅忠鎔必須對原詩進行縮減,筆者將其抄錄如下:
我是一朵牽牛花,
啞的鈴,渺小的花
鈴。我不會隨風作響
叮嚀,叮嚀,我發出美妙的聲音。
我祇是朵牽牛花,啞的鈴,
我不會作響,我沒有聲音,
然而,渺小的我,卻有我的生命。(39)
羅忠鎔縮減出來的兩段歌詞,正好對應華鈴詩的上下部分。雖然歌詞沒有詩修辭上的張力,但是可以從側面反映〈牽牛花〉類似藝術歌曲的結構。
華鈴並沒有如施蟄存所說“放棄了文字的音樂性”,也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派詩人。〈牽牛花〉在修辭上的藝術性不容置疑,華鈴卻在40年代中放棄藝術性的追求,轉而大量創作口語化的充滿激情的政治抒情詩。(40) 華鈴這一類的創作在〈可真是時候〉(1946) 中可見一斑:
國民的公敵呀!
火箭炮,
衝鋒槍,
不是武器!
定製四萬萬五千把剮刀吧!
進攻人民的大豆、高粱,
啥子用哪!
進攻人民怨恨的心吧!!(41)
為此,李健吾曾對其提出含蓄的批評:“詩是寫出來的,你寫來的詩卻有時候不全都是好詩。你應當再往語言裡揣摩,應當再往表現裡揣摩。光祇熱情不足以成為詩。因為詩是寫出來的。語言文字太有關係了。”(42) 許光銳的批評則更加直白:“他變成了一個詩底叛徒。他自誇他發現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健康的道路,一條脫去外衣露出本性的路。[⋯⋯]我擔心的是:過度的自由與毫無拘束的熱情奔放,對藝術是否一種損害?”(43) 華鈴顯然不接受這些批評,並在〈一封公開信〉中對其一一歪曲反駁,言辭間不乏調侃之意。(44) 華鈴自比何其芳的一段文字標誌着他文風的轉變:“不管我的〈牽牛花〉比何

李健吾與華鈴合照
(取自《華鈴詩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
其芳先生《夜歌》以前的詩是否高明一點,我卻多多少少和何先生對自己《夜歌》以前的作品似的,不滿於我自己一度驕傲的〈牽牛花〉。”(45)何其芳在30年代初創作的詩歌,詩意晦澀、意象瑰麗,後被收錄於《預言》;由於受到毛澤東〈延安講話〉的感召,詩風大變,熱衷於缺乏藝術性的創作朗誦詩,後被收錄於《夜歌》。劉再復將這種 “思想進步,創作退步”的現象稱為“何其芳現象”(46)。這種現象在華鈴的身上表露無遺。李健吾和許光銳的批評顯然集中於華鈴詩風的轉變上,而華鈴卻以寫詩所花費的時間來回應:“我寫作醞釀的時間比寫作的時間長得太多了。”(47) 不難想見詩人的棱角與倔強。
雖然何其芳詩風的變化使他落得“半個詩人”之名,但他的詩集《預言》還是讓人看到他早期在詩藝上的追求,以何其芳《預言》為題的研究也從不絕於學術界。而華鈴對自己詩歌中的藝術性否定得如此徹底,以致過去學者對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熱衷抗戰文藝的、熱情四射的孤島詩人上,而沒有從文本上挖掘他的詩中的現代派特徵。華鈴在40年代大量創作的政治抒情詩將他帶有現代派特徵的詩作完全掩蓋,而且他這段時期對“詩人”的理解也在於“詩人”需要肩負的歷史使命,而非必須承擔的藝術責任。華鈴的想法也真實地反映在〈詩人與惡勢力〉這首詩中的兩節:
是的,正是他,你們一度愛戴的詩人,
用隱喻寫過
百十美妙而又完整的詩篇,
博得你們聲聲叫好;
累得過激的朋友還擔心 ——
他,為藝術而藝術了。
聽,現在,他詩人瘋了:
他丟了隱喻,丟了美麗的言詞;
他祇想罵,
不,他想打!——
他罵:“狗東西,王八蛋!”
他要行兇,他要造反。
當孤島時期過去,當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結束,華鈴的政治抒情詩也寫到了盡頭。或許在華鈴看來,到了50年代,他心目中的“詩人”也完成了歷史使命,不再需要行兇造反,他對自己作為“詩人”的定位產生了疑問,創作的熱情也因此開始有所減退,到了晚年仍將自己看作“孤島詩人”。
【註】
(1) 上海孤島時期的文學概況可參考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1985。
(2) 華鈴:《向日葵》,上海 : 五洲書報社,1938;《玫瑰》,上海 : 五洲書報社,1938;《牽牛花》,上海 : 聯益書社,1938;《滿天星》,上海 : 五洲書報社,1940。
(3) 欽鴻:〈時代的號角——談澳門現代詩人華鈴的詩歌創作〉, 《華鈴詩文集》, 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頁1。
(4) 欽鴻:〈華鈴年譜〉,《華鈴詩文集》,頁273-275。
(5) 華鈴:《火花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9;《華鈴詩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
(6) 〈編者的話〉,《澳門現代詩刊》第7期 (1994) ,頁89。
(7) 鄭煒明:〈80年代澳門的文學作品〉,《澳門教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1995,頁223。
(8) 鄭煒明:〈澳門中文新詩史略〉,鄭煒明編《澳門新詩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111。
(9) 欽鴻:〈華鈴年譜〉,《華鈴詩文集》,頁273。
(10) 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 (1938-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73。
(11) 朱壽桐:〈略談澳門新詩研究的學術路徑〉,《澳門日報》,2012年12月5日。
(12) 見華鈴:《火花集》,頁80-83。關於“藝聯”的簡介,見鄭煒明〈前言一:澳門的戲劇活動與作品〉,《澳門當代劇作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3。
(13) 鄭煒明:《澳門文學史》,濟南:齊魯書社,2012,頁58。
(14) (15) 鄭煒明:《澳門文學史》,頁80-83;頁8-9。
(16)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頁143-144。
(17) 欽鴻:〈華鈴年譜〉,頁193。
(18)見吳岩:〈記詩人華鈴〉,《書城雜誌》第1期 (1994):頁43-46;許光銳:〈回憶華鈴〉,《華鈴詩文集》,頁315-319。
(19)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304。
(20) (21) 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 (1938-2008)》,頁74;頁76-77。
(22) 欽鴻:〈編後記〉,《華鈴詩文集》,頁329。
(23) 華鈴:〈華鈴自傳〉,原刊《中國現代文學辭典‧詩歌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後收入《華鈴詩文集》,頁239-241。
(24) 呂志鵬:《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 (1938-2008)》,頁72;程逸:〈詩人華鈴〉,《信報》,1982年7月5日。
(25) 許光銳:〈華鈴底道路〉,《火花集》,頁187-189。
(26) 華鈴:〈無情的美女〉,《華鈴詩文集》,頁39。
(27) “conceit”的譯名無關本文之宏旨,為了避免混淆,本文一律採用“奇喻”,雖然此譯未必合適。
(28) 見楊柳橋:《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2009,頁511-512。
(29) 見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校註《全漢賦校註(下)》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926-928。
(30)見汪聖鐸譯註〈會合聯句〉,許逸民編《容齋隨筆全書類編譯註(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頁217。
(31) Percy Bysshe Shelley, ‘The Witch of Atlas,’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ed. Mary Shelley, vol.3(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64), pp.77-78.
(32) Ovid, trans. Joseph Davidson, Metamorphoses (London:B.Law, 1797), pp.146-149.
(33)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20 vol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oed.com/.
(34) 作者自譯,原文為:“It is not a permanent necessity that poets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or in any other subject. We can only say that it appears likely that poets in our civilization, as it exists at present, must be difficult. Our civilization comprehends great variety and complexity, and this variety and complexity, playing upon a refined sensibility, must produce various and complex results. The poet must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more allusive, more indirect, in order to force, to dislocate if necessary, language into his meaning.”,見 T.S.Eliot, ‘The Metaphysical Poets,’in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32), p. 248.
(35) 施蟄存:〈《現代》雜憶〉,《施蟄存全集》(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279。
(36) 華鈴: 〈牽牛花〉, 《牽牛花》, 上海: 聯益書社,1939,頁5-15。《牽牛花》中的版本與《火花集》中的版本 (頁44-47) 大體相同,祇改了幾個錯字,分行有數處不同。
(37) 施蟄存:〈《現代》雜憶〉,頁282。
(38) 羅忠鎔:〈牽牛花(女高音獨唱)〉,《中國音樂》第2期(1982):頁65-67。筆者無從考究歌詞的作者究竟是羅忠鎔還是華鈴,鑑於羅忠鎔曾將許多詩改編成藝術歌曲,如〈涉江采芙蓉〉、杜牧的〈江南春〉、舒婷的〈二三事〉等等,筆者暫且推測羅忠鎔是〈牽牛花〉歌詞的作者。關於作曲方面的分析,見劉雪莎〈羅忠鎔藝術歌曲〈牽牛花〉分析〉,《中國音樂學》第3期2008):頁106-109;又見梁甫基〈亨利米特作曲技法在我國音樂創作中的運用〉,《藝術探索》第1期(1988):頁53-63。
(39) 羅忠鎔:〈牽牛花(女高音獨唱)〉,頁65-67。
(40) 華鈴:〈一封公開信 —— 給老師李健吾及其他工作上的朋友〉,《華鈴詩文集》,頁226-227。
(41) 華鈴:〈可真是時候〉,《華鈴詩文集》,頁103。
(42) 李健吾:〈給華鈴的一封信〉,《華鈴詩文集》,頁294。
(43) 許光銳:〈華鈴底道路〉,《火花集》,頁189。
(44) (45) 華鈴:〈一封公開信〉,《華鈴詩文集》,頁229-233;頁226。
(46) 劉再復:〈赤誠的詩人,嚴謹的學者〉,《文學評論》第2期 (1988):頁6。
(47) 華鈴:〈一封公開信〉,《華鈴詩文集》,頁230。
* 宋子江,現職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研究統籌主任,兼讀該校翻譯系博士。曾著詩集三本,詩翻譯多本,論文散見學術雜誌。2010和2011年兩度任澳洲本德農藝術邨駐留詩人。2013年獲意大利諾西特國際詩歌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