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化局主持出版的《大明國圖志 ——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以下簡稱澳門版)(1),距離羅薩度主編的《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以下簡稱羅馬版)(2),相隔二十年之久。澳門版按照羅馬版原樣影印了全部中國圖志手稿,裝潢與印刷之精美,足以與羅馬版媲美。羅馬版刊登的論文以意大利文為主,偶有英文,而澳門版論文有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三種文字,因而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和鮮明的澳門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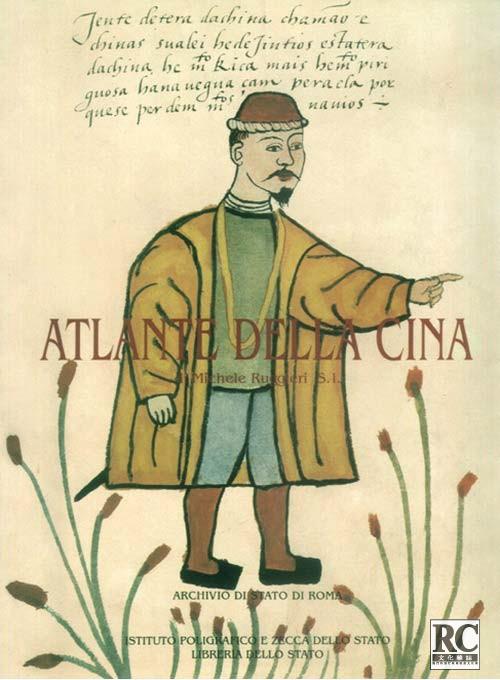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 封面羅馬檔案館及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Stato 出版,羅馬:1993年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版捨棄了羅馬版的所有論文,並發表了四篇新文,計有羅薩多〈再版《羅明堅地圖集》〉,金國平〈譯者弁言〉以及〈“Lampacao”史地範圍之追溯〉、薩安東〈羅明堅在歐洲〉。如此取捨,很大程度上是學術進步的必然結果。羅馬版學者一致認為,羅明堅手稿所本為明代著名的《廣輿圖》,但最近汪前進發現手稿中一幅《遼東邊圖》的殘葉來自《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以下簡稱《大明官制》),而且許多文字內容也來自同書,據此判斷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底本不是《廣輿圖》,而是《大明官制》。(3) 澳門版吸收了這個研究成果,金國平通過大量的王府以及“玉面狸”等特產專名,更進一步佐證了汪前進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澳門版不是羅馬版簡單的翻版,而是另起爐灶,並呈後來居上之勢。
澳門版的另一特色,是將羅明堅手稿的文字部分翻譯為中文。譯者金國平介紹說,羅馬版“對地名做了甄別,但僅僅限於省、府、州,數目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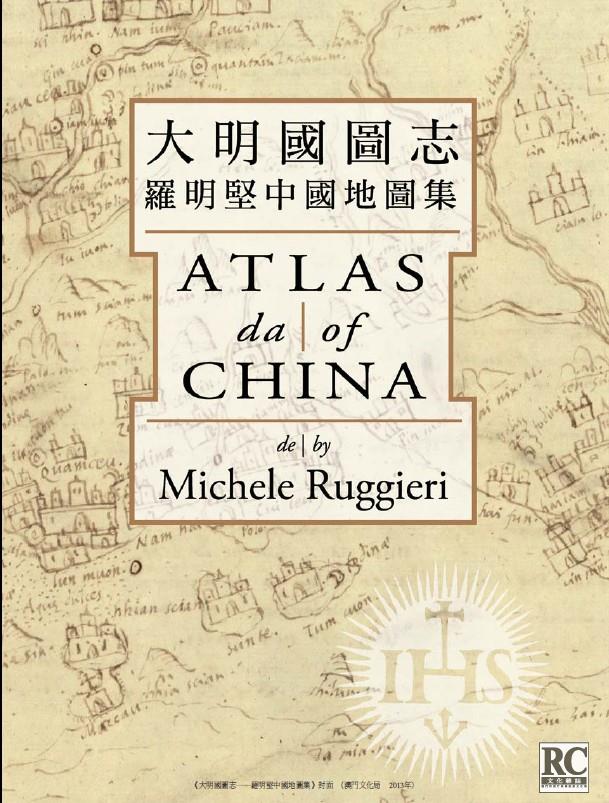
多的縣未做漢譯,大量的王府與衛所的漢譯也空缺。本譯為地名全譯本”。羅明堅手稿原文基本上為拉丁文,個別為意大利文,而這些文字在我國屬於小語種,能直接利用者寥寥無幾,因此,漢譯對於我國廣大讀者無疑為一福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漢譯存在着若干毛病乃至敗筆,堪稱澳門版之美中不足。本文指出漢譯的缺陷,並就如何深入研究羅明堅中國圖志手稿問題談點個人淺見。
缺陷之一:刪節與嫁接
澳門版漢譯糾正了羅馬版的某些錯誤,如羅馬版轉寫文字中將原稿的T14與T16顛倒了位置,並將北直隸圖志T32誤寫為T30,澳門版一併予以糾正。然而,羅馬版原先的一些標識,漢譯卻沒有譯出。如手稿T32北直隸僅有順天府的兩個州,即通州和昌平州,其餘部分均採自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相關內容,在其嫁接部位,羅馬版註明資料源自羅馬耶穌會檔案館 (ARSI, Iap.Sin.,101/II f.204 v);又如手稿T48雲南省圖志,羅馬版對於其中多次引用的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資料,標出“f.215r.,f.217r.,f.218.r.”等標識,而澳門版對此沒有翻譯,從而給人以這些手稿來源同一的錯覺。
就文本而言,澳門版明顯的缺陷是其刪節。譯者在〈譯者弁言〉中解釋道:“為了節省篇幅,譯漢刪節了重複部分,如海南島、廣東省、福建省和浙江省。”在這些刪節部分中,海南島、福建省和浙江省各有兩種,譯者各擇其一。廣東省的圖志有三種,譯者的處理別具一格。T12是一種完整的圖志,而T14和T16均為殘稿,祇有廣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和肇慶六府,缺少高州、廉州、雷州和瓊州四府。譯者將T16的六府嫁接T12後面四府,合為廣東省十府。儘管羅馬版有嫁接的先例,但其補缺的動機情有可原,而廣東省三種圖志中T12有完整的十府,澳門版譯者為甚麼不直接翻譯T12?另外,如果一定要嫁接,T16與T14同為六府,譯者為何取前者而捨後者?在我們分析三種廣東省圖志的差別後,也許可以找到問題的答案。
筆者註意到,譯者所謂“重複部分”,並非一模一樣,而是頗有差異。就三種廣東省手稿而言,它們之間的區別相當明顯。雖然都是廣東省,但它們的標題不同。T12題為 TABULA SECONDA PROVINTIA QUAMTUM (第二圖,廣東省),T14題為 DE SINARUM REGNI PROVINTIA DICTA QUAM TUM (中國名叫廣東的省),T16 題為 DE QUAM TUM PROVINTIA(廣東省)。此外,手稿的形式也有差別。T12 每個府的前面沒有數字,其餘的則有數字,如韶州府,T12 寫為“Sciau ceu fu”,T14為“2ªCiau ceu fu”,T16則為“2ª fu, Sciau ceu”。再則,從筆跡看,T14與T16出自羅明堅之手,而T12則不似羅明堅的筆跡。顯而易見,這是三種不同的廣東省手稿,T12與T6 (TABULA PRIMA INSULAE HAINAN, 第一圖,海南)、T18(TABULA TERTIA PROVINTIAE FUCHIEN, 第三圖,福建省) 為同類;T14自成一體;T16則與T75 (DE CHIANSINA PROVINTIA 江西省) 等多種地圖同類。
除了形式,三種廣東省手稿的內容也有差別。例如關於廣州的四至等消息,T12寫道:“東至惠州55意大利里,西至肇慶55意大利里,南至海85千步(milia passum),北至韶州101意大利里;至北京順天府 (即北京省京師 Quinsi Pachinae provintiae) 1959千步,至南京省應天府1097意大利里。米、小麥以及其它穀物 (orizae et frumenti et aliarum frugum) 33,000石。”T14寫道:“東至惠州240里,60意大利里,西至肇慶240里,60意大利里,(4) 北至韶州400里,100意大利里, 南至海580里 (?意大利里);至北京省順天府7835里,至南京省應天府4390里。年產穀物53石,米和小麥300,000石。”T16則載:“東至本省惠州府博羅縣55意大利里,西至肇慶府高要縣55意大利里,南至海岸85意大利里,北至韶州府英德縣63意大利里;至北京省京城順天府,即京師 (Chin sci,俗稱行在 Chin zai) 1959意大利里,至南京省應天府 (俗稱南京 Nan chin) 1097意大利里。盛產大米、玉米、豆類和其它穀物 (orizae et frumenti, leguminum et aliarum frugum),年產32,000石。”三種廣東省圖志的上述消息互異,與《大明官制》的相關消息也有所差異。
三種廣東省地圖中有關耶穌會在華傳教的消息也大不相同。T12在肇慶府中載:“Ubi recens residentia patrum Iesuitarum (那裡有耶穌會神父的新寓所)”。T14沒有肇慶寓所的消息。T16關於耶穌會寓所的消息有兩則。韶州府中載:“Hic resident duo Patres Societatis Jesu (這個居住着兩個耶穌會神父)”,肇慶府則載:“Hic fui prima residentia trium Patrum Societatis Jesu (這裡曾經是三名耶穌會神父的第一寓所)”。筆者猜測,這些耶穌會的消息是金國平對三種廣東省圖志取捨的主要考量,即T16載有耶穌會在廣東省的全部消息,而T12有肇慶而無韶州的消息,T14則一無所有;因為耶穌會在華消息對於耶穌會士繪製的中國圖志十分重要,所以譯者取T16並以T12補全之。毫無疑問,上述耶穌會在廣東的消息意義重大。1583年羅明堅與利瑪竇在肇慶建立了中國內地的第一個耶穌會寓所兼教堂,1588年羅明堅返回歐洲,不久利瑪竇被逐出肇慶並移至韶州,1589年在韶州建立韶州寓所,肇慶寓所遂不復存在。既然肇慶寓所新近建立,當無韶州寓所可言,所以T12韶州府自然沒有耶穌會寓所的消息;由此可以判斷,這個手稿成於1583年至1589年之間,當更靠近1583年。T14沒有任何耶穌會寓所的消息,為此可以判斷其寫作時間當為1583年之前。T16肇慶寓所和韶州寓所的消息兼而有之,而且肇慶寓所用的是過去時,所以該手稿的寫作時間當為1589年之後;它與T75同類,而T75署有年代1606年,為此可以判斷其寫作時間為1606年。總之,三種廣東省手稿不但內容不同,而且寫作年代也有異。因此,三種廣東省地圖應該全部翻譯。至於福建省、浙江省和海南島的所謂“重複”,也非完全一致,最好照譯而不刪。
缺陷之二:漏譯與錯譯
對於譯文,金國平在〈譯者弁言〉有此說明:“羅明堅繪圖與底本的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一方面方便了翻譯,但另一方面卻增加了難度。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採取的翻譯標準是:儘量尊重羅明堅的譯文,但不忘顧及原書中之遣詞造句。”在筆者看來,《大明官制》對於漢譯提供了較多的便利,據此,譯者甚至有意無意地糾正汪前進文章中的某些錯誤。例如,汪文稱羅明堅手稿中沒有提及“醫學”與“陰陽學”,而根據原稿中“Universitas medicinae et religionis(宗教與醫學大學)”,金國平正確翻譯為“醫學和陰陽學”(即《大明官制》中“陰陽醫學”)。又如,關於瓊州府所屬瓊山縣,原稿寫有“quae neque distantiam neque situm habet”,汪前進譯為“距離、方位不明”,並據此認為羅明堅不解“附郭”之意;但實際上汪前進對原文理解有誤,較為準確的翻譯當為“沒有距離、也沒有(自己的)地點”,意思是與瓊州府同城,即“附郭”。金國平未受汪文的影響,簡單而正確地將之譯為“瓊山縣附郭”。
另一方面,與《大明官制》基本無關的文字,例如,羅明堅用意大利文撰寫的T9-10,譯文則存在着較多的問題。例如,關於椰子樹的廣泛用途,羅明堅寫道:
Primo del suo legname solo senza mescolare altro si fanno i navilij, delle foglie se ne fano le vele e del suo frutto si caricano detti navilij, che sono noci simili al sapore delle nostre amandole,delle quali si fa vino et dal vino aceto.... Queati frutti delle migliara se sogliono metter per savorra o lastro delle navi, per difrescare i passagieri con la sua acqua, et da relevarsi supplendo al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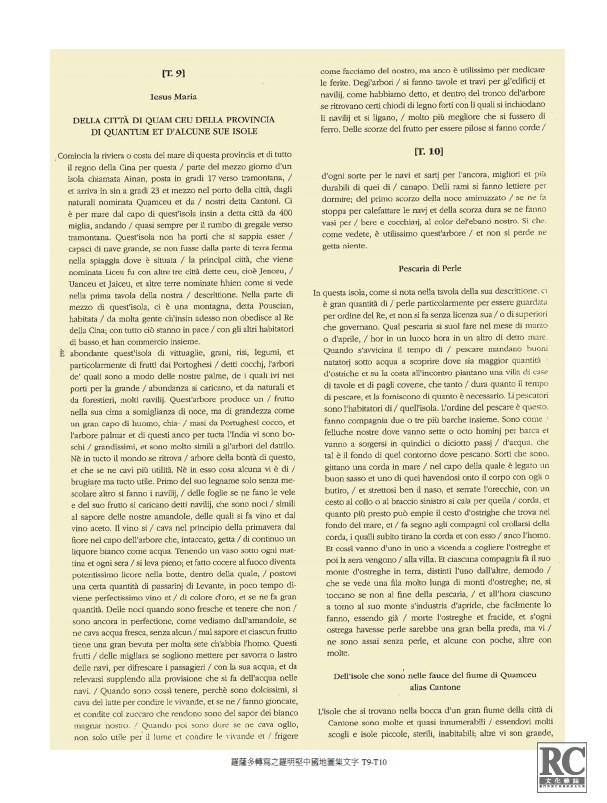
provisione che si fa dell’acqua nelle navi. Quando sono cossì tenere, perché sono dolcissimi, si cava del latte per condire le vivande, et se ne fanno gioncate, et condite col zuccero che rendono sono del sapor del bianco magnar nostro. Quando poi sono dure se ne cava oglio, non solo utile per il lume et condire le vivande et frigere come facciamo del nostro, ma anco è utilissimo per medicare le ferite. Degl’arbori si fanno tavole et travi per gl’edificij et navilij, come habbiamo detto, et dentro del tronco del’arbore se ritrovano certi chiodi di legno forti con li quali si inchiodano li navilij et si ligano molto piu megliore che si fussero di ferro. (5)
金國平譯文:
首先,不必混加任何其他木質,其木材便造船。核桃狀之菓實味似我們的杏仁,可釀酒與造醋。[⋯⋯] 如前所述,木材可供建造樓宇內用之桌臺與船舶之橫樑。樹心木質堅硬。用來加固船隻,質堅如鐵。
與原文相比,漢譯遺漏了許多內容,如椰子樹葉可製帆、菓實可為船舶壓倉,新鮮椰子之汁可解渴、調味以及炮製布丁,而乾燥椰子之油可照明、油炸食物以及醫治創傷等。事實上,漢譯份量不及原文內容的三分之一,而且沒有使用任何省略號。此外,已譯部分也有不妥之處,如“tavole”不是“桌臺”,而是木板,可用於造屋,也可用於造船; “ travi” 作為“棟樑”,也是屋、船通用。譯文中不見原文中“某種堅硬木釘” (certi chiodi di legno forti) 及其“釘船”(si inchiodano li navilij) 的功效,而譯文“質堅如鐵”也不合原文所強調的木釘強於鐵釘之意。
又例如,關於海南島居民,羅明堅寫道:
Nella parte di mezzo di quest’isola ci è una montagna, detta Pouscian, habitata da molta gente ch’insin adesso non obedisce al Re della Cina; con tutto ciò stanno in pace con gli altri habitatori di basso et han commercio insieme. (6)
金國平翻譯為:
一山脈橫貫該島中部。據傳,住民多不歸順中國國王,但與島外人民和平相處,相互通商。
羅明堅原文有山名 Pouscian, 當指位於海南島中部的五指山或黎母山,漢譯省略不顧。羅明堅筆下“至今不服從中國皇帝”的“許多人 (molta gente)”,指居住在 Pouscian(五指山?)山上的山民,《明史》卷四十〈安定縣〉載:
“南有五指山,亦曰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為熟黎,內為生黎。”這些山民當為“生黎”,或《大明官制》瓊州府下幾次出現的“黎寇”,指尚未歸化或“不服從中國皇帝”的黎人。相反,所謂“低地的其他居民 (gli altri habitatori di basso)”當指平原居民,是服從皇帝的順民,也許包括“熟黎”。漢譯將“山民”錯譯為“居民”,並將“低地的其他居民”錯譯為“島外人民”,似乎海南島居民多不歸順皇帝,顯然與史實不符。
再舉一個例子。羅明堅關於海南島珠池寫道:
Quando s’avvicina il tempo di pescare mandano buoni natatorj sotto acqua a scoprire dove sia maggiore quantità’ d’ostriche et su la costa all'incontro piantano una villa di case di tavole et di paglia coverte, che tanto dura quanto il tempo di pescare, et la forniscono di quanto è neccesario. Li pescatori sono l’habitatori di quell’isola. (7)
金國平譯文:
採集期間,潛者下水,盡可能多撈蚌殼。海岸上建起草頂木屋。採期多長,它就保留多長。裡面一切應有盡有。島民皆漁人。
羅明堅寫的是採珠之前的準備工作,即先派遣善泳者潛水,探明水下珠蚌情況,然後再在相應的海岸搭建茅屋群,漢譯第一句全部譯錯,而“海岸上建起草頂木屋”句也有毛病,海岸前缺少“相應的 (all’incontro)”,而“草頂木屋”後則缺少“村(villa)”。在羅明堅和利瑪竇等早期耶穌會士的語境中,villa 經常指縣城,有時也指村落,這裡當指臨時茅屋村落。“Li pescatori sono l’habitatori di quell’isola”意為“這些漁人是海南島居民”,漢譯“島民皆漁人”顛倒了主語與賓語,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彷彿所有的海南島居民祇幹採珠這種營生。
缺陷之三:註釋問題
翻譯過程也是一個研究過程,而譯者的研究成果,則可體現於譯文的註釋。羅明堅中國圖志手稿中載有Lampacao, 金國平論文〈“Lampacao”史地範圍之追溯〉,某種意義上是一超級大註,而此文本身的註釋就有三十三個,長達一頁有餘。相比之下,羅明堅手稿漢譯的註釋顯得太少,總共三十七個,篇幅不足一頁。譯者可以而且應該做更多的註釋。有些註釋是必不可少的,如T9載東莞駐紮一名中國官員,中國人稱之為“Aitan”,金國平譯為“海道”而未加解釋。羅明堅和利瑪竇等通常將中文的海道拼寫為Aitao,並非Aitan,金國平如此翻譯,當源於對海道副使的深入研究,在他與吳志良合著的《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一書中,提到萬曆十年駐紮在東莞南頭的海道副使,這意味着至少此時海道已經從廣州移至東莞;這一消息來自大英博物館所藏古手抄本《中國諸島簡訊》,羅明堅所記與之脗合。金國平當為此做一註釋,並說明 Aitan 為 Aitao 之誤。
漢譯現有的註釋中,有些相當精彩。T70湖廣省長沙府茶陵州的土產中,羅明堅寫道:“est etiam magna copia lapidum praeciosorum vocantur io mien li”(此處還有大量的名叫“玉面狸”的寶石),漢譯註35中正確指出:“‘玉面狸’不是一種寶石,而是一種狸。又稱牛尾狸,菓子狸。面白色,尾似牛,喜食菓實,捕鼠勝於貓。”可惜的是,譯者在糾正羅明堅錯誤的同時,自己卻犯了新的錯誤。例如,關於湖廣省辰州沅陵的土產,《大明官制》載有麩金、水銀、丹砂、石青,羅明堅手稿有關土產則寫為 “Argenti vivi fodinae. Sunt lapides preciosj: aurum in magna copia (水銀、寶石、大量的金子)”,漢譯譯為“水銀、寶石、麩金”,並就“寶石”加註 36:“漢語原文為‘青石’,可作建築材料、碑板等用。[⋯⋯]”金國平此處顯然看錯了漢語原文,原文中的“石青”為藍色的礦石,可作顏料,與可用作建材的“青石”是兩回事,而羅明堅將丹砂、石青等統稱為寶石,雖不中亦不遠矣。另外,“麩金”一詞,《大明官制》湖廣省中此處是首次出現,羅明堅寫為“大量的金子”,也不十分準確,如同漢譯註33所言,“麩金為一種碎薄如麩子的金子”。但是註33放錯了地方,註在沒有麩金的長沙府攸縣。關於攸縣的土產,《大明官制》載有銀、海金沙,羅明堅將後者正確譯為 arena aurea e mari (大海的金沙),海金沙不是麩金。在長沙縣的土產中,羅明堅也寫了 arenae aureae e maris,金國平正確還原為海金沙。海金沙為一種多年生攀援草木,可入藥。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色黃如細沙也,謂之海者,神異之也。”這個土產似也可一註。
漢譯最長的註釋是註9,佔全部註釋篇幅三分之一強。羅明堅手稿T3介紹中國概括時最後涉及宗教,其中有一句話寫道:“Hic apud Cinas existunt Christi veneratores, etiam virgo vocatur habens lunas et draconem sub pedibus”,金國平譯為“在中國,有人崇拜基督,亦供奉一腳踏月亮與龍之童貞聖母”(8),註9分析了龍的拉丁文涵義,回顧了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並聯繫到澳門大三巴牌坊上“聖母踏龍頭”的圖案而得出結論:
“聖母踏龍頭”的象徵意義是正義戰勝邪惡。羅明堅此語告訴我們,這是16世紀中國崇拜的一幅聖母畫像,所以將它刻到了耶穌會在澳門的標誌性建築物——大三巴牌坊上。
然而,羅明堅所說童貞者,腳下不但有龍,而且有月亮,而澳門大三巴牌坊上“聖母踏龍頭”則沒有月亮,似不可等而同之;再者,如果龍在西方文化中代表邪惡,那麼月亮又是甚麼涵義?筆者發現,在致總會長一份著名的中國傳教報告中,羅明堅回顧1585年底至1586年初紹興之行時寫道,1586年1月15日,他與同會麥安東抵達Caulino (高嶺?)城,居留三日,其間應邀去一佛寺赴宴,看到僧人做佛事,如同“魔鬼舉行天主教神聖教堂的儀式”,而麥安東“輕易地誤以為一個腳下有龍和月亮的女人畫像 (facilemente s’ingannarebbe che quella donna pittata che vedeva tener il dragone et la luna debasso i piedi)”為聖母瑪麗亞 (Madonna)(9),而佛寺中腳下有龍與月亮的“女人畫像”無疑為觀音像。天主教在華傳教之初,聖母與觀音相互混淆的例子甚多,例如耶穌會士在肇慶期間,不少當地居民將聖母像當作觀音像並借此求子。(10) 羅明堅此處所記為一相反的例子,即麥安東輕易地將佛教觀音誤為天主教聖母;一個耶穌會神父尚且如此混亂,早期中國天主教徒則可想而知。因此,前引T3羅明堅關於宗教的敍述,更為合理的解釋或許是,中國的天主教徒誤將觀音當作童貞聖母。至於澳門大三巴牌坊上“聖母踏龍頭”的圖案,也更可能是借鑒觀音與龍的形象,以此顯示聖母如同觀音一樣法力無邊,或許無涉“正義戰勝邪惡”。
註釋中涉及面最廣的是註1和註10,堪稱敗筆。先看註1:“古羅馬單位,作為里程單位的‘步’,相當於0.4872千米。”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換算,比如說廣州到北京的距離,羅明堅手稿T16寫為m.1959,漢譯為1,959,000步,根據其換算等於954,425千米,數十倍於赤道的長度(40,076千米)。羅明堅手稿中的m,是 miglia 的簡寫,可謂羅馬里 (1,482.5米),也可為意大利里(1,851.85米),為甚麼譯者偏偏使用“步”呢?究其原因,或許因為在手稿T12中,廣州與北京的距離寫為1959 milia passum,即1595千步;換言之,milia passum (一千步) 等於 migliaia (一羅馬里或一意大利里),金國平註釋中“千米”必為“米”之誤。然而,即使一步等於0.4872米也無濟於事,因為據此廣州與北京的距離約等於945千米,比實際距離又短了許多。事實上,古羅馬的一步不是等於0.4872米,而是約等於1.48米,按照這一換算,廣州與北京的距離為2899千米,接近《大明官制》所載7835里。無論如何,羅明堅手稿用的不是羅馬里,而是意大利里,如T16所寫 italica miliaria (意大利里);而且“四里等於一意大利里(4 li sono un miglio)”,如T4廣東省地圖左上角批註所示。事實上,《大明官制》中的7835里除以手稿的m.1959,等於3.9995,可知原稿的換算是一意大利里約等於四里。此外,手稿T14中也有不少現成的例子,如前述廣州東至惠州240里,即60意大利里,等等。因此,對於原稿中的里程單位,漢譯可以使用原來的數字和單位,並註明一意大利里等於四里,或者乾脆還原《大明官制》的里數。
再看註10。這是關於“磅”的換算,譯者寫道:“古羅馬時代,作為重量單位的‘磅’,相當於328.9千克。”這也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換算。根據《大明官制》,廣州的糧食年產量為32萬石,手稿T16寫為32萬pondo,漢譯則為320,000磅。關於一石的重量,通常有100市斤和120市斤兩種說法,以此換算,32萬石等於3200萬市斤(1600萬公斤),或者3840萬市斤(1920萬公斤),而根據漢譯的換算,320,000x328.9千克,廣州糧食年產量則為105,248,000公斤,大於實際糧食產量5.5倍到6.6倍之多,由此可知一磅等於328.9千克的換算是錯誤的。無論如何,手稿中 pondo 所對應的數字與《大明官制》中“石”對應的數字完全一致,這意味着在羅明堅的換算系統中,一磅 (pondo) 等於一石。因此,漢譯最簡單的方法是將 pondo 轉換為石,如果一定要用“磅”做單位,則須解釋一磅即一石。“步”和“磅”在漢譯中貫穿始終,筆者一路讀來,深感“步”“步”驚心,“磅”“磅”沉重。
對羅明堅中國圖志的再思考
借此機會,筆者也想就羅明堅中國圖志的研究談一點個人淺見。汪前進從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手稿中殘葉〈遼東邊圖〉追蹤到《大明官制》,實為學術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可喜可賀。然而,誠如汪前進本人所言,在現有《大明官制》中,尚未發現與〈遼東邊圖》相同的圖頁,這意味着《大明官制》當有其他版本。在〈羅明堅地圖的中文資料來源〉一文中,畢戴克指出,明代最好、最著名的地圖是廣輿圖,而且利瑪竇在《中國劄記》中提到1579年印刷的一本書籍,其中有一百五十八省,二百四十七州,一千一百五十二縣;這當指1579年版廣輿圖,而羅明堅當參考過利瑪竇看過的該書。(11)那麼,有無可能存在1579年《大明官制》呢?如果能核實此事並從中找到與中文〈遼東邊圖〉相同的地圖,則可確認利瑪竇所說中國地理書籍,即《大明官制》而非《廣輿圖》。此外,就三種廣東省圖志而言,其中一些消息並不一致,那麼是否作者依據了不同版本的《大明官制》?換言之,在不同的《大明官制》版本中,是否存在着差異?這些都要求我們對《大明官制》進一步研究。另外,T3關於中國的綜述以及T9-10有關海南島和廣州附近島嶼的消息,均不見於《大明官制》,如果不僅僅限於耳聞,那麼羅明堅又是依據了甚麼中文資料?因此,即使已經證明羅明堅中國圖志的主要來源為《大明官制》,目前也不能排除羅明堅利用其它中文資料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對於羅馬檔案館所藏中國圖志手稿,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學界至今基本沿用了羅薩多定下的基調,即它們為羅明堅手稿,且為1606年製作。事實並非如此。首先,手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大部分無疑是羅明堅的作品,但其它一些手稿的筆跡明顯不同。譬如根據中文〈遼東邊圖〉繪製的T77遼東圖 (LIAUTUM),其字跡不是羅明堅的,而是出自另外一人之手;與此筆跡相同的還有T63南直隸 (NANCHIN) 地圖、T39山西省 (SCIANSII) 以及T4廣東省 (QUAMTUM) 地圖左上角有關距離的批註。此人是羅明堅繪製中國圖志的重要助手,而且在羅馬國家檔案館所藏手稿中有幾幅中文繪製的地圖,據此可以猜測此人或為羅明堅從中國帶回意大利的中國翻譯。另外,如前所述,T6、T12和T18的筆跡既非羅明堅,又非疑似中國翻譯,而且根據T12有關耶穌會士在華消息可判斷其寫作時間為1589年之前,那麼這些手稿是否出自利瑪竇之手?然而,這些手稿不似利瑪竇筆跡,那麼其作者究竟何許人也?其次,手稿並不僅僅限於1606年,如前所述,三種廣東省圖志出自三個年代,即1583年前,1583年至1589年之間和1606年。另外,手稿絕大部分為拉丁文,祇有T9-10為意大利文,這充分說明T9-10有別於其它手稿。T9-10文末提到羅明堅寫給總會長一份關於中國傳教的報告,而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收藏了羅明堅1598年後致總會長的報告書,由此可知T9-10作於1598年之後。因此,羅馬國家檔案館所藏中國圖志手稿,是多種手稿的混合物,其中有三種不同的字跡,而且可以確定四個不同的年代。
羅馬檔案館所藏中國圖志手稿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且不是羅明堅所繪中國圖志的全部。如前所述,羅馬版內容並非統統為羅馬國家檔案館的收藏,其中採用了少許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資料。事實上,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收藏着大量的羅明堅中國圖志手稿(見ARSI,Iap.Sin.101/II),學界尚未進行過認真的研究。該館另一宗卷中 (ARSI,Iap.Sin.,11 I) 還有一幅地圖,名為 Sinarum regni aliorumque regnorum et insularum i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o (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地圖),以及數頁相關手稿,手稿無疑出自羅明堅之手;手稿日期署為1583年,是目前可見最早的羅明堅中國圖志手稿。(12) 此外,羅馬國家圖書館有一藏品 (Ges.1276),在羅明堅用拉丁文撰寫的《天主實錄》(Vera et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Catechismi sinici paraphrasis) 前面,有數頁有關中國以及周邊國家的拉丁文手稿,它們不是《天主實錄》的組成部分,而是單獨的中國圖志,如同羅明堅本人在著名的《中國傳教報告書》中所寫道:“1590年12月羅明堅覲見教皇格里戈利奧十四世 (Gregorio XIV) 時,在拉丁文譯本《天主實錄》外,獻上一冊中國圖志 (un descrittione della Cina)。”(13) 同樣通過這份報告,可知羅明堅1588年返回歐洲時攜帶了多種中國圖志,而且在1596年還專門為羅馬學院繪製了一種精美的中國圖志。(14) 學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羅馬國家檔案館收藏的羅明堅手稿,對其它方面的有關材料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因此,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羅明堅中國圖志,可以說任重道遠。
【註】
(1) 《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年12月。
(2) 羅薩多主編《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羅馬,1993年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I.a cura di Eugenio Lo Sardo, Roma, 1993)。
(3) 汪前進〈羅明堅編繪《中國地圖集》所依據中文原始資料新探〉,《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4) 原文轉寫為“a civitate Sciau chin ad occidentem 240 li,m.66”,即廣州西至肇慶240里,66意大利里。筆者核對原文,發現“m.66”為“m.60”之誤。
(5) 筆者試譯:“首先,不加其它材料,單用其木便可造船,其葉片可作船帆,其菓實可為船舶壓倉;菓實呈核桃狀,類似於我們的杏子,可釀酒並由酒製醋。[⋯⋯]成千上萬這樣的菓實,通常作為重物載於船上,其汁供乘客解渴,是淡水的補充物。當它們非常鮮嫩時,因為非常甜,可取其汁為食物的佐料,也可製成軟乳酪 (gioncate),加糖後味道類似我們的白布丁(bianco magnar)。當它們乾燥時,則取其油,不但可以照明、調味食物或者像我們這樣炸食物,而且對於醫治創傷也非常有用。如前所述,其樹木可製木板與棟樑,用於建造房屋和船舶,而在樹木之中有某種硬木釘,用它們釘船,遠比鐵釘結實。”
(6) 筆者試譯:“一座叫做 Poushian (五指山?) 的山脈橫貫該島,山民至今多不歸順中國皇帝;儘管如此,他們與低地的居民和平相處並互通有無。”
(7) 筆者試譯:“臨近採蚌期間,派遣善泳者潛水,以探明何處珠蚌最多,然後在相應的海岸上建立稻草為屋頂的木屋村 (villa),直到採珠結束,其中必需品應有盡有。這些採珠人皆為當地居民。”
(8) 此譯不盡妥帖。譯文中“供奉”一詞的拉丁文對應詞為vocatur,意思是“被稱為”,故此句當譯為“腳下有月亮與龍者被稱為童貞”。
(9) 《羅明堅中國傳教報告》(Rel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missione della Cina del mese di Novembre 1577 sino all’anno 1591 del padre Ruggiero al nostro reverendo padre generale Claudio Acquaviva generale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ARSI, Iap.Sin., 101 I), 頁45v。
(10) 肇慶知府王泮婚後三十三年無子,結識耶穌會士後於1584年先有一女,繼而又生一子,利瑪竇在1586年致總會長函中寫道:“嶺西道一直想有兒子,今年終於快樂地生了一個。他要求我們對天主多加祈禱。我們贈送了一個聖母像,他放在家裡,非常崇拜。為此,肇慶城傳言,我們天主給他生了兒子。許多沒有生育的婦女去一個教徒家中,對我們送給他的一個聖母像禮拜並祈求生子,還要給他錢財。但這個天主教徒說,我們不為此斂財,他沒有接受錢財。”見《利瑪竇信函》(M.Ricci, Lettere, 1580-1609, Macerata 2001),頁123。
(11) 畢戴克〈羅明堅地圖的中文資料來源〉(Luciano Petech,“La fonte cinese delle carte del Ruggieri”),羅薩多主編《羅明堅中國地圖集》,頁41-44。利瑪竇關於1579年中國地理圖書的記載,見《利瑪竇資料》(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D’Elia,Roma, 1942-1949),頁14-15。
(12) 關於這一手稿的初步研究,見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與利瑪竇〉,《海國天涯 —— 羅明堅與來華耶穌會士》,澳門文化局,2013,頁129-136。
(13) 〈羅明堅中國傳教報告〉,頁71v。
(14) 〈羅明堅中國傳教報告〉,頁63v-74。1596年10月12日利瑪竇致 G.Fuligatti 函也指出:“中国圖志 (la descrittione della Cina) 通過許多途徑送到歐洲,但有許多錯誤。”(《利瑪竇信函》,頁326),可為多種中國圖志存在之佐證。
* 宋黎明,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史博士肄業 (1986-1988),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政治學院訪問學者 (1988-1990),2008年至今為南京大學特聘研究員,著有《神父的新裝 —— 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