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們就設定了自己的位置:作一個忠實的奴僕,努力使一個記憶、一份財富或者歷史的契機得以延續下去。秉承這一宗旨,我們滿懷犧牲精神去填載我們的方舟,猶如一位母親孕育她的胎兒。
如今,這一方舟裝滿了珍奇寶藏,它將會像一條江河,匯入未來的海洋。
在未來的世紀裡,當人們打開神奇的船艙,就會揀回一段清晰的記憶,一種秉性的脈絡,和在這世界的一隅把人們連接起來的鏈環。
這是一個心臟,一艘寶船,一支聖杯,或者一個裝滿使人新生的仙丹靈藥的寶匣。蒼穹佈滿星辰,閃耀着我們射向未來的光芒。
——《文化雜誌》第三十三期“封面說明”
澳門的《文化雜誌》從創刊至今已經一百期了。作為一份在澳門介紹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綜合與涵蓋歷史、文學、藝術、宗教學、人類學、考古學、地圖學和語言學等諸多學科的綜合性刊物,它做出了獨特的和不可替代的貢獻。從一開始起,直至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它一直堅持以世界主義的視野以及觀察文化交融的視窗作為定位,介紹東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扮演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作用。它的第一百期的出版,是值得廣大的讀者和雜誌的作者紀念和慶賀的。
《文化雜誌》中文版百期紀念《文化雜誌》在最初創刊的時候就已經聲明:這是一份研究學問的雜誌,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以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中葡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限政治見解。文章中的觀點和理論不代表本刊的立場。編輯部還指出,這是一份季刊,以葡文、中文和英文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會注意到這些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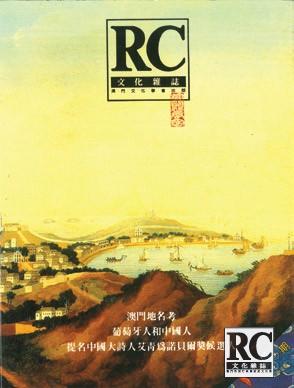
該雜誌最初由成立於1982年9月的澳門文化學會創辦,最初的《文化雜誌》內頁還刊印了“澳門文化學會”的感言:
澳門是一部傑作,兩國人民譜寫。作家、詩人、學者,妙筆生花,澳門因之生輝,青史長留。書,良師益友;書,智慧結晶。
第二期 (1987) 卷首刊登了當時澳門文化學會主席彭慕治 (Jorge Morbey) 的感言,表明了編輯者的態度。他指出歷史上的澳門,“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國當局的手上,由他們頒佈涉及澳門利益的規章制度,包括葡國人的利益在內。這個階段在澳門歷史上佔了三分之一的時期。耶穌會在澳門建立了遠東第一所大學,成為在中國宣傳西方文化的中心和向西方宣傳中國文化的傳播站,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重新恢復最古老、豐富和持久的傳統,為澳門的文化復興創造客觀的條件。”也就是說,編輯者認為,澳門回歸祖國將有助於文化的復興,長期以來專家學者從事不同文明比較研究得不到鼓勵的局面將會被改變,編輯者高興地看到,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前提之下,澳門自然而獨特的文化遺產將會得到尊重和保護。《文化雜誌》應該也必須對於澳門以及相關的文明以及文化研究做出貢獻。1990年第九期由馬若龍 (Carlos Marreiros) 撰寫的〈宗旨〉指出,他對於官龍耀 (Luís Sá Cunha) 被委任為主編感到欣慰和具有信心,並指出這份雜誌是“葡萄牙與中國的相互認識不斷加深及其歷史交匯連續性之不可替代的工具”,“在國際上代表着澳門的形象和反映澳門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歷史上的澳門,作為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一部分,曾經在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達到它的輝煌時期。在近代早期的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它作為葡萄牙人海外貿易活動和宗教活動的一個東方的基地,是葡萄牙海洋帝國連結世界各地的樞紐。在17世紀中葉以後,它在貿易上的全盛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的文化屬性仍然在發揮作用,同時繼續成為東西方各民族交融的熔爐。澳門本身發展的歷史及其研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將它與葡萄牙海洋帝國的其它部分聯繫起來觀察和研究,特別是以在今天後殖民化時代人們所普遍奉行的全球史的觀點以及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觀點加以審視,可能是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文化雜誌》從一開始就表明了這一立場。該雜誌中文版編輯者在
〈澳門的文化視野:世界與中國〉一文中指出:
所謂“澳門文化”,不應被簡單化地定義為某種歷史積澱的靜態的概念。“澳門文化”應該被理解成為一個由差異而交結並趨向整合的動態系統,它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 [⋯⋯] 尤其是人類在近代發生的具有全球意義的第二度浪潮的衝擊交匯打通了中國與整個世界的封閉隔絕,澳門在中西文化溝通方面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是至關緊要的。
第三十三期編者寫道,對於澳門的歷史研究,“不僅必須尋根究底地跟大明國的眾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聯繫起來作層層深入的追蹤考察,而且必須把自大航海時代產生的由東西方海上資本交往形成的‘真正的世界史’作為審視澳門全景關照的宏大背景。”
澳門文化交融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當地的東西方宗教的交融與和諧共存的現象。《文化雜誌》對於此一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予以充分的刊載。1999年第三十八期〈編者前言〉指出:
就澳門四百年文化的豐富性而言,堪稱“東方的聖地”,或者可以說,澳門是一個典型的東西方宗教文化的博覽城。澳門素有“東方的梵蒂岡”之稱,而基督教以澳門為傳教的據點,無論天主教和新教都遭遇到一個自身必須加以“中國化”的自我改造甚至脫胎換骨的嚴峻課題,否則,西方的上帝就不能被中國人的天地所容納。因此,一直關照着澳門街寧靜的媽祖娘娘被請進路環島的聖方濟各教堂並非沒有道理。媽祖在遠東的沿海早就是聖母瑪利亞的替身了。
澳門的宗教交融還表現在本土宗教之間。“明清以來,澳門的普濟禪院、媽閣廟以及蓮峰廟皆有曹洞宗傳人主持,三大寺廟裡皆供奉聖母娘娘也稱天妃娘娘的娘媽女神,形成中國佛教禪宗南傳澳門的最大特色。”1999年第三十九期〈編者前言〉再以豐富的想像力這樣寫道:
我們不妨設想,未來的澳門將作為東方獨特的一方宗教文化旅遊聖地,加強保護“西方宗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澳門原有的西來宗教文化形成的歷史文化遺產,更須強化對於本地所有的“東方宗教”包括佛教禪道和諸多民間信仰共同形成的歷史文化遺產的全面保護和重新開發。例如,以普濟禪院為依托,建立澳門禪宗文化博物館和研究院,並大力推動使之成為一個中國佛學南傳研究中心;在媽閣山或疊石塘山創建‘世界媽祖民間信俗博物館’,進而研究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中國海神文化的學術中心;在摩羅園範圍建立一座大型清真寺和五星級清真賓館,形成一個澳門伊斯蘭文化中心。
如果將文化理解成為被人們所認可的價值、信仰、種族的神話、記憶以及行為準則的話,宗教當然屬於文化的層面。澳門的宗教文化有它的獨到之處,葡萄牙人雖然將澳門視為“天主聖名之城”,但是澳門不同於果阿或者巴伊亞,它從來就不是以基督教文明單一顯現的城市,而是包容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巴哈伊教以及中國民間宗教神靈的薈萃之地。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在具有強烈宗教情感的葡萄牙人的影響之下,澳門的天主教會當然顯示出它的輝煌與壯麗的形象,但是由於獨特的歷史狀況,澳門也變成了中國宗教寺廟最好的庇護所。在不同的時期,許多內地的宗教人士也選擇此地作為避難所或者進而邁向國外的跳板。這些歷史的脈絡,在《文化雜誌》中有着清晰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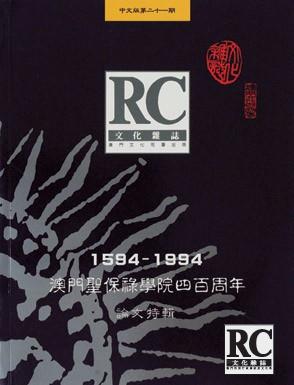
首先,在天主教研究方面,1994年中文版第廿一期刊出“1594-1994:澳門聖保祿學院四百週年論文特集”。官龍耀在〈編者前言〉指出:本期特刊是專門奉獻給耶穌會士的,“以此向他們表示在人類歷史上投入各種文化相關的運動從而令人讚歎地聚集了具有非凡人文價值的機構和個人”,“崇敬他們即意味着緬懷和紀念過去以及展望與預測未來。耶穌會在面對像澳門這樣的國際舞臺的貢獻始終與他們初創時刻緊密相連,就像幾個世紀以來創立並付諸實施的葡式亞洲市政管理方案一樣。耶穌會是由葡-亞商人和居民、廣東商人和掌權階層與耶穌會傳教理想之間的有效聯盟的港口城市利益相關的三角形的第三邊。在這三角鼎立的均勢中,耶穌會是東方社會的穩定力量和對內的巧妙庇護。”該集刊載有耶穌會士山度士 (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S. J.) 的〈遠東第一所大學〉,寇塞羅 (Gonçalo Couceiro)的〈澳門與耶穌會藝術在中國的發展〉,梅迪納(Juan Ruiz de Medina, S. J.) 的〈澳門大三巴教堂的建築師〉,馬愛德 (Edward Malatasta) 的《范利安 —— 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西比斯 (Joseph Sebes, S, J.) 的〈利瑪竇的前輩〉,陳阿瑟的〈中國的巴羅克:耶穌會士的聯繫〉,福斯 (Theodore N. Foss) 的〈西方解釋中國:耶穌會士製圖法〉以及戈爾維斯 (Noel Golver) 的〈南懷仁與北京欽天監〉等論文。1997年中文版第三十期再次以澳門聖保祿學院為主題出版了特刊,其中有馬愛德的〈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院〉,寇塞羅的〈澳門‘天主之母’會院教堂〉,維特克 (John W. Witek) 的〈着眼於日本:范禮安與澳門學院的開設〉,迭戈.結誠(Diogo Yuuki) 的〈澳門聖保祿學院與日本傳教會〉等。2006年是著名耶穌會士以及東亞傳教聖徒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誕生五百週年以及耶穌會東方視察員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逝世四百週年,《文化雜誌》於第六十四期設“聖方濟各沙勿略研究專題”,刊登了沙勿略的東方來信、他在印度以及東南亞的傳教活動、印度果阿的紀念活動以及沙勿略聖徒形象塑造的過程等專文;第六十六期 則為利瑪竇研究專輯。該雜誌在此以前和以後發表了眾多的有關耶穌會士在澳門、中國大陸、日本、越南、印度以及葡萄牙本國的歷史活動的極有價值的專論。
在佛教研究方面,清代的大汕大師的研究成果也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姜伯勤的〈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第十三、十四期),第三十八期又刊載了姜伯勤的〈澳門蓮峰廟與清初鼎湖山禪宗史〉以及〈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何健明〈略論清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 —— 以普濟禪院為主的個案研究〉以及〈竺摩法師與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特別是後一篇文章初步探討了竺摩法師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投身救國的事業。1939年他來到澳門的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主辦《覺音》,並與嶺南文人學士以及畫家交遊。姜伯勤另撰寫有〈澳門普濟禪院所藏大汕自畫像及大汕廣南航行與重修普濟禪院的關聯〉,譚世寶〈澳門三大古禪院歷史源流新探〉(見四十二期)。第七十三期是非常特別的,此期專門介紹竺摩法師及其傑出畫作,還發表了由柳蓮輯錄的〈竺摩法師自述及濠江遺稿鉤沉〉。編者稱:“竺摩十八歲進入閩南佛學院,得以親近太虛大師,濡染了一身禪化之般若智慧,修成一名去弊開悟自性超絕的模範青年法師。他不僅具備圓覺的智慧關照真理洞悉世事,而且用於在個體實踐和社會活動上有所承當。”
媽祖是澳門民間宗教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自然也是《文化雜誌》討論最多的內容。第四十八期刊載了2001年10月在澳門舉辦的“媽祖文化研討會”的許多論文,它們的作者是分別是魏美昌、吳幼雄、蔣維琰、許在全、汪征魯、石奕龍、莊景輝、莊國土、林美容、江瀅河等學者。
比較特別的還有華南沿海地區以及澳門的拜火教徒的研究。中文版第四十七期刊載了“巴斯人”(The Parsee) 在華南活動以及他們在澳門的墳場的調查。這兩篇文章分別是郭德炎的〈粵港澳三地文獻與巴斯在華史研究〉以及陳澤成的〈澳門白頭墳場 (瑣羅亞斯德教墓地) 的保護〉。瑣羅亞斯德教是流行於古代波斯以及中亞西亞的宗教,亦稱拜火教。6世紀時傳入中國,13世紀以後漸漸地絕跡了。“巴斯人”是指17世紀在印度孟買的的瑣羅亞斯德教徒,1870年代,他們隨着葡萄牙人從印度西海岸地區和孟買來到澳門以及華南沿海地區進行貿易活動,並把他們信仰的宗教再度傳入中國的土地。隨着英國人在香港的立足,他們逐漸將貿易活動遷到了香港。20世紀初以後,他們在澳門的行蹤就就逐漸地絕跡了。前文考察了“巴斯人”在華南以及香港的活動,介紹了位於廣州黃埔長洲島上巴斯山的巴斯人墓地;後一篇文章則披露了澳門的鮮為人知的“白頭墳場”。澳門人稱這個宗教為“白頭教”,大概因為該教的祭司以白布裹頭的緣故。考察報告披露“白頭墳場”內有十四座建於1900年以前的石棺式的墓塚。除了“巴斯人”以外,亞美尼亞人也在澳門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第五十期有施其樂 (Carl T. Smith) 的〈一位18世紀的澳門亞美尼亞富商〉,第五十五期又刊載了施其樂與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的〈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探討了澳門亞美尼亞人社團的活動。亞美尼亞曾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人以極強的生命力在全世界各地拓展其宗教和商業的活動,早在元朝時期,我國的泉州就有他們留下的足跡。以上的這些討論增加了人們對於澳門文化多面性的理解。
澳門在地理和文化上地處中國的邊陲,這可能是多種宗教能夠在這裡共存的原因之一。澳門一直提倡不同宗教的包容與共存,不僅顯示了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文化融合與宗教妥協,還證實了東西方宗教實踐的並存。它提供了一研究宗教文化的微觀世界,同時,這些宗教又與中國內地以及海外保持聯繫,展示出了廣闊的衍生研究的前景。這些特徵都在《文化雜誌》中得到了深入的展現。
美國的歷史學家布羅基 ( Liam Matthew Brockey) 指出:
葡萄牙也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美洲、非洲和亞洲的全球性的帝國,它所建立的殖民地城市不僅是聯繫帝國的樞紐,而且也是最初的具有全球化特徵的城市,它們使得貿易以及文化的網絡連成一片。這些世界主義的城市擁有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和訓練有素的權力機構,在不同的空間中以特殊的方式組織起來,對於整個帝國的構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包括澳門在內的歷史上的葡萄牙殖民地港口,在城市模式、都市制度、貿易體系、宗教組織、民族通婚、建築與繪畫形式、語言構成乃至烹飪文化上都有相似的地方。因此,以聯繫的觀點加以研究和比對是十分必要的。《文化雜誌》從創刊之初就已經體現了這一思想,並貫徹始終。早在第三期和第五期,該雜誌就已經刊載了維約(Selma Vieira Velho) 的〈葡萄牙航海家在東方沿海諸社會可能存在的影響〉;阿澤維多 (Carmo Azevedo) 的〈葡萄牙傳統民間宗教日在果阿〉,它們涉及葡萄牙人在印度以及東南亞社會的活動。
第二十二期是十分特別的“澳門與巴西”的專輯。官龍耀在〈編者前言〉中指出澳門由於“成為中介人的天責而不朽於歷史”,這是一種“一個世界同另一個世界相連接的運動中的一種使命,是過去也是未來的使命”。編者指出,巴西人是通過澳門認識中國的,植物的種籽、澳門瓷、漆器、彩釉、茶葉被運抵巴西,里約熱內盧則種植茶樹,澳門的土生家庭則移居巴西,由此促成了巴西的社會觀念的更新以及擴充,“這條北回歸線至南回歸線之路是環繞世界之路,老子的生命哲學、理想哲學、拉丁的創生哲學由此自由碰撞”。該期刊載了巴西考古學家莫羅(Fernanda de Camargo-Moro) 的〈澳門和巴西需要加強的古老對話〉、雷戈 (António da Silva Rego) 的〈澳門與巴西的直接關係:一個不可思議的夢想?(1717-1810)〉;莫拉 (Carlos Francisco Moura) 的〈19世紀上半葉澳門與巴西的關係〉;達斯內維斯 (João Alves das Neves) 的〈巴西人眼中的澳門〉;萊特(José Roberto Leite) 的〈宋呱與中國畫匠的里約熱內盧風景畫〉;蓋拉 (Joaquim A de Jesus Guerra)馬沙多.德.阿西斯的〈中國詩韻〉等等。
以長崎為中心的日本九州在歷史上也曾經是葡萄牙人重要的活動地點,從1540年代至1640年代,來到東方的葡萄牙人開闢了著名的果阿-麻六甲-澳門-長崎航線,葡萄牙人通過澳門不僅與日本九州保持密切的貿易聯繫,而且將天主教帶入當地,這段時期曾經被西方學者稱為“日本的基督教世紀”。在雜誌的五十一期、五十五期、五十七期、六十四期、八十三期和九十七期,分別發表了戚印平的〈加比丹.莫爾制度與早期澳門的若干問題〉,〈加比丹.莫爾及澳日定期商船的若干問題〉,〈加比丹.莫爾及其澳日貿易與耶穌會士的特殊關係〉,〈陸若漢其人其事〉,〈晚明海外生絲貿易 —— 以耶穌會參與澳日貿易為中心考察〉以及〈晚明澳門-日本貿易中的中國黃金〉諸文;又在六十四期、七十一期和八十七期發表了劉小珊的〈沙勿略早期日本開教活動考述〉,〈南蠻通辭對於葡日貿易的貢獻〉以及〈關於日本教區天主教主教的設立問題〉諸文。
葡萄牙在印度以果阿為中心的殖民地的歷史也是雜誌編者關注的對象,在第四十八期即刊載了布羅基 (Liam M. Brockey)〈穿越印度之路:天主教通往東亞的必經之路 (1570-1700)〉,在五十九期、六十四期、六十七期、七十二期、八十八期和九十一期上分別刊載了關於在印度的耶穌會士諾比利 (Robert de Nobili)、“耶穌會在南亞”研討會記錄、〈17世紀果阿的耶穌會教堂〉、〈果阿的宗教裁判所〉、〈果阿的好耶穌教堂〉、〈保存在果阿的沙勿略遺體〉等論文。這些研究論文雖然都不局限於澳門本身,但卻注重澳門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其它同類的葡萄牙殖民地的聯繫。
目前,中國的學術界已經着手開始從全球史的觀點研究世界歷史的進程。然而,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錢乘旦教授指出的那樣,真正能夠用全球史的觀點來做研究的並不是很多,人們對於全球史及其意義是陌生的和茫然的。澳門史的研究除了可以放在中國史以及葡萄牙海外領地史的背景之下加以研究之外,應該有“第三個背景,並且是更大的背景,即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一旦把澳門的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中進行觀察,就一定能夠發現一個新的澳門。換句話說:如果把澳門作為觀察世界的視窗,那麼世界歷史也會出現新的面孔。”(《總序:全球史與澳門》)這是富有遠見卓識的重要論述。在《文化雜誌》上發表的這些研究成果,應當可以視為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嘗試。
歷史上的澳門一直是華洋雜處的地方,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與自我身份的認同。與所有葡萄牙海外殖民地一樣,作為人數較少的葡萄牙殖民者,為了維護對於殖民地的統治和管理,必須有賴於與當地人合作與共存。與本地人 (尤其是本地婦女) 的通婚就成為包括澳門在內的這些葡萄牙殖民地城市的普遍的現象。這種泛種族的理念與行為產生了生活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交界面的所謂的土生葡人族群,他們是殖民地遺產的一部分。土生葡人在外貌與生活方式上介於歐亞兩大民族之間,兩者兼有的文化特徵往往使得他們的身份認同會發生迷茫與矛盾。但是,這恰恰是澳門文化最重要的基本特性之一。與此相伴的土生葡人的語言以及獨特的烹調風格 (即融合果阿、麻六甲和中國風味的澳門菜) 也都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文化雜誌》也刊載這方面的研究,如賈淵與陸凌梭的〈起源問題:澳門土生的家庭與族群性〉(第十五、十六期);阿馬羅 (Ana Maria Amaro) 的〈澳門的婦女:據16-19世紀旅行家的記載〉(第十七期) 等。1994年的第二十期是非常特別的“澳門土生葡人特輯:人類學、歷史和文化”。〈編者前言〉指出這一特定的人群的特別定義是“他們遠離自己的原居地,他們必須服從一個重新選擇的居住國家的陌生的環境和要求。他們永遠會表現出那種令人矚目的適應能力,保護他們那有別於葡萄牙文化和中國文化的自身的文化特徵,並重新恢復其獨一無二的和人格化了的遺傳基因 —— 種族融合的特質。”該期有潘日明 (Benjiamim Videira Pires) 的〈亞婆井 —— 尋找澳門的同一性〉,阿馬羅的〈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以及〈變遷中的土生社會〉,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的〈關於澳門土生人起源的傳說〉,巴塔亞 (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的〈澳門語: 歷史和現狀〉, 萊薩 (Almerindo Lessa) 的〈澳門人口:一個混合社會的起源和發展〉,佐治 (M. Da Graça Pacheco Jorge) 的〈澳門土生葡人的烹調術〉,彭慕治的〈澳門土生葡人:種族同一性的幾個側面〉,卡布拉爾 (João de Pina Cabral) 的〈澳門族群的構成〉等。第五十期刊載了鮑登 (C. R. Bawden) 的長文〈18世紀澳門葡語方言的漢語資料〉以及由奧涅爾 (Brian Juan O’Neill) 撰寫的與土生葡人問題相似的〈麻六甲葡人的多重特性〉;第五十二期中又刊出了巴塔婭的〈20世紀50年代澳門土生葡人口語遺存研究〉以及胡慧明的〈《澳門記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等論文。卡布拉爾指出,土生葡人毫無疑問是中國人,而且他們自己也強烈地感受到與中華民族的聯繫,但是他們自己個人和家庭的經歷、受教育的情況、習以為常的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四海為家的秉性、精通英語和葡萄牙語和熱衷於自由旅行的特性,又與一般的中國人有很大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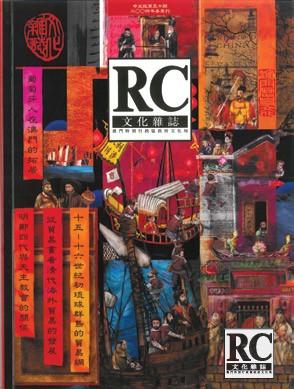
第三十五至三十七期為“澳門四百週年城市建築遺產”特輯,官龍耀指出這是為了迎接澳門回歸而作的特別回顧。〈編者的話〉指出,沒有澳門的建築遺產,就不存在所謂的澳門。澳門的建築遺產,以其與眾不同而成為其獨特身份的一種重要的象徵。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層面上,澳門自有它別具一格的城市建築輪廓,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
我們不要把那些倖存的建築僅僅當作過去時代的遺物和歷史見證,更重要的乃是要把它們看作是人類精神不朽的時代化身、人類不朽的活力體現。在那裡,遙遠的過去凝聚於更加遙遠的未來。思念既屬於過去,也屬於未來,因為思念也是憧憬,都屬於永恆。而尊重遺產是實現永久思念和無限憧憬的最佳方式之一。[⋯⋯] 澳門是一部屬於世界歷史的教科書,是人類大同提前實現的一個象徵,所有的差異都在這裡和諧地融為一體。澳門是一顆由中華民族和葡萄牙民族用智慧和勇氣凝孕出來的明珠寶貝。
在這三期中,刊載了葡萄牙建築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一批重要文章,包括科斯塔 (Maria de Lourdes Rodrigues Costa) 的〈澳門建築史〉,巴拉舒 (Carlos Baracho) 的〈澳門中世紀風格的形成過程〉,巴列托 (Luís Filipe Barreto) 的〈16-17世紀澳門的地位〉,費爾南德斯 ( José Manuel Fernandes) 的〈1820-1920年的澳門〉以及〈自本世紀20年代迄今的澳門〉等。在第四十八期刊載了克萊頓 (Cathryn Hope Clayton) 的〈論當代澳門特徵以及形成與城市變遷〉,馬若龍的〈澳門的多元化建築格局和城市佈局〉等。第四十六期的主題則是“‘城市文化遺產的保護:澳門視野’國際研討會專輯”。這是為澳門歷史城區申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世界歷史文化遺產”所做的準備。
2005年7月15日,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決議,“澳門歷史城區”正式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這是全體澳門居民的榮光,也是中華文化的光芒。《文化雜誌》第六十期出版特輯,刊載了2005年11月28日在北京舉行的頒證儀式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主席、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國家文物局局長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的致辭以及“澳門歷史城區”的介紹。該介紹最後指出:澳門歷史城區符合世界遺產的標準,“體現某一時段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人類價值以及表現手法在建築學或技術領域、在不朽的藝術創造、城鎮規劃等方面發展進程中的相互交流與影響價值的重要交替”,“包含一種文化傳統或依然存在或已經消失的文明的獨一無二或至少是不可多得的證明”,“是標示人類某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的某類建築物,或建築群體、或技術組合,或景觀的傑出例證”。
鼓勵藝術史的研究也是《文化雜誌》的重要的辦刊方向。為配合在澳門舉辦的“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精品展”,《文化雜誌》出版了“清代宮廷耶穌會士畫家特輯”(第四十二期),其中有聶崇正的〈清代宮廷繪畫制度探微〉以及〈郎世寧的非‘臣字款’畫〉,傅東光的〈西洋傳教士畫師與清代宮廷建築繪畫〉,吳夢麟的〈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在北京的文物遺存〉,余輝的〈清宮人物畫的自然主義傾向〉等論文。同期還刊載了當時任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的吳衛鳴為畫展寫的〈序〉,他特別提到耶穌會藝術的本質就是以視覺藝術為宗教服務:
(他們) 善於以繪畫和建築營造出類似舞臺景觀的圖式與空間,以便在禮儀以及崇拜過程中從視覺上刺激信徒的感官,並為靈修和默禱提供一種可見的視覺意向及記憶的場所。為達致上述的目標,一種由精確的數學關係來確立的視覺科學—— 透視法的理論與技術便得以提昇。
這段論述揭示了耶穌會藝術的本質。耶穌會是羅馬教會反宗教改革運動中最重要的新興修會。該會在葡萄牙海洋帝國擴張史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該會也極力提倡以視覺藝術作為推進宗教傳播工具。耶穌會在東方(印度、中國和日本)的藝術活動是其全球傳教區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早期的東亞,耶穌會在日本最初建立的神學院中設立了藝術學校,後來其部分成員因日本的禁教而遷往澳門 ,其中一些人又去了中國大陸的傳教區。在18世紀,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耶穌會藝術家從澳門進入北京的宮廷,他們在中國的藝術活動比日本的更為持久。在那段特殊時期,澳門本地不僅留下了包括“天主之母”教堂 (大三巴) 等標誌性的耶穌會宗教建築,也曾經在耶穌會藝術東漸進入大陸的道路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文化雜誌》還在不同的期刊特別探討“清初六大家之一”吳歷的生平、思想和藝術。這位出身在江南、具有極高的繪畫、音樂與詩歌稟賦的中國籍耶穌會士與澳門有着特別的緣分。他曾經於1680-1682年在澳門耶穌會的聖保祿學院學習天主教神學,其在澳門的生涯成為其個人生命的重要的經歷。澳門的文化界和藝術家以及許多中國學者對於他有着特殊的感情。在第七、八期合輯就刊載了章文欽的〈吳漁山的澳門詩〉;第四十三期 (2002年) 為“吳漁山傳世佳作與研究特輯”,刊載了章文欽的〈吳漁山的明遺民形象〉、〈吳漁山的傳世佳作〉, 〈吳漁山的繪畫與天學〉(第四十七期) 等論文。以後有關吳歷的研究不斷出現,成為探討吳歷生平與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園地。
本文無法一一列舉在《文化雜誌》上發表的所有的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就以上數種重要的特輯(宗教文化、全球史的研究、土生葡人族群與民族融合、建築歷史遺產和藝術史研究)就可以看出該雜誌所秉持的世界主義的視野和人文主義的情懷。它所揭示的澳門的文化的這種特質在新的歷史轉型時期也許會面臨挑戰,是否應當持守這些特質是處於轉型時期的當代的人們應該深思熟慮的。不過,筆者深信,這份雜誌本身所反映的時代氛圍、文化內涵以及中外學者的研究將是後來者研究歷史轉折時期澳門的重要素材,而這份雜誌編輯者的良苦用心以及奉獻精神也將會長久地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 顧衛民,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