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民族是不注意其文化傳統和交流的,凡是現實的都會合理地存在和發展,哲學作爲時代精神的精華,也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問題在於哲學自身的品德和客觀需要,需要爲哲學發展提供了源泉和必要的橋樑。
實現文化交流之橋形形色色,地域之橋有之。沒有與朝鮮毗臨之地利,儒學就不會那麼早(公元前三世紀)地在朝鮮傳播並再傳日本。沒有澳門這個近代文化交流窗口爲橋,很難想象中國哲學如此迅速地傳遍歐美。1517年葡人來華通商,澳門就成爲通往中華腹地的跳板。第一個來華的傳教士(意)羅明堅就是率先(1579)在澳門傳教的;世界上第一部《英華詞典》也是在澳門出版的(1817);第一個來華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澳門最早(辭海新版1839年不確,應爲1832年)辦起介紹中國的《澳門月報》(參見劉曼仙《歐美收集漢籍紀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澳門的津梁地位早已彪炳史冊。誠然橋的意義不完全是“第一”,“最早”,但“早”之本身其意義就非常巨大。
如果將地域爲橋擴大爲地理環境對文化交流、社會發展的影響就更加明顯。古雅典羅馬之商業,斯巴達之奴隸制、日本之“開放型社會”、威尼斯之較早產生資本主義,西藏之長期閉塞不能說完全是環境使然,但其作用之大是勿庸置疑的。
人之爲橋有之,人爲橋僅16世紀以來葡、西、荷、比、英、美成千上萬的傳教士擁向中國,前有意大利的利瑪竇(1552-1610),後有美國李桂白(1883年來華,1927年客死中國)。無論他們怎樣全副儒家打扮,手捧《論語》和《聖經》,但儒學仍是其傳教的最大障礙。兩刃相交不僅有衝撞的火花,更有結合融匯之成果。1582年利氏來華後,從廣州就讀,韶州傳教,南昌著述歷盡艱辛,才去北京叩擊宮門,費時28個春秋,譯著20餘種,終於建起了一座“人橋”,被譽爲“基督教的孔子”,“博學西儒”(見《蒿庵閑話》,《利瑪竇與中國》)。值得強調的是利氏之獨到處: 他作爲傳教士並不視儒學爲宗教,而看成哲學。他堅持了一條附儒、習儒、補儒、批儒的明智路線,才使其傳教活動取得了輝煌成就。尤其是他在華逝世後敕賜墓地、晉錄明史的殊榮。李桂白繼利氏之後,也特別注意華人感情,以儒釋耶,耶儒並宣,倡導耶儒“互相合作,互相敬愛”,因而成功地建起又一座“人橋”。
人爲橋,固然傳教士捷足先登,但大量學人志士的到來和開拓進取,則更廣泛地發揮了作用。(美)艾默生是鴉片戰爭後來華的,他悉心硏究四書五經,對儒學敬慕不已,稱“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是哲學上的華盛頓”,“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他對孔子的崇敬甚至到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地步(見張其昀《美國文化與中美關係》1957年台灣版第14、109頁)。本世紀20年代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了一爿書店進行文化交流,誠如其墓碑所書: “設書肆爲津梁,期文化之交流,生爲中華友,死爲中華土”。寓意更形象的是遵內山之囑特意將其墳墓修成橋狀以明志(《今晚報》1991.8.26)。
地爲橋,人爲橋,書店爲橋,關鍵在於條件及其同實際結合的狀況。利氏來華的最初十年成效甚微;李氏來華後由於某些不良意向,也曾影響過他們與華人的有效交往。之後,他們改進了工作,成效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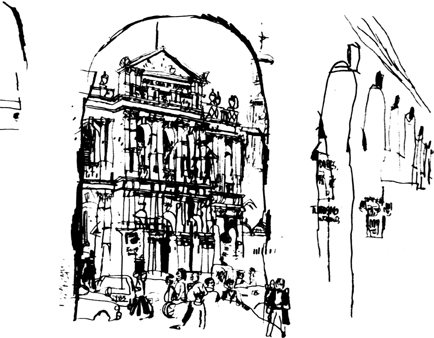 吳衛鳴速寫: 澳門仁慈堂
38×29cm·1990
吳衛鳴速寫: 澳門仁慈堂
38×29cm·1990
被西方知識界視爲古代科學著述典範的歐幾里得《原本》,兩千多年來幾乎被譯成所有國家的文字。公元1607年,明人徐光啓就與利瑪竇合譯出中文《幾何原本》前六卷。這是阿拉伯文字外的第一部東方文本,僅比西方近代科學發源地之一的荷蘭譯本晚一年。然而荷譯本用了11年就全部譯完,而中文全譯本竟拖延了整整250年,至晚淸才全部譯完。難道這一“爲用至廣”、“尤所急需”的世界名著要翻譯250年,僅僅是地緣或文字的原因,或是中國人缺乏幾何素養?無獨有偶,徐的同代人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遭遇更慘。不僅習者甚寡,竟曾絕跡海內三百年,後由淸末王星拱才從日本帶回而獲流傳(見《哲學硏究》1988年第2期第46頁)。
晚明,商品經濟雖步履唯艱,但仍有所前進,宋明理學漸趨衰退,而部份先進的知識分子則不屑空談玄理,講求實學,崇尚眞知,力主經世致用,科學民主思想潛生,滋長。除上述徐宋譯著外,尚有李時珍、徐霞客、李之藻等人的科技論著問世。稍後的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王船山等一代思想家、哲學家紛紛登上歷史舞台。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匡復明室失敗之後,或隱居鄉野,或開館講學,或著書立說以弘揚華夏文化造福國家,復興中華。
同時在狹隘(漢)民族優越感和嚴酷現實的交織下“西學中用”說泛起,重談體用成風。昔時的“體外無用,用外無體”(《華嚴疏經》卷23)“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氏文集》卷八)再受靑睞,於是“體用不二”、“立體開用”、“由用顯體”、“體用二分”紛至沓來。連崇禮西學的康熙皇帝也大言“西學貫源中法”(見淸梅文鼎《續學堂詩鈔》卷四)。這就使“中體西用”再成氣候;然而康熙的後繼者鎖國自縛,即便是乾嘉盛世,也無可挽回使中國走向衰落。至於所謂“同治中興”、“洋務運動”的“師夷”、“制夷”更是強弩之末。但當年徐光啓“吾迎難,難自衰微”的奮進精神並沒有完全泯滅,知識界的中堅仍在求索。像上述擱淺250年的《幾何原本》後九卷就在晚淸經李善蘭(1811-1882)與多方合作,歷經四個寒暑續譯大業方告功成(見金陵重刻《幾何原本》李善蘭新序)。
《幾何原本》250年成書的漫長歷程,體現了明淸知識分子憂患意識和務實精神。雖然歷史兜了個圈子,走了個之字形——開放、鎖國、再開放。這期間,實學、務實思潮與王道正統觀念,激烈地、艱難地進行著較量。
印度佛教傳入,走了比科技知識交流更漫長的融合道路;因爲儒學是難以逾越的障礙。於是出現了中國化佛教和儒佛道三足鼎立狀況;禪宗能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它這時破除印度佛教的神秘化,又能積極尋覓與中國儒學的交匯點密切相關(1),所以它能得以立足和發展。實際上它已成爲儒學的一個外翼——中國佛學。所謂“宋儒之學,入門皆由於禪”,正指此而言。儒佛交融可見一斑。
另外,傳爲中西文化交流美談的儒學曾對西方啓蒙學者進行過“啓蒙”,發人深思。法國啓蒙學派代表霍爾巴赫和伏爾泰,在鑽硏儒學之後,對孔子更加敬仰不已。霍氏認爲法國要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更有意思的是,他還爲法文增添了一個儒味十足的新詞——“德治”;伏氏將《趙氏孤兒》改編爲法國話劇《中國孤兒》,他平日還堅持對著孔子的掛像“朝夕禮拜”;法國雅各賓黨領袖羅伯斯庇爾也很崇拜孔子,在他起草的第一部資產階級人權宣言中,多處引用孔子的思想、格言。如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規定爲道德的最後界限。難怪不久前,當今科學界的泰斗們——部份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其“巴黎宣言”中稱: “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到2500年前的中國孔夫子那裡找機會。”(轉引自《社會》1991年第8期董啓元文)這是巧合?還是偉大思想的生命力的表現?
通過法國,儒學對德國也產生了影響。萊布尼茨在靑年時代就習儒,後來又通過法人白晉(康熙的老師,著有《康熙皇帝》等)的著作和書信硏討,特別是對從白晉處獲得的《易圖》的鑽硏,竟發現自己的“二進位數學”早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獲得了確證和運用! 這不僅促成了他的“二進位數學”和“單子論”的完善和發展,而且使他更加景慕中國文化。他曾呼吁彼得大帝俯允經過俄國開一條通往中國的歐亞大道(見(美)威·杜蘭《中國與遠東》第66頁)。他還直接影響其學生沃爾夫硏究儒學;沃氏於1721年在哈爾大學講授《中國實踐哲學》時,因對比儒耶哲學而觸怒當局,被宣判24小時離境,要麼就被絞死! 萊氏還影響過後來的康德和黑格爾。雖說康德黑格爾對儒學貶大於褒,但也從另一方面告訴人們,人爲橋的意義至關重大。總之,文化只有交流才能確定其存在價值;只有發展才能顯現其生命活力。實現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人橋;凡橋都要通過人來建造和發揮作用。中西文化交流淵遠流長,津梁靑春常住。
(1991.0.5)
〔注〕
(1)例如孔子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禪宗曰: “頓悟成佛”。孟子曰: “人皆可爲堯舜”;禪宗曰: “自性若佛”,“人皆可以成佛”。儒家講修齊治平;禪宗講心性善佛……
*韓學本,中國蘭州大舉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