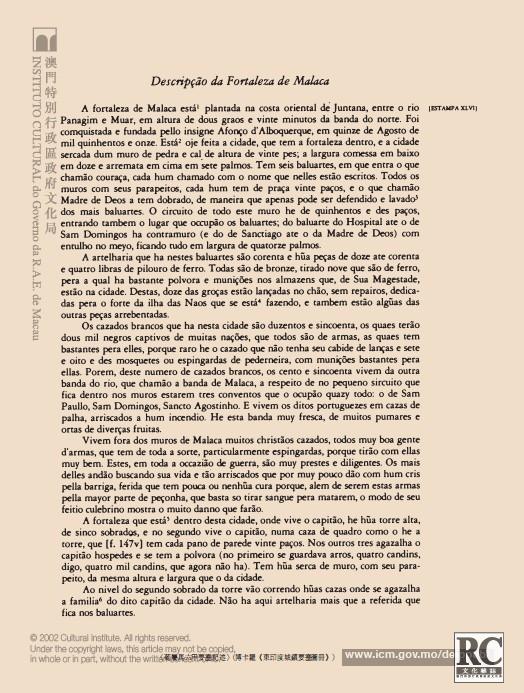
本文從滿剌加與中國、滿剌加與葡萄牙、中國與葡萄牙彼此之間圍繞滿剌加展開的博弈和對滿剌加歷史的反思等方面研究了滿剌加的興亡,從全球史的視角揭示葡萄牙佔領滿剌加後對東西方的影響,從而凸顯滿剌加之滅亡對全球史研究的價值。
滿剌加與中國
滿剌加 (1),今為馬來西亞馬六甲,地處馬六甲海峽要塞,是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那裡原本是一個 “沙鹵之地,氣候朝熱暮寒,田瘦榖薄,人少耕種”(2),僅居住着二三十個土著馬來人的荒僻漁村。滿剌加國的創建人拜里迷蘇剌 (Parameswara) ,原是巴領旁夏連特拉王朝的一個王子。“他最初是在巴領旁充當麻嗒巴歇的封臣。14世紀90年代,他擺脫了爪哇的霸權後,便轉到單馬錫(現今的新加坡)”(3),大約於1400年輾轉到馬來半島,開始以麻六甲為落腳點,建立港口貿易城市。此時,滿剌加尚稱不上是一個獨立的王國。 此處是暹羅王國的勢力範圍,“拉馬鐵善菩提 (1350-1369) 是第一位統治馬來邦國的暹羅國君”(4)。中文史料也證明了這一點。馬歡說:“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曰五嶼。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管轄,歲輸金四十両,否則差人征伐。”(5)
滿剌加國迅速崛起有三大原因:其一,與中國建立朝貢關係,確立了自身的地位,擺脫了暹羅的控制;其二,充分利用當時馬來半島貿易形勢的變化,抓住了歷史機遇;其三,充分利用了地理優勢。
首先是滿剌加與中國的關係。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於永樂元年 (1403) 十月派“尹慶使其地,賜以金織文綺、金帳幔諸物”(6)。拜里迷蘇剌抓住了這個機會。永樂三年 (1405) 九月,滿剌加的使者就跟隨尹慶到南京進行回訪,同年十月丁丑日,明成祖賜宴滿剌加使團。(7) 其使者“王慕義,願同中國列郡,歲効職貢,請封其山為一國之鎮”(8)。明成祖非常高興,將其“封為滿剌加國王”,並饋贈褚印、彩幣、襲衣、黃蓋等禮物。永樂三年十月壬午《明太宗實錄》又載錄了〈賜滿剌加鎮國山碑銘〉(9);永樂五年九月(1407) 滿剌加派使者隨鄭和來朝貢 (10)。
這裡有一個問題尚待研究,即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是否與滿剌加國建立了聯繫。以往中外學者一般認為,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與滿剌加沒有發生直接關係。中國與滿剌加關係的開端,是由尹慶完成的。尹慶出使滿剌加是在永樂元年(1403)十月,《明實錄》記載,永樂三年 (1405) 九月,尹慶使團返回,並帶有滿剌加使臣第一次來華,而在此前,這一年六月,永樂帝已下詔派遣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因此二者之間似乎聯繫不上,就此得出的結論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沒有到滿剌加。學者萬明認為鄭和很可能是同滿剌加使臣一起回國的,“鄭和作為正使,在第一次下西洋時齎詔賜印,‘建碑封城’於滿剌加。更何況中國史籍中沒有滿剌加首次派來使臣回國的記錄,因此,可以認為他們有可能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隊帶回國的。”(11)
筆者贊成萬明的觀點,並做以下論證 ——
第一, 永樂元年 (1403) 十月明成祖已經派尹慶去了滿剌加,說明當時朝中已經知道滿剌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樂三年 (1405) 六月己卯,“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王,賜金織、文綺、彩絹各有差”(12),具體的時間應是1405年6月27至7月25日 (13)。滿剌加使者跟隨尹慶到南京進行回訪的時間是永樂三年 (1405) 九月,應該說,鄭和並未見到滿剌加第一次來華朝貢的使臣。但這並不妨礙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作為正使,‘齎詔賜印’,‘建碑封城’”(14)。
第二, 《明太宗實錄》卷四七載:“永樂五年 (1407) 九月,爾 [滿] 剌加國王,遣使來朝,具陳王意。以謂:厥土協和,民康物阜,風俗淳熙,懷仁慕義,願同中國屬郡,超異要荒,永為甸服,歲歲貢賦。”從時間上看,“這應是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中國時隨來的滿剌加使者所上的奏陳”(15)。這樣便可以理解,如果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未去滿剌加國,何以帶滿剌加國使臣回國,並表示“歲歲朝貢”呢?因此,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去了滿剌加是可能的。
滿剌加來使以“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効職貢,請封其山為一國”(16)。明成祖依其所請,“封為國王,給以印綬”(17)。因為滿剌加原為暹羅屬國,“歲輸金絲十両”(18),明朝對滿剌加的嘉封引起暹羅的不滿,“發兵奪其所受朝廷印誥”(19)。拜里迷蘇剌於永樂五年 (1407) 九月遣使,請求明朝出面干預此事。朱棣認為滿剌加與暹羅“均受 (封) 朝廷,比肩而立”,都是獨立之國,暹羅不應“持強,拘其朝使,奪其印誥”,遂遣使責諭暹羅歸還“所受印誥,自今安分守禮,睦鄰保境,庶永享太平”(20)。永樂七年(1407), 鄭和第二次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送去〈賜滿剌加鎮國山碑銘〉。(21) 碑文云:
西南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
洗日沐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濃。
金花寶鈾生青紅,有國於此民俗雍。
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
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褐襲禮虔恭。
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
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險降在彼灣。
後天監視久彌隆,爾眾子孫萬福崇。(22)
皇帝讓鄭和帶去“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剌加國,是後暹羅國莫敢侵擾”(23)。費信《星槎勝覽‧滿剌加國》載:“永樂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齎捧詔敕,賜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為滿剌加國,其暹羅始不敢擾。”(24)
這是滿剌加與明朝的正式建交,滿剌加由此加入了明朝的朝貢體系。(25)
由此,滿剌加成為鄭和下西洋的重要中轉站。“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放在內。去各國船隻俱回到此取齊,打整番貨,裝載停當,等候南風正順,於五月中旬開洋回還。”(26) 中國和滿剌加的友好關係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1411-1432年的二十三年間,滿剌加三位國王先後五次訪問中國。據不完全統計,1405-1508年的一百多年間,滿剌加先後二十六次派出使者對明朝進行友好訪問,而在1403-1481年,不算鄭和寶船的經過停留訪問,明朝先後七次派出使者到滿剌加進行友好訪問。這樣的來往關係在明朝與東南亞各國中是極其少見的。
基於雙方的友好關係,鄭和七下西洋,雙方貿易往來極為頻繁。根據《明會典》的記載,滿剌加運來的貨物有四十餘種之多:犀角、象牙、玳瑁、瑪瑙珠、鶴頂、金母鶴頂、珊瑚樹、珊瑚珠、金鑲戒指、鸚鵡、黑猿、黑熊、白鹿、鎖服、撒哈剌、白芯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鰻、薔薇露、栀子花、烏爹泥、蘇合油、片腦、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樹香、木香、沒藥、阿魏、大楓子、烏木、蘇木、番錫、番鹽、黑小廝等。(27) 而中國的瓷器、絲綢、綾絹、紗羅、綵帛、錦綺、瓷器、藥材、鐵器、銅錢、茶葉、麝香、大黃等也運往滿剌加,進而轉運到阿拉伯世界。(28)
政治上的友好,經濟上的往來,促使去滿剌加的華人移民不斷增多。鄭和船隊每次都有兩萬多人,許多船員都是福建、廣州一帶的漁民,而鄭和返航時人員大減,除傷亡外,隨船出海的沿海居民滯留海外也不失為一個重要原因。據《廈門誌》載,萬曆時汶萊島就有不少華人居住,其中許多人是隨鄭和下西洋而留居下來的。《明史‧婆羅傳》記載:“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據學者估計,鄭和七次下西洋,僅隨他出海下西洋而滯留在南洋的,就有十萬多人。(29) 朝廷對所在國的態度 (即是否是友好國家),貿易是否繁榮 (即是否有商業利益),所在國的環境如何 (即是否利於經商),成為中國古代人們是否向外移民所考慮的三個主要問題。鄭和下西洋後,明朝與南洋諸國關係友好。永樂二十一年 (1423),出現了西洋古里、忽魯謨斯、錫蘭山、阿丹、祖法兒、剌撒、不剌哇、木骨都剌、柯枝、加異勒、溜山、南渤利、蘇門答剌、阿魯、滿剌加等十六國派遣使節一千二百人到明朝朝貢的盛況,大大推動了移民潮的到來。而滿剌加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四方來客,商品繁多,中國商品在那裡受到歡迎。可見那裡商業環境很好。所有這些都是明朝移民南洋諸國的重要原因。鄭和下西洋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向滿剌加等南洋國家的移民活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以鄭和下西洋為契機,滿剌加抓住了歷史性機遇,很快使其成為中國與非洲、阿拉伯世界貿易的交匯點。
其次是馬來半島貿易形勢的變化。馬來半島最初的強國是室利佛逝。室利佛逝是一個統稱,“用來指7至14世紀以蘇門答臘東南部為中心的連續存在的海上政權”(30)。唐昭宗天祐元年 (904) 以後的中國文獻改稱其為“三佛齊”或“佛齊”(31)。宋代室利佛逝與中國關係密切,在很長時間裡是馬來半島的強大政權。但到13世紀,室利佛逝逐漸走向衰落,1397年終於被興起於東爪哇的麻若巴歇王國所滅。麻若巴歇(Majapahit) 也稱作作麻喏八歇、滿者伯夷、門遮把逸。“麻若巴歇是借助元軍力量在新柯沙里王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是1293-1478年統治馬來群島絕大部分地區的跨島帝國,在印尼古代歷史上譜寫了輝煌燦爛的一頁。”(32) 麻諾巴歇是一個跨島統治的商業帝國,中央集權雖有一定的力量,但地方勢力與中央的關係並不穩定;同時因為貴族之間的爭鬥和矛盾,很快便四分五裂,麻諾巴歇所控制的爪哇逐步喪失了對麻六甲海峽貿易的控制權。1478年,淡目攻下了麻諾巴歇的首都,麻諾巴歇成了淡目的所屬國。“隨着爪哇北部海岸的多個穆斯林政權的出現和掌握主動權,麻喏巴歇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33)
在這樣的背景下,穿越麻六甲海峽的東西方的船隻和商人們希望在海峽有一個穩定的國家政權來控制海峽,保護航道。拜里迷蘇剌看準了這一點,迅速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大大鞏固了他在馬來半島的地位,從而很快在爪蛙之後使麻六甲成為海峽航運的中心。“當局任命了四名沙班答(syahbandar,港口官吏),每個沙班答各自代表一個不同的種族群體”,從而很好解決了貿易與族群之間的矛盾。滿剌加政權對商業的有效管理,使港口的經商環境大為優化,滿剌加逐步成為當時東南亞的重要港口。正如有學者所說:“[⋯⋯]15世紀中後期,麻六甲能夠迅速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轉口貿易港之一和東南亞最主要的貨物集散地,在國際貿易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除了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強盛的麻六甲帝國所統轄的廣袤地區的物產作為經濟基礎外,王國鼓勵吸引各國商人前來貿易、允許各種貨幣流通使用和管理港口的一整套有效的措施 (包括設置港務官、規定進出口稅、統一度量衡等) 及對來自各方商人的保護政策等等都是促成其繁盛的重要原因。”(34)
滿剌加以麻六甲海峽為中心,地跨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呈東南至西北走向,西北端接安達曼海進入印度洋,東南端接南中國海進入太平洋,全長108公里,海峽最寬處370公里,東南部最窄處約37公里。滿剌加國地處海峽中部最狹窄的地方,可為一劍鎖喉,對於由印度洋進入太平洋的船隊和由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船隊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咽喉要衝。“麻六甲位於中國和印度之同的狹小海道的匯合點上,港口有密佈紅樹林的沼澤地作力屏障,海道之深足以使大噸位船舶安全。[⋯⋯]由於擁有豐富而潔淨的水資源和木材供給,麻六甲是一個理想的國際貿易地點。在各種條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它天然地具有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雖然麻坡也是一處很有前途的貿易基地,但它比麻六甲更容易受到攻擊,而麻六甲有一座高聳的小山,從那裡可以俯瞰入海口。”(35) 滿剌加是一座天然良港,為歐洲、非洲與亞洲連接的關鍵點。
滿剌加在15世紀中期至16世紀初 (1434-1511) 已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國際貿易樞紐和南海貿易的中心。16世紀初曾到過滿剌加的葡萄牙人巴博沙 (Duarte Barbosa) 讚歎道:“這個麻六甲城是最富的商埠,有最多的批發商,艦船之多,貿易之盛,甲於全球。”(36)
滿剌加王國的崛起與強大,儘管有天時、地利與人和各種因素,但與中國友好關係的確立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鄭和七下西洋是一個偉大的壯舉。“這樣大規模的航海活動是人類歷史上的破天荒頭一次。明朝的船隊在葡萄牙人於1498年到達印度的近一個世紀之前就到達了印度洋地區,比西班牙的無敵船隊於1588年進攻英格蘭亦早了一百五十年。”(37) 鄭和七下西洋極大地擴大了明朝官方朝貢貿易活動,從而極大地帶動了滿剌加的商業貿易,使其迅速成一個繁盛的貿易中心,“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文明互動中心”。這種繁榮的局面持續了一個世紀,直至葡萄牙人東來才被打斷。(38)
滿剌加與葡萄牙
15世紀是伊比里亞半島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向外擴張的時期。這個被稱為“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是歐洲向世界擴張的開始。“亞洲的貿易額——無論是對內貿易還是對外貿易 —— 以及生產總量、人口和財富都比歐洲大得多,這使得歐洲人急於尋找到直接聯繫他們的途徑,尤其是1293年馬可波羅從中國返回後,他對東方財富神話般的描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39) 尋找契丹是百年大航海的靈魂。
葡萄牙沿着西非海岸不斷前進。1497年達‧伽瑪 (Vasco da Gama, 1469-1524) 率領的船隊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1502年他率領一支由二十艘帆船組成的巨大艦隊第二次進入卡利卡特,開始了對印度西南海岸的武力征服,並在柯欽建立代理站。葡萄牙認為:“這次偉大的航行歷時兩年以上,出發時一百七十人,回來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葡萄牙與東方建立了聯繫,那是真正的東方,而西班牙在大西洋彼岸所發現的不毛之地,未免相形見絀。”(40) 1504年意大利人亞歷山德羅‧佐治 (Alessandro Zorzi) 在其《印度遊記》中稱,葡萄牙船隊與來自中國的白人相遇。1505年葡王派遣唐弗朗西科‧德‧阿爾梅達 (Francisco d’Almeida) 出任葡印艦隊司令時,囑咐他“對滿剌加及尚未十分瞭解的地區”(41) 進行開發。1508年葡王詔令海軍將領狄奧戈‧德‧塞克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 遠征麻六甲,並指示他:“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 (Chijs) 的情況, 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麻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它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麻六甲或其它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炮?他們穿着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它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它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教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42)
1509年葡萄牙海軍將領狄奧戈‧德‧塞克拉率船五艘遠征,經柯欽及蘇門答臘 (Sumatra) 之亞齊 (Achin) 抵達麻六甲。他要求與麻六甲通商,並希望與麻六甲蘇端媽末 (Sultan Mahmud Shah) 簽訂友好通商條約。但當時麻六甲實際掌權者為莫泰希,蘇端媽末不過是一傀儡。而印度回教徒摩爾人欲壟斷麻六甲之商務,故挑唆莫泰希拒絕與葡人貿易。他們設宴請狄奧戈‧德‧塞克拉等上岸,望全獲葡人艦隊。然消息走漏,僅拘葡人二十餘名,焚葡船兩艘。狄奧戈‧德‧塞克拉率餘船返葡。狄奧戈‧德‧塞克拉在麻六甲港時,遇到了兩三艘中國船。他直接接觸了中國商人,並在中國船上吃了飯,還瞭解到了一些中國人的習俗。(43) 1510年2月6日,當時被滿剌加抓住並關在滿剌加監獄的盧伊‧德‧阿勞若 (Rui de Araújo) 從滿剌加監獄中偷偷發出了一封信,詳細介紹了滿剌加的貿易、航行以及防衛等情況。(44)
葡萄牙人瞭解了滿剌加的地理位置以後,就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用皮雷斯的話來說,她的“地位如此重要,獲利如此豐厚,以至於在我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同麻六甲相媲美。”(45) 佔領滿剌加已成為葡萄牙的戰略目標。
葡萄牙東方帝國的真正創建者是繼阿爾梅達後任印度總督的阿豐索‧德‧亞伯奎(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46) 1510年11月,亞伯奎佔領印度果阿,以此作為葡萄牙東方帝國的中心和控制印度洋貿易的據點。他的戰略計劃是:“首先攻佔麻六甲,控制東部入口;其次在紅海的入口佔領亞丁;最後奪取波斯灣的霍爾木茲。”1511年5月2日,一切準備就緒後,亞伯奎統領十九艘船隻和一千四百人的軍隊 (其中葡萄牙人八百名,印度和霍爾木茲士兵六百名),駛向麻六甲港。1511年7月1日薄暮時分,葡萄牙船隊駛入麻六甲港。馬哈茂德素丹深知來者不善,而此時墨泰希首相已被誅殺,他派人通知亞伯奎說,首相因對葡萄牙人滋生事端已伏法,可以商談。但亞伯奎置之不理,向麻六甲提出交還被押的葡萄牙人並用莫泰希的產業來賠償葡萄牙人損失的要求。 滿剌加使者要求首先簽訂一項和平條約,然後釋放俘虜。但亞伯奎堅持自己的條件,聲稱將不惜發動戰爭。在葡萄牙人對滿剌加人開戰前,他們也與停泊在港口中的華人進行接觸。華人告誡他們,攻打滿剌加並不容易,城中有兩萬多守兵。但亞伯奎決心開戰,他對他的部下說:“華人以為此次攻打難以成功。[⋯⋯] 為挽回面子,他決定在華人返回中國前攻打滿剌加城堡,為國王効勞。”(47)
7月7日,亞伯奎率船駛入港口,開炮摧毀岸上的房屋和停泊在港內的商船,搶走五艘中國商人的帆船。素丹被迫釋放俘虜,歸還葡萄牙人財物,並允諾劃出一塊地供葡萄牙人建立要塞。然而,亞伯奎並不善罷甘休,又提出更多新要求。素丹見和談無望,便調集戰象二十頭、兵士兩萬名準備應戰。麻六甲戰事一觸即發。(48)
7月24日拂曉,葡軍對麻六甲發動第一次總攻擊。葡軍在這天的戰鬥中付出了慘重代價,約有七十人被麻六甲軍隊的毒箭射傷,後來除一人外全部斃命。
葡軍經過十幾天的周密準備,於8月10日漲潮時再次發起總攻擊。亞伯奎用高於大橋的大帆船作為水上堡壘,船頭裝上擋箭板;另外兩艘船裝載重炮,用炮火從側翼掩護。他指揮士兵首先在城北登陸,接着又分兵一隊攻佔清真寺並奪取封鎖主要街道的圍柵。這些圍柵受到葡軍炮火的轟擊,迅即被佔領。素丹和王子頑強抵抗後被迫後撤。葡軍兵力少,無法分兵追擊,而是從船上搬下已備物資構築炮壘,將戰船開進停泊在橋頭兩側,鞏固佔領地帶。亞伯奎接着下令在城內大肆劫掠,對男女老幼格殺勿論,被害者不計其數。入夜,葡軍不斷炮轟城內,馬哈茂德素丹攜帶家眷和財寶逃出城外。 麻六甲陷落後,滿剌加國遂亡。(49)
《馬來紀年》也詳盡記載了滿剌加與葡萄牙的的戰鬥。第二十三章記述了葡萄牙人和滿剌加的第一次戰鬥。第三十四章記述了葡萄牙人第二次攻打滿剌加,“佛郎機駐果阿總督阿爾方梭·楚爾柏爾加爾基卸下總督職務後,回國謁見葡萄牙國王,請國王出兵進攻滿剌加。國王同意他的請求,撥給他四艘大型帆船及五艘長艇。他即駕船赴果阿,在果阿又加上三艘海船、八艘三桅船、四艘長艇及十六艘戰船,總計四十三艘船隻浩浩蕩蕩殺奔滿剌加來。”“滿剌加兵不能抵擋佛郎機兵的進攻,節節敗退。佛郎機兵隨後掩殺,追到王宮前。他們登上王殿,闖入宮內,滿剌加王蘇丹阿赫瑪特被迫離宮逃亡,宰相也由人用轎子抬走。”(50) 儘管《馬來紀事》是文學作品,但仍可以從中看到一些當時滿剌加人與葡萄牙人戰鬥的情況。
在葡萄牙人的研究著作中也提到了葡萄牙對滿剌加的佔領。《葡萄牙史》中說:“首先是麻六甲問題,1511年阿爾布克爾克(51) 出發到那裡,向這個膽敢襲擊洛佩斯‧德‧塞克拉的城市大興問罪之師,並迫使它變成葡萄牙的一個永久據點。阿爾布克爾克遭到猛烈的反抗,對麻六甲進攻好幾次才把它佔領下來。”《葡萄牙的發現》一書中也記錄了這場戰役:“那時的麻六甲是一座擁有近十萬人口的城市,由三萬馬來人和爪哇人守衛着。他們多數是優秀的戰士,擁有許多戰船、幾千門火炮,還有大象和蘸了毒液的武器。儘管該城首領及其謀士們都知道艦隊統帥的名聲及其業績,但看到兵力懸殊如此之大,仍拒絕了阿爾布克爾克提出的交出俘虜、進行賠償及割讓一塊土地來修建一座要塞的要求和建議。7月24日,阿爾布克爾克發動的第一次進攻沒有奏效,葡萄牙人祇得退回到戰船上。8月10日,艦隊統帥再次向該城發起攻擊,經過一個星期的鏖戰,終於攻克了該城。”(52) 遺憾的是,當代葡萄牙史的專家們雖然也認為他是一個為葡萄牙做出傑出貢獻和令人厭惡的罪行交織在一起的矛盾人物,但對其道德的批判顯然不夠,反而將其說成一個大無畏的英雄,這是不可以接受的。從今天的歷史觀來看,要看到西方在全球擴張中對東方民族所犯下的罪惡,應給予譴責。我們還應看到,雖然在東方民族的血泊中歷史也有了進步,但這種在宗教狂熱和自身國家經濟利益驅動下的殖民擴張在道德上應永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滿剌加:中國與葡萄牙的首次交鋒
滿剌加被葡萄牙佔領兩年後,1513年 (正德八年) 葡萄牙人若熱‧阿爾瓦雷斯 (Jorge Álvares)到達中國廣東珠江口的屯門,葡萄牙人開始進入中國。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六年後,1517年他們派出了一個訪問中國的使團。團長托梅‧皮雷斯 (Tomé Pires) 進入屯門後,稱自己是佛郎機(Feringis) 國王的特使。廣州的官員雖然不知佛郎機國為何方國家,但仍允許他們在此停留一段,待上報有結果後再議。
《明武宗實錄》對此有記載:“佛郎機國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並給勘合。廣東鎮巡等官以海南諸番無謂佛郎機者,況使者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下禮部議處。得旨:‘令諭還國,其方物給與之。’”(53) 使團在南京期間,因通事火者三亞“夤緣鎮守中貴”,賄賂武宗佞臣江彬,得到武宗皇帝召見。據葡萄牙文記載,明武宗甚至和皮雷斯一起下棋,並十分喜歡會幾種語言的火者三亞。(54)
中葡第一次外交並未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武宗返京後病故;二是通事火者三亞等人驕橫,見到禮部主事不行跪拜禮,引起眾怒;三是明朝官員得知葡萄牙吞併滿剌加之事。
滿剌加於正德十五年第一次具奏求救。《明武宗實錄》“正德十五年十二月”條有載:“宜候滿剌加使臣到日,令官譯詰佛郎機蕃使侵奪鄰國、擾害地方之故,奏請處置。”一年後正德皇上有旨:“會滿剌加國使者為昔英等,亦以貢至,請責諭諸國王,及遣將助兵復其國。[⋯⋯]滿剌加救援事宜,請下兵部議。既而兵部議事敕責佛郎機,令還滿剌加之地,諭暹羅諸夷以救患恤鄰之義。其巡海備倭等官,聞夷變不早奏聞,並宜逮問,上皆從之。”(55) 監察御史丘道隆得知這個消息後,要求祛除葡萄牙使臣。“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宜卻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剌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檄告諸蕃,聲罪致討。”(56)御史何鱉言:“佛郎機最兇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前歲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鬥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57)
正德十六年 (1521) 三月武宗駕崩,四月世宗嗣位,殺江彬、亞三,明廷對葡萄牙人的態度發生大的變化。最後使團被責令返回廣州,隨員都被關入廣州牢中。第一次中葡外交以失敗而告終。
圍繞着滿剌加被佔一事,中國和葡萄牙展開了一場外交博弈。歷史已告訴我們,在這場博弈中,明朝處於被動一方。
按照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維艾拉的記載,在葡萄牙人佔領了滿剌加以後,滿剌加流亡國王的兒子端‧穆罕墨德 (Tuan Mohammed) 到了北京,向皇帝傾訴了葡萄牙人在滿剌加的罪行。“這夥佛郎機強盜用大軍蠻橫無理地闖入麻六甲,侵佔土地,大肆破壞,荼毒生靈,洗劫眾人而把其他人投入牢獄。那些留在當地的人處於佛郎機統治之下。為此,麻六甲國王終日心驚膽戰 ,愁悒不寐。他攜帶那個中國國王賜予的印璽逃往賓坦 (Bentão),現在仍在該地。我的兄弟和親友們則逃往其他國家。那個現在正在中國土地上的葡萄牙國王的使臣是個騙子。他並不是抱着誠意前來,而是想騙中國。仰乞中國國王對憂心忡忡的麻六甲國王表示憐憫,特呈獻禮物,懇求得到救助和援軍,使他們得以收復失土。”(58) 但明朝反應遲鈍。(59)《明史》載:“後佛郎機強,舉兵侵奪其地,王蘇端媽末出奔,遣使告難。時世宗嗣位,敕責佛郎機,令還其故土。諭暹羅諸國救災恤鄰之義,迄無應者,滿剌加竟為所滅。”(60)明朝並未採取任何行動,至正德十六年 (1521)武宗死後才傳遺旨:“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61) 如有學者所說,這祇是“一具紙文”(62)。吳晗先生說:“明人不自強,不造浮海大舶,與佛郎機、荷蘭等國爭鋒於海上,而獨欲一紙敕諭令佛郎機還滿剌加地,令暹羅出兵,明人謬甚。”此言極是!雖然將葡萄牙使團人員扣留廣州獄中,但這些馬後炮已經解決不了滿剌加亡國後的實際問題。中葡圍繞着滿剌加國所展開的外交博弈,實際上以明朝失敗、葡萄牙人實際控制麻六甲海峽為最終結局。
歷史的反思
葡萄牙是歐洲一個小國;滿剌加是馬來半島的強國,亞洲大國中國的藩屬國。中國和葡萄牙圍繞着滿剌加的爭奪是中國與西方第一次利益衝突和交鋒。葡萄牙對滿剌加的佔領,中國與葡萄牙圍繞滿剌加展開的鬥爭的失敗,對全球的經濟和政治格局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葡萄牙對滿剌加國的佔領是其對歐洲香料市場爭奪的一個重大勝利。由於地理氣候原因,歐洲不產香料。一直以來歐洲人並不知香料的真正產地,祇是通過貿易間接獲得香料。自14世紀到葡萄牙佔據滿剌加以前,香料貿易的中心是威尼斯。14世紀末,香料佔威尼斯利凡特貿易總投資額的75%以上,有時甚至高達98%。但當葡萄牙人開闢了印度洋的新航線後,特別是佔據了滿剌加後,歐洲香料貿易的格局開始被打破。皮雷斯曾說過:“馬來商人說,上帝賜予帝汶檀香木,賜給班達肉豆蔻衣,賜給馬魯古丁香。除了這幾個地方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能夠獲得這些商品。”(63) 1513-1519年是葡萄牙香料貿易的鼎盛期,年均進口香料37,493擔 (quintal) ,1518年的進口量更多達48,062擔。同時,威尼斯的香料貿易幾近崩潰,1514年,連威尼斯自己也從里斯本購買香料。(64) 由於威尼斯的香料是從埃及進口的,葡萄牙新航線的發現和對滿剌加的佔領,導致了埃及人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於1508年派遣一支海軍遠征隊,以期幫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人從印度洋上趕出去。埃及人的努力失敗了。但是,於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繼續從事反對葡萄牙人的運動,在以後數十年中派出了好幾支艦隊。他們也沒有成功,香料依舊繞過好望角流向歐洲。(65) 對印度洋和東南亞香料的壟斷,使葡萄牙獲得了鉅額的利潤,我們可以從一些基本資料看到葡萄牙在香料上所獲得的巨大利益:“在1511年佔據東南亞著名港口麻六甲之前,葡萄牙人自己運抵歐洲的香料不及穆斯林船隊運輸量的四分之一。 從1513年到16世紀30年代,葡萄牙人時來運轉,平均每年轉運三十多噸的丁香和十噸的肉豆蔻,從而主宰了歐洲市場。”(66) 歷史的轉折就是從葡萄牙佔領滿剌加開始的,由此,“獲取香料並控制香料貿易的慾望促使葡萄牙創建了其‘胡椒帝國’(67),從而使葡萄牙一躍成為當時歐洲的強國,成為“一個在規模和性質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實體,標誌着全球貿易平衡和力量平衡開始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變”(68)。葡萄牙對滿剌加的佔領造就了這個海上帝國的興起。
其次,葡萄牙對滿剌加的佔領是其進入東方市場的關鍵一役。
葡萄牙人佔據滿剌加後很快就與中國建立了貿易關係。對中國來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自己的商品直接賣給歐洲人,而不再經過中間商人的盤剝,但實際上葡萄牙人從中國買來的貨物很少運回本國。因為他們在返回印度洋時,會在印度洋國家把中國的貨物賣掉,獲得利潤,再裝上南亞的香料和貨物回到歐洲。同時,他們開始利用滿剌加這個據點把東南亞的胡椒運到中國。意大利人安德雷‧科薩里曾說過:“將香料載往中國所獲得的利潤與載往葡萄牙所獲得的利潤同樣多。”(69) 葡萄牙人將來自蘇門答臘、馬拉巴爾、北大年等地的胡椒、坎貝藥材、鴉片、五倍子、藏紅花等運往中國,開始壟斷中國與南洋各國的貿易。
與此同時,當葡萄牙人在澳門站穩腳跟以後,他們充分利用了明朝當時因為防止海盜而禁止中國人出海的法令,使其成為東亞內部貿易的中轉者,直接參與到東亞內部的貿易體系中來。由此,澳門成為馬尼拉、日本、朝鮮、東南亞的貿易中心。澳門— 日本是當時利潤最大的一條貿易航線 (70)。澳門— 馬尼拉同樣是葡萄牙所控制的利潤很高的航線,“1634-1637年間,澳門-馬尼拉貿易利潤約為澳門海外貿易的50%”(71)。葡萄牙充分利用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制度與文化差異,將其貿易形式發展成極為複雜的形式,並從中獲得鉅額利潤。如學者所說,葡萄牙人以澳門為基地,充分利用了亞洲內部複雜的貿易網絡,每年4-5月葡萄牙人將佛蘭芒鐘、葡萄酒、印度的棉布等運到印度的柯欽,在柯欽換得香料和寶石,然後將這些南亞的貨物運至麻六甲,賣掉棉布等商品後買來東南亞的胡椒、丁香、肉豆蔻、蘇木、檀香、沉香、樟腦等,一路順風到達到澳門後用東南亞的香料換取中國絲綢。待到第二年6-8月,乘着西南季風前往日本,在那裡賣掉中國的絲綢換來中國奇缺的白銀。10-11月初乘東北季風再從日本返航澳門,賣掉白銀後可得兩三倍的利潤。然後,在澳門這個葡萄牙人臨時的據點滯留數月後,滿載中國的絲綢、麝香等返回南亞。歸途中,葡萄牙人將丁香賣給印度,滿載中國貨物和南亞香料返回歐洲。
葡萄牙人充分地利用了亞洲內部的貿易體系,充分利用其獨家掌握的通向中國的航道,發了一百多年的橫財,使其成為歐洲當時的第一強國。
最後,葡萄牙對滿剌加的佔領是中國朝貢體系瓦解的開始。
朝貢貿易是中國歷代王朝遵從儒家傳統文化處理對外關係的一種行為方式,具有較強的倫理性。從思想上講,“夷夏之辨”是朝貢制度建立的理論前提;從政治上講,“天下共主”是朝貢制度的政治追求;從文化上講,“禮治德化”是朝貢制度的基本目的;從經濟上講,“厚往薄來”是朝貢制度的重要方法。朝貢制度是一種和平主義的國際關係設計。從歷史上看,國家之間的關係大體有三種形式:軍事征服、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朝貢制度即是通過經濟貿易和文化傳播形成國家之間的和諧關係。儘管朝貢國在形式上與中國是宗藩關係,但實際上各國仍保留自己完整的國家機構,也不會受到中國的干預。因此,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利己主義原則相比,中國的朝貢制度具有道德的高度和濃重的倫理色彩。費正清曾說:“納貢的地位就是給外國人在特定條件下的經商權,使皇帝對外國朝貢者的權威合法化。但是這並非附庸關係,也並不表示要求清朝保護。”(72)
不能將朝貢體系僅僅看成一種政治關係;它是中華帝國與外部政治與經濟關係的一個完整體系。也不能僅僅將朝貢體系看成官方單一的行為;它同時包含着官方和民間兩種貿易內容。“島夷朝貢,不過利於互市賜予,豈真慕義而來。”(73) 而對於海外諸國來說,“雖云修貢,實則慕利”(74)。“朝貢貿易本身帶有互通有無的互市貿易過程。私人貿易不僅在會同館中是存在的,而且在官方遠航的海外貿易中也是存在的。”(75)
鄭和下西洋的偉大意義在於,通過官方和民間的貿易,中國和亞洲、非洲各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貿易體系。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後對朝貢貿易體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他們充分利用這個貿易體系;另一方面又逐步蠶食和瓦解了朝貢國與中國的關係。
首先,不要誇大葡萄牙在亞洲貿易體系中的建設性作用。有些學者認為,在葡萄牙人進入亞洲之前,亞洲沒有現代國際貿易體系,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後,中國的朝貢貿易基本上就解體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貿易體系。隨着鄭和下西洋的停止,亞洲內部舊有的貿易系統也逐步停止了。
這種觀點有兩個問題。第一,在葡萄牙人來亞洲以前亞洲已經存在一個龐大的貿易體系。從西元1000年到1500年,印度洋一直是全球貿易的中心,阿拉伯商人掌握着從東非到紅海口、波斯灣以及印度西海岸的貿易,印度商人控制着從錫蘭到孟加拉灣再到東南亞的貿易,而中國人控制着從中國到印尼和麻六甲海峽的南中國海貿易。美國學者羅伯特‧B‧馬克斯 (Robert B. Marks)認為:“四大文明和經濟實力中心為印度洋貿易提供了原動力:伊斯蘭教的中近東、印度教的印度、中國、印尼或香料群島。中國人把製造品—— 其中特別是絲綢、瓷器、鐵器、銅器 —— 運到麻六甲,換取香料、新異食品、珍珠、棉織品及白銀帶回中國。印度人運來棉織品換回香料。印度出口棉紡織品和其它製造品到中東和非洲東部,其中一些紡織品還遠達非洲西部。從非洲和阿拉伯人那裡,印度人得到棕櫚油、可可、花生和貴金屬。[⋯⋯] 這種巨大的全球貿易的引擎主要是中國和印度。”(76) 亞洲與非洲之間的貿易體係一直就存在,並非葡萄牙人帶來的,鄭和七下西洋證明了這一點,滿剌加國的興起與繁榮也證明了這一點。按照濱下武志的看法,亞洲內部以朝貢體制為特徵的貿易圈一直是很活躍的,直到鴉片戰爭前都是主導型的貿易體制。“自14、15世紀以來,亞洲區域內的貿易在逐漸擴大,存在着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貿易圈,及以此兩個貿易圈為中軸,中間夾以幾個貿易中轉港的亞洲區域內的亞洲貿易圈。歐美各國為尋求亞洲的特產品,攜帶着白銀也加入到這個貿易圈中來,並在此加入的過程中與亞洲既存的貿易圈發生關係,英、印、中三角間貿易關係就是其表現之一。”(77)
第二, 葡萄牙人進入亞洲後並沒有帶來新的貿易體系。
無論葡萄牙人在佔領滿剌加之前還是之後,他們不過是充分利用了亞洲內部已經存在的貿易體系而已。“就亞洲貿易而言,建立在戰爭、強制和暴力之上的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根本就不是甚麼經濟上‘高度發達’的階段。傳統的貿易結構儘管遭到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爆發的宗教戰爭的嚴重破壞,但依然如故。這一時期的貿易額並沒有甚麼值得一提的增長。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的貿易和經濟管理方式同亞洲貿易和亞洲經濟管理方式一個樣 [⋯⋯] 葡萄牙殖民統治時期因而並未向東南亞的貿易帶入甚麼新鮮玩藝兒。”貢‧佛蘭克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證明了這一點。18世紀前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主車軸,“歐洲諸國對亞洲的滲透,特別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滲透,其過程是為歐洲諸國謀求所需的亞洲產品,通過進入亞洲區域內的貿易而獲取了最初的可能。也就是說,在此不是以西方的產品和亞洲的產品進行直接的交換,西方要麼將白銀運來,要麼利用在亞洲區域內進行貿易的所得再購買亞洲產品。”(78)
所以,認為葡萄牙佔領滿剌加後建立了一個新的貿易體系,取代了朝貢貿易體系的看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其次,不能忽視葡萄牙佔領滿剌加後對朝貢體系的瓦解作用。葡萄牙以武力佔領了滿剌加,當時能夠制止葡萄牙這種行為的祇有中國,但明朝沒有採取實際行動制止葡萄牙這種野蠻行為。這是當時明朝自身衰落的表現,同時亦說明,雖然中國通過鄭和七下西洋成功地在東南亞建立起朝貢體系,有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但這種新秩序必須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海上武裝力量和殖民制度的支撐,是缺乏競爭威力的,一旦受到西歐殖民勢力的強有力的挑戰,則顯露出一籌莫展的窘態”(79)。
中國和葡萄牙圍繞滿剌加展開的博弈,實質上反映了兩種國家關係理論與實踐的差別與鬥爭。一種是中國的朝貢體制。這是一種具有理想主義和濃厚倫理色彩的國際關係設計,以“天下共主”的理想國際社會秩序為目標,而“非有意於臣服之也”。(80)一種是葡萄牙的武力征服的形式。這是一種完全站在自身國家利益之上以強權奴役、欺辱、佔領、剝削弱小國家的殖民主義的設計。當中國缺乏強大的國力來維護這個朝貢體系時,葡萄牙的殖民主義體系就佔了上風。《明會典》所載六十三個朝貢國,有三分之二以上位於滿剌加以西。明王朝一旦失去滿剌加,意味着朝貢體系不僅被打破,而且面臨着根本上動搖和瓦解的危險。歷史證明了這一點。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就控制了麻六甲海峽,同時也確立了其在東南亞的海上霸權地位。葡萄牙的霸權使那些原為中國朝貢國的各國紛紛放棄向明廷朝貢,轉而承認葡萄牙的霸權。“在佔領滿剌加的最初幾年裡,就有彭亨(Pahang)、監篦(Campar)和英德拉基里 (Indragiri) 成為葡萄牙的朝貢國,米南加保 (Menangkabau)、阿魯(Aru)、巴塞 (Pase) 和勃固 (Pegu) 成為友好的屬國,暹羅成為友好的國家,還有馬魯古、爪哇的革兒昔(Grisee)、杜板(Tuban)、Sidayu、泗水(Surabaya)、巽他 (Sunda) 和渤泥 (Brunei)都向葡萄牙人表示臣服。”(81) 中國與這些朝貢國的關係開始疏遠與終結,葡萄牙在政治上樹立了自己的霸權。
但又要看到葡萄牙此時並未建立新的貿易體系,祇是充分利用明朝原有的朝貢體系和亞洲內部早已存在的貿易網絡。朝貢體系的政治和經濟一體的結構,在葡萄牙佔領滿剌加後開始逐步解體,明王朝的對外關係中政治和經濟開始分離,經濟上允許葡萄牙合法地在亞洲貿易體系內活動,政治上則逐步失去了對朝貢國的保護,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明王朝建立的朝貢制度。英國歷史學家D.G.E.霍爾在《東南亞史》一書中說:“亞洲感覺到歐洲人統治的威脅是從1511年(東南亞的麻六甲被葡萄牙人侵佔)開始的。”這無疑是正確的。1511年葡萄牙佔領滿剌加無論對世界還是對中國都是一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滿剌加的淪陷,意味着西方與東方的角力中佔了上風。葡人據居澳門,象徵着西方在東方建立了侵略參透的橋頭堡,預示了中國不久將世界政治經濟中心讓位與西方。”(82)
【註】
(1) 滿剌加 (Malacca),馬來文作“Malaka”,即今日之馬來西亞。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鄭和航海圖》、黃衷《海語》也稱滿剌加,陳倫炯《海國見聞錄》稱麻利甲,謝清高《海錄》稱馬六呷,張燮《東西洋考》稱麻六甲,《皇清職貢圖》稱麻六甲。許雲樵翻譯《馬來紀年》時叫滿利加。關於滿剌加的歷史記載,西方學者主要依靠《馬來紀年》和葡萄牙人皮雷斯 (Tomé Pires) 的《東方誌》(Suma Oriental,又稱《東方國家敍事全集》),西方學者完全不知中國這些重要的歷史文獻。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學者的中文研究論文和著作至今尚未被西方學術界所重視。參閱芭芭拉‧沃森等著、黃秋迪譯《馬來西亞史》,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10年。
(2) 《贏涯勝覽‧滿剌加國》。
(3) (新) 尼古拉‧塔林主編、賀聖達等譯《劍橋東南亞史》,第一卷,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3。
(4) 吳迪著、陳禮頌譯《暹羅史》,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78。
(5) 馬歡《瀛涯勝覽》,商務印書館校註本。
(6) 《明史》卷325。
(7) 《明太祖實錄》卷47。
(8) 《明史》卷325。
(9) 《明太宗實錄》卷47。
(10) 參閱萬明〈鄭和與滿剌加:一個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11) 參閱萬明〈鄭和與滿剌加:一個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12) 《明太宗實錄》,卷43。
(13) 伯希和:《鄭和下西洋考》,中華書局1955年,頁28。萬明認為“關於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出發時間史載闕如 ”。看來並非如此。
(14) 史書對究竟是鄭和第一次西洋還是第三次下西洋到滿剌加,記載並不一致。《西洋朝貢典錄》:“永樂初,韶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名滿剌加國。”《殊域周諮錄》:“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剌使奉金葉表文朝貢,賜王彩緞襲衣。七年,明中官鄭和等持詔封為滿剌加國王。”《西洋朝貢典錄》的記載可以理解為鄭和在尹慶永樂元年出使滿剌加後,接着又作為正使,在第一次下西洋時去了滿剌加。但《西洋朝貢典錄》則可以理解為鄭和第一次去滿剌加是永樂七年。《星搓勝覽》記述與《西洋朝貢典錄》一致。
(15) 鄭永常:《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臺灣稻鄉出版社,2011年,頁160。
(16) 《明史》,卷325。
(17) 《明太宗實錄》卷46,“永樂三年九月癸卯”。
(18) 《西洋番國誌》,中華書局,2000年,頁15。
(19) 《明太宗永樂實錄》卷53,《馬來紀年》頁102-105,記載滿剌加和暹羅之間的戰爭。(馬)敦‧斯利‧拉囊著、黃元煥譯,學林書局,2004年。
(20) 《明太宗永樂實錄》卷60。
(21) 鄭永常在這裡將鄭和第二次下西洋的時間和目的都講清楚了,也說明了〈賜滿剌加鎮國山碑銘〉是鄭和第二次下西洋帶去的。參閱《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臺灣稻鄉出版社,2011年,頁171。
(22)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六‧滿剌加〉。
(23) 《贏涯勝覽‧滿剌加國》。
(24) 《西洋番國誌‧滿剌加國》:“主國封王,建豎碑。”《東西洋考‧麻六甲》:“從此不復隸暹羅矣。”參閱《馬來紀年》頁132-133。
(25) 王賡武先生指出:“麻六甲是接受永樂皇帝碑銘的第一個海外國家,這一事實是突出的。” 王賡武著,姚楠編《東南亞與華人 ——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頁88。
(26) (明) 馬歡原著、萬明校註《明抄本‘瀛涯勝覽’校註》,海洋出版社,2005年,頁41。
(27) 《明會典》,卷105。
(28) 參閱余定邦〈明代中國與滿剌加(麻六甲)的友好關係〉,《世界歷史》,1979年第1期)。
(29) 參閱萬明〈鄭和下西洋與亞洲國際貿易網的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11月。
(30) (新) 尼古拉‧塔林主編、賀聖達等譯《劍橋東南亞史》,第一卷,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2。
(31) 梁志明等《東南亞古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52。
(32) 梁志明等《東南亞古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68。
(33) (新) 尼古拉‧塔林主編、賀聖達等譯《劍橋東南亞史》,第一卷,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7。
(34) 余思偉:〈麻六甲港在十五世紀的歷史作用〉,《世界歷史》,1983年6期。
(35) 芭芭拉‧沃森等著、黃秋迪譯《馬來西亞史》,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10年,頁44。
(36) 理查‧溫斯泰德: 《馬來亞史》,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109。
(37) 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224-225。
(38) 萬明:〈鄭和與滿剌加:一個世界文明互動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春之卷。
(39)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on Missions in China, The Macmilla Company, NY, 1929, p. 80.
(40) (44) (美) 查‧愛‧諾埃爾著、南京師範學院教育系翻譯《葡萄牙史》上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73年,頁123;頁132。
(41) 轉引自金國平 吳志良《鏡海縹緲》,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頁21。
(42) (43)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中華書局香港書局,1988年,頁36。
(45) 轉引自芭芭拉‧沃森等著 黃秋迪譯《馬來西亞史》,頁40,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10年,頁151,轉引自金國平吳志良《鏡海縹緲》頁23,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
(46) 如果按照葡萄牙漢文譯名,應為“阿豐索·德·阿爾布開克”但在《明史錄》、《明史》中有“亞伯奎”之稱,在這裡用了亞伯奎。參閱廖大柯〈“佛朗機黑番”籍貫考〉。
(47) 轉引自金國平〈1511年滿剌加淪陷對中華帝國的衝擊〉,金國平、吳志良《鏡海縹緲》頁24,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
(48) 關於滿剌加和葡萄牙人之戰參閱《馬來紀年》,頁271-279。
(49) 參閱梁志明主編《殖民主義史:東南亞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3-57。
(50) 《馬來紀事》,頁271-274。
(51) 就是上面提到的“阿豐索‧德‧亞伯奎 (Afonso de Albuquerque, 1453-1515)。
(52) (葡) 雅依梅‧科爾特桑《葡萄牙的發現》第五卷,頁1242,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7年。
(53) 《明武宗實錄》卷一五八,“正德十三年正月壬寅”。
(54) 廖大珂:〈滿剌加的陷落與中葡交涉〉,《南洋問題研究》,2003年第3期。
(55) (明)《世宗實錄》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已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08。
(56) (57) (60)《明史》卷325〈佛郎機〉。
(58) 張天澤: 《中葡早期通商史》, 中華書局香港書局,1988年,頁58-59。
(59) 《明世宗嘉靖實錄》
(61) (明)《武宗實錄》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頁3682。
(62) 廖大珂:〈滿剌加的陷落與中葡交涉〉,《南洋問題研究》,2003年,第3期。
(63) 轉引自 (澳) 安東尼‧瑞德著、孫來臣等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二卷〈擴張與危機〉,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
(64) 田汝英:〈葡萄牙與16世紀的亞歐香料貿易〉,《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
(65) (美) 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等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137。
(66) (澳) 安東尼‧瑞德著、孫來臣等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二卷《擴張與危機》,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6。
(67) A. R. Disney, Twilight of the Pepper Empire: PortugueseTrade in Southwest India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Manohar Publishers, 2010.
(68) 田汝英:〈葡萄牙與16世紀的亞歐香料貿易〉,《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3年1期。
(69) 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頁67。
(70) 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澳門史新編》第二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頁408-430。
(71) 羅利路 (Rui Lourido):〈16-18世紀的澳門貿易與社會〉,《澳門史新編》第二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頁402。
(72) 費正清等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44。
(73)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31,〈四裔八〉。
(74) 《正德大明會典》卷97,〈禮部〉五六“朝貢”二;卷98,〈禮部〉五七“朝貢”三。
(75) 萬明:〈鄭和下西洋與亞洲國際貿易網的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11月。
(76) 羅伯特‧B‧馬克斯:《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的述說》,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70。
(77)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0。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以“衝擊—反應”式來解釋中國近代的發展,將中國和亞洲祇是作為歐洲發展的一個階段來處理,亞洲近代以來沒有自身的動力,像沃爾斯坦所說,歐洲是近代經濟的中心,而亞洲祇是邊緣。這樣就過分強調了西方進入亞洲後的作用。
(78)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31。
(79) (81) 廖大珂:〈滿剌加的陷落與中葡交涉〉,《南洋問題研究》,2003年第3期。
(80) (明)《太祖實錄》卷37,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頁750。
(82) 金國平:〈1511年滿剌加淪陷對中華帝國的衝擊〉,金國平、吳志良《鏡海縹緲》,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頁32。
*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漢學》主編、國際中國文化研究學會會長、國際儒聯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