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 (Charles Ralph Boxer, 1904-2000) 乃有史以來研究葡人在歐洲海外擴張中發揮的作用及葡萄牙帝國的最為多產、最受敬重的非葡籍史學家,其一生從頭至尾幾近橫跨整個20世紀。查爾斯1904年生於英國一個海、陸軍之家,父親休‧博克塞 (Hugh Boxer)為林肯郡團軍官,一戰期間於西線陣亡。查爾斯因此自小由其澳大利亞籍的母親及其家族中的其他成員撫養成長。其外祖父收藏的一套根付(netsuke)象牙製品,令小查爾斯心醉神迷,激發起他對日本文化和歷史的終身興趣。
在追求其日本興趣時,查爾斯很快覺察到,葡人是與日本發生物質接觸的第一批歐洲人。不久,他就對葡萄牙本身及其在歐亞交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產生了濃厚興趣。1924年,為了閱讀原始文獻,他開始學習葡語。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加入日本學會,着手學習日語。約在1927年,他又開始認真學習荷蘭語,因為荷人是繼葡人於17世紀初葉到中葉被逐之後進入日本的第二批歐洲人。大約在此時期,查爾斯開始了兩大終身學術追求:一是收集有關葡萄牙及荷蘭帝國歷史的手稿與書籍,並最終使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圖書館之一;二是自其1925年對葡國的首訪起,認真營造一個廣泛的葡國與荷蘭學者聯繫網。(1)與此同時,在剛滿十九歲的1924年,他完成了桑赫斯特軍事學院的軍官訓練,被分配到父親的老部隊林肯郡團,授少尉軍銜,從此開始了二十餘年的軍旅生涯。
查爾斯‧博克塞從軍之後,先被派駐當時局勢相對平靜的北愛爾蘭,後又很快調往奧爾德肖特 (Aldershot) 一個時期。然而因為學術興趣之故,他申請參加語言官培訓,為此於1930年被派赴日本,隨第三十八奈良步兵聯隊接受軍官訓練,後又到名古屋士官學校進修數月,初步掌握了日語口語。1933年加入英國陸軍部情報處之前,他在亞洲進行了廣泛的旅行。1937年,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任駐港英軍指揮部情報官兼日語翻譯。香港的工作令其忙得不亦樂乎,在隨後的四年間,他因執行各種情報任務,在中國內地進行了廣泛的旅行。1941年12月7日,日軍進攻香港,在接下來的戰鬥中,博克塞試圖收聚一支潰散的印度守軍,身負重傷。1941年聖誕節前夕,殖民地香港投降,博克塞此後被囚三年半之久 [這一不快經歷在道利爾‧奧登 (Dauril Alden)所寫的傳記中有詳盡描述],但博克塞還是咬緊牙關相當堅強地挺了過來。關押結束後,他依舊無怨無悔地履行自己的職責。(2)
博克塞1941年12月遭日軍俘擄及關押的後果,便是其史學家生涯的突然中斷。在接下來的囚於香港及華南的三年半中,他的私人藏書及手稿被剝奪了,而且也無法與出版商聯繫,其學術活動因而暫停,當然也給他提供了一個評價此前所獲成果的機會。(3)
1926年9月至1941年12月間,博克塞發表了大約八十五篇學術論著,約兩個月一篇。這些作品幾乎全部涉及葡國及荷蘭的海洋與海外史,而且主要是期刊文章或合著書籍中的章節。許多著述援引了以前從未出版過的文獻,通常來自博克塞的個人收藏。但博克塞在同一時期還出版了兩部相當規模的譯著,均為由其親手譯成英語並詳加註釋的17世紀手稿。兩部譯著分別是《馬頓‧哈珀茨松‧特羅普航行日記》(The Journal of Maarten Harpertszoom Tromp) 和《雷伊‧佛雷爾‧德‧安德拉德評註》(The Commentaries of Ruy Freyre de Andrade)。作者均為17世紀的司令長官,前者乃荷蘭著名海軍上將,後者為葡國傑出海軍提督。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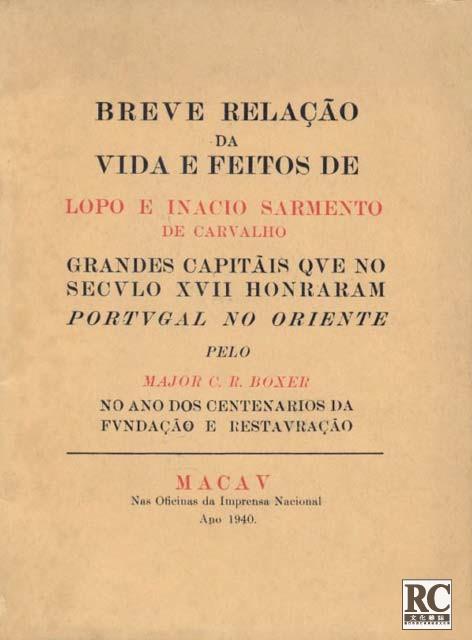
分別詳述了兩位作者在唐斯丘陵 (Downs) 與西班牙人的戰鬥以及在波斯灣對英國人和波斯人的海戰。博克塞親為兩部譯著撰寫長篇引言。
在港期間,博克塞另於澳門出版了兩本有相當篇幅的作品,頗值一提。第一本為《德羅佩與卡瓦略小傳》(Breve Relação da Vida e Feitos de Lopo e Inácio Sarmento de Carvalho),約70頁,1940年問世。該書重構了兩位17世紀居於澳門的貿易商父子的生活及功績,對與他們分別在捍衛澳門與柯欽 (Cochin) 時所展現的愛國主義和勇敢精神,博克塞認為應予以承認。第二本為《中國與日本的亞洲》(Ázia Sínica e Japónica),是一部18世紀中期的葡語手稿註釋本,共350頁,作者據說是若澤‧德‧熱穌‧瑪利亞修士 (José de Jesus Maria)。此書1941年於澳門出版,博克塞為之寫了引言。(4)
在博克塞學術生涯這一階段之末,其許多史學研究方法特徵,均已顯露無遺。首先,收集手稿書籍與寫史之間存在密切聯繫。這一特點也和其下筆之前窮盡相關原始資料、去偽存真的決心有關聯。憑藉自己超人的記憶,博克塞因而似乎毫無例外地掌握了多得令人咋舌的細節。其生動的文風,優雅、辛辣、引人入勝的文辭,是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又一優良特徵。此外,他還形成了一種超凡能力,能將講述的歷史人物描畫得有血有肉,活靈活現。
另一方面,在其歷史著述中,博克塞對思想前提或理論模式幾乎毫無興趣,其作品可以說無一例外地屬於經典的經驗主義的傳統範疇。此外,在其學術生涯的此一階段,他還未曾出版過一本正兒八經的專著,除非把前文所述的特羅普及佛雷爾手稿譯著算作專著。他也還未曾對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進步態度予以公開支持,這一支持後來成為其20世紀50年代或60年代初的特有標誌。在20-30年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列強的內部及彼此爭鬥。他尤其想論證的是,葡人與荷人在這些爭鬥中,既有付出也有收穫。為此,他辯稱,他們應當得到更多的尊敬,而不是如在英語國家傳統中的那樣屢遭貶斥。例如他在1935年的一章中寫道:“[英人] 很容易將他們那夥人[葡人] 斥為墮落的‘意佬’或受教士壓迫的教宗門徒 ,然而如此一來,我們便可悲地低估了我們的前輩所取得的成就。”他接着補充道:“葡人中雖不乏懦夫和雜種,但他們在印度也有‘付出與收穫相當的戰士和水兵’ 。”(5)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博克塞短暫恢復了其在香港的情報官職務;同年11月,他最終被撤往美國三藩市(San Francisco),從那裡前往東海岸,與髮妻離婚後迅速與1940年以來其在香港的實際搭檔、美國冒險家及作家“米基”‧項(‘Mickey’ Hahn) 結合。同年12月,經著名日本學家喬治‧森塞姆 (George Sansom) 推薦,他在遠東委員會日本辦事處謀得一職,並於該處追回了大部分1942年被日軍作為戰利品運回東京帝國博物館的私人藏書。
博克塞此時仍然期望能在遠東繼續自己的戎馬生涯,同時拾回自己的學術興趣。但事與願違。1947年,四十三歲的他在軍中服役約二十二年之後,戀戀不捨地辭去了心愛的職務,永遠結束了部隊生活。博克塞退役的癥結在於,軍方醫療部門認為他不適合長期駐紮遠東,因其左臂在香港保衛戰中受傷,處於半癱狀態。然而香港卻令其魂牽夢縈,一是因為他對該地的歷史抱有興趣,二是因為他在那裡建立了許多根基和關係。他堅決不願在英國的某張寫字檯後面無休止地辦公。(6)
與此同時,倫敦國王學院葡萄牙研究的卡蒙斯教授職位,卻幸運地空缺出來,博克塞應邀擔任該職。經過反覆權衡,他深信此機會千載難逢,於是決定改換門庭,接受國王學院的邀請,做一介平民。1947年10月,他就任卡蒙斯教職。對於一名從未受過正規學術訓練、且無大學文憑的業餘史學家來說,這絕對稱得上成就巨大。用休‧特雷弗-羅珀 (Hugh Trevor-Roper) 的話來說,博克塞無疑是“偉大的史學家都是業餘的”這句話的活證據。(7)
博克塞一到國王學院,便開始了其學術生涯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從1947年底始,到1967年止,歷時約二十年。毫無疑問,上述歲月是其作為歷史學家最為豐產的時期,許多重要作品均於此期寫成出版。二十年間,他總共發表130-140件作品,即不到兩月一件。儘管這一速度與其在香港淪陷前的第一學術階段達到的一樣,但根本的區別在於,他在國王學院出版了十五六本書。而且大都是專著,其中幾本很快成為經典。彷彿他對過去二十年積累於胸的海量細節之掌握、理解及詮釋技巧,如同火山熔岩,突然衝破地殼,噴薄而出。
除了一兩本例外,最明顯的莫過於《荷蘭的海上帝國,1600-1800》(1965)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博克塞50-60年代出版的著作完全或者主要聚焦於葡人的海外活動。(8) 在戰前的第一階段,他關注的主要是南亞、東亞及東南亞的發展,而在國王學院的那一時期,他筆下涵蓋的地域則更為寬廣。戰後他出

版的第一本書《遠東的貴族,1550-1770》(1948)(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實際上是由十五篇先前發表的文章及論文結集而成,因此仍未跳出原有的窠臼,或者說至多處於轉型時期。博克塞本人稱其為對澳門歷史“主要節點及階段”之研究,兼顧一些“特定人物”。(9) 他將本書題獻給其葡籍好友亞曼多‧科特桑和卡洛塔‧科特桑 (Armando and Carlota Cortesão) 夫婦,然而這一姿態很快就變得極具諷刺意味。
博克塞的下一本書《日本的基督教世紀,1549-1650》(1951)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就與之前的作品大相徑庭。該書權威地敍述了16及17世紀起初雄心勃勃、最後終於慘敗的日本基督教皈依運動。該運動在葡萄牙保教權的語境之下展開,主要是一場耶穌會的事業,儘管也有一些不受耶穌會士歡迎的其他教派的傳教士參加。博克塞在寫該書時,不僅查閱了大量葡語及歐洲語文獻,包括阿茹達宮圖書館及大英圖書館卷帙浩繁的耶穌會報告,還參考了相當數量的日語一二手相關資料。一批重要日語文獻被譯成英語後,收在附錄之內。著名日本學家、前美國駐日大使賴世和 (Edwin O.Reischauer) 稱,該書是“對日本史學研究的重大貢獻” 。(10)
繼《日本的基督教世紀》之後,博克塞首次認真地將其注意力轉向殖民地巴西,並一連寫下三本書。1952年刊行的第一本為《薩爾瓦多‧科雷亞‧德‧薩與巴西及安哥拉的爭奪,1602-1686》(Salvador Correia de Sá and the Struggle for Brazil and Angola 1602-1686),可以歸入半自傳類。緊接着出版的是《荷蘭人在巴西,1624-1654》(1957) (The Dutch in Brazil 1624-1654)。過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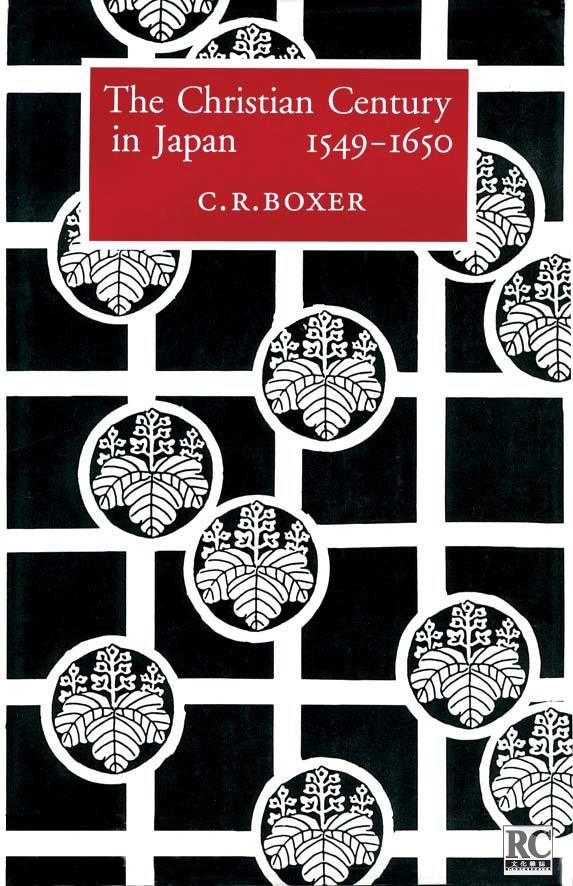
段時間,《巴西的黃金時代,1695-1750》(1962)(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 面世。前兩本書因年代重合,且大都涉及葡-荷對葡國南美殖民定居點控制權爭奪的諸方面,因而相輔相成。在《薩爾瓦多‧德‧薩與巴西及安哥拉的爭奪,1602-1686》的序言中,博克塞將英人對殖民地巴西的歷史常識恰如其分地描述為“糟糕透頂”。他指出,自羅伯特‧騷賽 (Robert Southey)的多卷本《巴西史》(History of Brazil) 問世以來,英國史學家對巴西幾乎一言未著,而騷賽的大作早在1810-1819年間就已出版。博克塞稱薩爾瓦多‧德‧薩 (1602-1686) 為17世紀葡萄牙世界的一位關鍵人物,繼而又強調,“本書的主體部分,出自葡國及巴西檔案館文獻” 。(11)
正如博克塞對薩爾瓦多‧德‧薩的半自傳體研究令其得以較為詳盡地描述及詮釋17世紀葡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所作所為那樣,《荷蘭人在巴西》同樣使其能夠對荷蘭人進行描繪,並且一如既往地聚焦於一位著名領袖。該領袖便是開明的荷屬巴西總督、拿索-錫根親王約翰‧毛里茨(Prince Johan Maurits of Nassau-Siegen),其人生跨度 (1604-1679) 與薩爾瓦多大致相當。最後,《巴西的黃金時代》講述了葡人在南美近半個世紀 (直至1750年) 的故事。與前兩本書不同的是,《巴西的黃金時代》缺乏一個中心人物。書中的篇章基本上按照地理區域組織,該殖民地各主要地區均有獨立的一章。在那一階段,殖民地巴西業已從一連串沿海定居點整合為一個幅員更為遼闊、更具凝聚力的政治實體,其經濟重要性遠遠超過宗主國葡萄牙。
在國王學院的同一時期,博克塞完成了三部歷史敍事的英譯,每一部均經過精心編輯,並配以相當篇幅的學術引言。第一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1953)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由反映16世紀下半葉前二十五年的華南的兩篇葡語及一篇西班牙語敍事組成。(12)另兩部為《悲慘的海洋史,1589-1622》(1959)(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1589-1622) 及近乎十年後出版的《悲慘的海洋史續編,1559-1565》(1968)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Sea, 1559-1565)。後兩部每本收錄三篇16/17世紀初記述葡萄牙在非洲沿海沉船的英語譯文。第一部譯著還包括了一篇描述印度航線(Carreira da India) 的運作及困境的精彩引文。同時,《來自阿媽港的大船:澳門與古代日本貿易編年史,1550-1640》(1959)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與上述三部譯著的主題相關。此書以長達150頁的引言開篇,按時間順序描述了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30年代澳門與日本近百年的貿易往來;接着便是豐富的同時代的文獻,特別反映了貿易的組織和運行、貿易的貨物、簽訂的各類合同、航海慣例及經歷、日本人的態度及反應等諸多方面。本書論證了該階段的日本貿易對葡屬印度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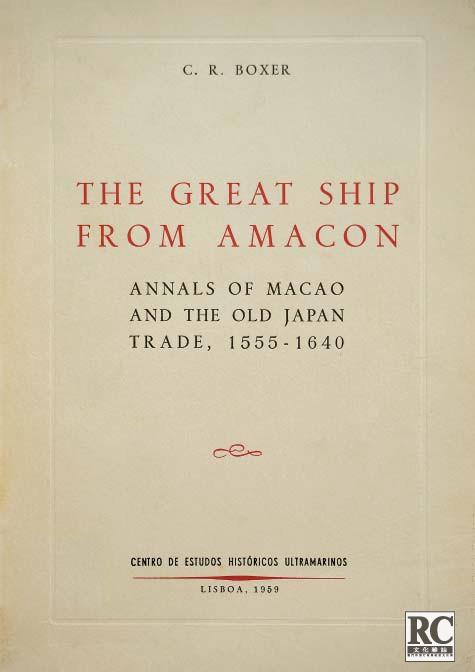
《來自阿媽港的大船》發表後的翌年,博克塞與其友人卡洛斯‧德‧阿澤維多 (Carlos de Azevedo) 合出了另一本專著《蒙巴薩的耶穌堡及葡人,1593-1729》(1960) (Fort Jesus and the Portuguese in Mombasa, 1593-1729)。該項目始於1957年,並受到古本江基金會 (The Gulbenkian Foundation) 董事們的鼓動。該基金會決定資助耶穌堡的修復,因此邀請查爾斯和卡洛斯寫一本關於耶穌堡的書,還熱情資助二人赴東非一遊。蒙巴薩這本書是查爾斯的第一部東非力作,與以往的研究再度發生了偏差。肯雅之行也標誌着其海外旅行階段的肇始。其海外之行不外乎是為了歷史研究、寫作及與此相關的觀光。
在國王學院的最後幾年,博克塞寫出了令人交口讚譽的荷蘭與葡萄牙兩大帝國的總體概述。《荷蘭的海上帝國,1600-1800》及《葡萄牙的海上帝國,1415-1825》(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實際上發表於其離開國王學院之後的1969年]),均為推理與反思之傑作,很快便成為相關領域的標準教材。然而在上述兩本書刊行之前,查爾斯於1963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卻比他所寫的任何東西都產生了更大的戲劇性影響,引起了更多的痛苦與爭議。這本小書由其1962年11月在佛吉尼亞大學所作的三篇演講組成,即《葡萄牙殖民帝國內部的種族關係,1415-1825》(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該書直接挑戰了當時葡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即“種族主義”從來就不是里斯本海外帝國的甚麼特徵,而且它從來就是為官方所擯棄的。整體而言,該書在提出自己的見解時表現得彬彬有禮,尊重並理解那些誠懇地持反對意見的論者。但由於博克塞質疑的是當時對國外批評高度敏感的薩拉查政權的根本信條,他肯定應該知道自己必將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此外,書中有一段話差不多構成了對薩拉查 (Salazar) 的人身攻擊。這段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巨大關注,因而被廣泛引用。(13)
薩拉查政府選中了博克塞的親密老友亞曼多‧科特桑教授出馬回擊《種族關係》。科特桑在20世紀30年代屬“自由派”,當時還曾自我流亡海外,但是到了50年代初,他卻決定與里斯本政權握手言和,並且回到葡國。為了支持薩拉查的殖民政策,他寫了一篇聲討博克塞新書的惡毒文章,刊登在葡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民眾日報》(Diário Popular) 上,指責查爾斯對一向熱情歡迎並款待他的國家恩將仇報。(14) 科特桑至死也未原諒博克塞的“背叛”,並嚴辭拒絕與其和解。
此前,博克塞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捲入當代葡國政治。那麼在寫《種族關係》之時,他怎麼會決定打破這一傳統?道利爾‧奧登辯稱,很可能是他“蓄意挑起的爭端”,蓋因他“十分崇拜”真相,而他知道,葡國政權的殖民領地種族關係史的官方版本,並非真相,而是對真相的嚴重歪曲。(15) 然而儘管這是一個可能性因素,本人卻傾向於認為,許多解釋(尤其是時機)均屬政治範疇。1961年初,安哥拉爆發了旨在推翻葡國統治的解放戰爭,內中不乏令人作嘔的暴行。類似的戰爭很快波及葡屬幾內亞 (Guinea) 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而葡國在上述三地的 “平叛”行動,不僅耗費鉅大,還導致了顯著的擴軍。更有甚者,1961年12月,印度軍隊佔領了果阿 (Goa)。因此,對薩拉查政權來說,60年代初不啻於一個生死存亡之期,其殖民理論及帝國的虛榮,受到越來越多的國外敵對勢力的密切審視。與此同時,葡國史家及帝國也受到越來越大的表明政治色彩(即支持或反對現狀) 的壓力。因此,像博克塞那樣的著名葡萄牙帝國史專家,就真的是面臨險境,如果他不明確擯棄薩拉查主義,就可能被貼上薩拉查走狗的標記。
對於60年代初的博克塞而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關切。當時,他已經開始厭倦為之工作了十幾年、且教學負擔日益加重的國王學院,期待着在美國的大學裡尋找工作機會,尤其是那裡的教授待遇更加優渥。1962年11月,他接受了弗吉尼亞大學的短期訪問教授職位,並於該校發表了引起爭議的種族關係演講。據稱,他當時是有意選擇抨擊種族主義問題的,而且期望得到最大程度的宣傳,以便在美國主流大學中建立自己不支持薩拉查殖民原則的史學家聲譽。(16) 兩年前,博克塞尚可避免涉足這一傷感問題,如此既可保有科特桑等人的友誼及尊敬,同時又能維護自己在英語世界的聲譽。1960年,他幾乎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薩拉查政府邀請其參加航海家亨利王子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逝世五百週年慶典時給予的款待。事實上,他是參加該次活動的英國代表團團長,而且還作了措辭巧妙、沒有爭議的發言,恭維自己的東道主。(17) 但是繼1961年葡國在非洲及果阿的動盪之後,這種走鋼絲式的平衡就行不通了。博克塞對此似乎心知肚明,因而直言不諱。但是葡萄牙保守派的逆反之劇烈,卻是他始料未及的。
與此同時,查爾斯繼續向北美學界挺進,並於1964年在威斯康星大學發表了系列演講。這些演講涉及果阿、澳門、巴伊亞 (Bahia) 與盧安達(Luanda) 的市議會,並於次年結集出版,長達240頁。(18) 大約此時,博克塞開始與有興趣最終收購其私藏圖書及手稿的各院校談判,最後於1965年和印第安那州布隆明頓市 (Bloomington) 的印第安那大學莉莉圖書館達成協議。結果他獲得該校的訪問研究教授身份,並於1967年入住該校。在此後的十二年裡,布隆明頓成為其在美國的活動中心,1969-1972年例外,其間他在耶魯大學擔任教授。在耶魯大學和印第安那大學期間,他被公認為優秀導師和教師,而且還因參加各種聚會成癮而負有盛名。因此,1967-1979年構成了博克塞學術生涯的第三階段,或者說其北美階段。然而就寫作而言,相對於國王學院那時,此一階段的產出甚少。部分原因可能在於,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來上課,準備演講稿和演講。話雖如此,這一階段博克塞出版的作品,祇有四五本小冊子。
其中一本小書講述的是17世紀葡國一名成功私商法蘭西斯科‧維艾拉‧德‧費格雷多(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的活動。該商人的貿易範圍,主要是南亞及東南亞地區。儘管以原始材料作為基礎,但是博克塞對那人的經商活動的敍述,充其量祇能算一個初步研究,談不上是全面傳記。(19) 然而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查爾斯在履行其長期義務的同時,不斷接受短期訪問教授和巡迴演講邀請,其中一些訪問導致了有意義的發表。例如,1972年10至11月他在布林茅爾學院發表的系列演講,就與當時日益熱門的婦女史課題相關。演講描述了葡萄牙及西班牙婦女在四百年 (1415-1815) 的海外擴張進程中所起的作用。這些講稿後來被結集成一本140頁的書:《伊比利亞海外擴張進程中的婦女,1415-1815》(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 1415-18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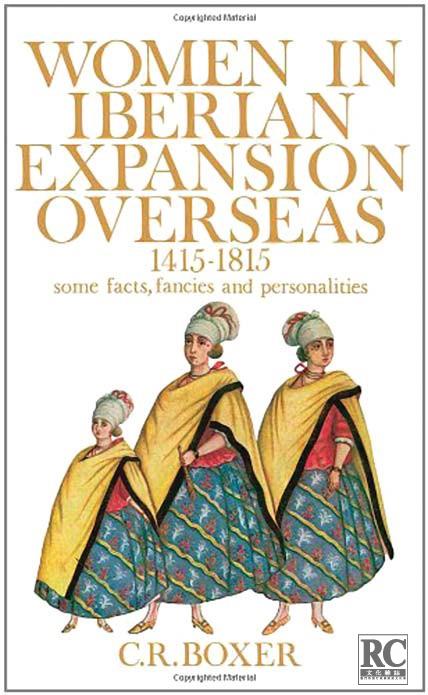
1976年,博克塞再度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邀請,前往開設斯庫勒講座 (Schouler Lectures)。他此次選講的,是在葡萄牙及西班牙擴張的語境下天主教會進入非歐洲世界的傳教事業。有趣的是,他給四篇演講中的第一篇起了個“種族關係”的標題,因而回到了十三年前引發那場悲痛的話題。斯庫勒講稿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於1978年集結出版了專著《教會激進分子與伊比利亞擴張,1440-1770》(The Church Militant and Iberian Expansion 1440-1770)。《教會激進分子與伊比利亞擴張,1440-1770》問世時,博克塞已近七十五歲,仍在從事教學。他越來越感到歲月不饒人。1979年春,在印第安那大學上完最後一個學期的課程之後,他決定退休。同時他寫完了最後一本小書《若昂‧德‧巴羅斯:葡萄牙人文主義者及亞洲史學家》(João de Barros.Portuguese Humanist and Historian of Asia)。該書於1981年出版,儘管完稿於數年以前。它展現了博克塞之所以成名的一系列品質:全面搜集原始資料,去偽存真,充分掌握細節,強烈的語境感及優雅的表達。
70年代末,博克塞仍想迎接一些學術挑戰,其中不乏重大項目。然而此時的應戰,似乎均顯得有些好高騖遠。他本想為兩位歷史人物立傳,一位是安東尼奧‧維艾拉神父 (Fr. António Vieira),另一位是阿勞那侯爵 (Marquis of Alorna)。維艾拉乃17世紀著名耶穌會傳教士及宮廷神甫,博克塞認為他是葡語散文創作的最佳典範。(21) 早在50年代,查爾斯就曾為維艾拉寫過幾個短篇,但後來卻堅信,真正需要的是為其作一全傳。然而因為手頭有更緊要的任務,他不得不數度推遲傳記寫作。最終,維艾拉傳記始終沒有問世,奧登因此大發感歎,稱其為“子孫後代的巨大損失。”(22) 另一個擬作傳記的對象,是唐‧佩德羅‧米格爾‧德‧阿爾梅達‧博爾圖加 (Dom Pedro Miguel de Almeida Portugal, 1688-1756),第一代阿勞那侯爵,第四十四任葡屬印度總督。1959年,博克塞獲得該侯爵的大批文獻,激起其對阿勞那的興趣。在整個60-70年代,他無疑對阿勞那項目充滿了熱情,但由於手頭有更要緊的學術任務,他同樣被迫幾度推遲傳記的寫作計劃,到頭來,阿勞那傳記也未寫成。(23)
在此,筆者想給這篇回顧查爾斯人生及工作的短文增添一些個人回憶。在筆者記憶中,第一次感覺到查爾斯作為歷史學家的存在,是50年代初在通俗期刊《今日歷史》(History Today) 上讀到他的文章之時,當時他定期給該雜誌撰稿。數年後的1960年,在牛津大學讀研究生時,我第一次買下了博克塞的《蒙巴薩的耶穌堡及葡萄牙人》。我對該地十分熟悉,因為孩提時代在東非時多次路過耶穌堡,祗是從未進去,因為英國殖民當局當時將它用作監獄。該書寫得引人入勝,愈加加深了我對史學家博克塞的尊敬。當然,到那時為止,我還未曾有幸目睹過他的尊容,也未曾與他通過信,甚至未曾聆聽過他的發言。過了一段時間 (大約是1960年底或1961年,記不準了),我才在牛津聆聽了他的一次客席講座。
直到1964年在墨爾本大學擔任青年代理講師並考慮做一篇葡萄牙課題的博士論文時,我才第一次嘗試與其接觸,儘管是通過時任墨爾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麥克斯‧克勞馥 (Max Crawford)教授間接進行的。博克塞善意地親筆作覆,進行鼓勵,並寬慰道,我所考慮的葡萄牙殖民史的各領域,均“存在充分的空間”,還敦促我盡可能多地閱讀相關題材。(24) (當時我還不是十分明確自己到底想要研究哪一課題,儘管曼努埃爾國王[King Manuel] 這一人物及其主張令我着迷。)當時,博克塞正準備離開國王學院。有一段時間,誠如他在1965年的一封信中告訴我的那樣,他曾認真考慮是否來坎培拉 (Canberra) 任專職研究員。果真如此,我肯定會成為他的博士研究生。但是,他當時解釋道,他的家人反對他移民澳洲,最終祗得“忍痛割愛”。(25) 為了減輕我的失望,他在同一封信中安慰道:“當然,我認為導師問題並非關鍵。我審閱過的最優秀的博士論文 ( 自1947年起,我審閱過無數),幾乎90%乃至99%是博士生自己寫的,基本或根本不欠導師甚麼。”一年之後,我去了哈佛大學文理研究生院,在帕里 (J. H. Parry) 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
1969年初,與博克塞見面的機會終於到來了。當時他已在布魯明頓,而我則在芝加哥紐伯利圖書館做為期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從芝加哥飛往布魯明頓,簡直是輕而易舉,所以我寫信詢問是否可去看他。“當然”,他回覆道,“很高興將與您見面,您的課題我很感興趣。”(26) 他指的是我論述葡萄牙東印度公司歷史 (1620-1633) 的博士論文。當然,他對我使用的資料瞭若指掌,如倫敦國王學院的私刑法典 (Codex Lynch) 及哈佛霍頓圖書館的各類阿泰德文獻 (Ataide Documents)。對於我來說,那次會面啟迪心智,彌足珍貴,分手之後,心中仍然驚訝他對細節的難以置信的掌握,並感激他慷慨與我分享所知。
數月之後,我又收到他一封來信,問我能否幫其解開一個神秘的謎團。他解釋道,早在1962年4月,他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個叫麥克羅伯特 (Captain E. MacRobert) 的人從據稱是墨爾本郊區博馬里斯 (Beaumaris) 寄來的信。寄信人自稱是澳大利亞聯邦航運和交通部航海司司長。麥克羅伯特寫道(引查爾斯):“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馬蒂亞斯‧德‧阿爾布克爾克 (Matias de Albuquerque) 的個人日記原本在墨爾本 [⋯⋯] 科堡 (Coburg) 的沃爾特‧伯奇 (Walter Birch) 先生手中,並得到妥善保管。”他進而詢問查爾斯是否對那些文獻感興趣,並且還附了一份清單。博克塞說他“立即”回函表示極感興趣,但又補充道,他沒有收到回信,此後這位神秘的麥克羅伯特便音信全無了。(27)
博克塞和我都清楚,如果馬蒂亞斯‧德‧阿爾布克爾克(1591-1597)年任果阿總督)的“個人日記”真本果然在墨爾本現身,那麼它將成為研究這位16世紀葡萄牙總督的潛在價值無量的獨特資料。因此我當即表示,一俟回到澳大利亞,立即着手查證麥克羅伯特的說法。我也的確那樣做了,但是到那時為止,麥克羅伯特的信已是七年之前的事,線索都斷了。儘管我十分賣力,但仍未追蹤到那個神秘的麥克羅伯特或伯奇,那個說法也日益顯得虛無縹緲。我把情況向查爾斯作了彙報,他回信稱:“你我的看法一致,那個伯奇和阿爾布克爾克有關係的說法 [⋯⋯] [聽上去] 像是子虛烏有。”他補充道:“我們應把此事視為扯淡,除非有甚麼東西意外出現。”(28)
經歷了阿爾布克爾克這一掃興事件之後,博克塞在70年代繼續與我偶爾通信。回顧這些信件,不難看出,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的態度變得日益放鬆隨便。起初他總是相當正式地稱我為“迪士尼先生”,但是到了70年代的某時,對我的稱呼就變成了“迪士尼”(他在一封信中寫道:“現在我們完全可以不必那麼拘禮。”),最終成為“安東尼”,甚至“托尼”。署名同樣發生了變化,起初無一例外是“查‧拉‧博克塞敬啟”,後來開始用“查拉博”(CRB),最後是“永遠的老友查爾斯”。
1978-1979年間,我倆之間書信往來頻繁,事關我為其安排的澳洲之行。行程定於1979年7-8月進行,他將於三到四週內走訪墨爾本、坎培拉、阿米代爾 (Armidale)、阿德萊德 (Adelaide) 和珀斯 (Perth),並在每個城市做一場演講,或主持一次研討課,或兩者兼顧。此前他從未到過澳洲,心中卻一直對其充滿嚮往。他迫不及待地添加了霍巴特 (Hobart),因為,他解釋道:“那是我母親的出生地。”然而他同樣意識到,對於他那樣的老人 (時年七十五歲),行程未免過於緊張。(29)他擔心怎樣才能完成將於拉籌伯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宣讀的論文,因為主題必須是拉丁美洲。(最後他確定論述的,是英商與巴西貿易。(30)) 他非常關心 (也是我關心) 的另一問題,是能否籌到足夠的經費。“假如天從人願,”他說,“我將手持化緣缽於7月22日抵達墨爾本。”但他的擔心是多餘的,經費已經為其湊齊。儘管旅途勞頓,他依然感激涕零。10月份到家後,他來信稱:“我依舊沉浸在澳洲之行的歡樂中,每一分鐘都

1991年澳門大學向博克塞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是享受。”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但願我能回到澳洲。”(31) 每逢晚會,他都特別開心,縱情高歌,一如既往。雖然他自己會唱很多歌曲,但很快就和當地一名流浪歌手打得火熱,還堅持稱對方為“伯爾‧艾弗斯”(Burle Ives)。(32)
澳洲之行結束後,查爾斯又踏上了新的旅程,這次是前往海灣地區,對馬斯喀特(Muscat)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他稱,因為政治局勢緊張,去那裡“很不容易,費盡了周折”。1979年底和1980年,他還出訪了阿布達比(Abu Dhabi)、葡萄牙、荷蘭、斯里蘭卡和日本。儘管年齡不饒人,他的身體顯然依舊健朗。1980年在歐洲休教學假時,我和家人有幸去了小加德斯登 (Little Gaddesden) 的查爾斯家中拜訪。他給予我們熱烈歡迎,並設午宴款待,還送給孩子們一盒巧克力。下午,我的家人去動物園參觀,而我則留下來抄錄博克塞私藏手稿中有關利尼亞雷斯伯爵 (Conde de Linhares) 的資料。80年代初,我們繼續通信。查爾斯不喜歡英國的冬天,總是抱怨天氣。“經歷了這場有史以來最大的鵝毛雪之後,”他抱怨道,“一切都亂了套,人們感到恐慌,不知所措。”他似乎不合邏輯地補充道:“當然,自1066年 (如果不是更早)以來,每年至少都下一場。”(33) 幾年後,他寫道:“今年夏天熱破了紀錄,人人都熱得怨聲載道,[但] 總比冬天的冰雪嚴寒好受些。”然後,在回答我提的里斯本問題時,他略顯頑皮地寬慰道,我錯過的那次大會“真的是一團糟,七百多人(大部分是小妾和幫閒),而且組織得很差。”(34) 在後來的另一封信中,他又以相當嚴肅的口脗對我說,他“在紅色中國呆了一個月,剛剛到家,重遊了從長城到廣州等30年代就熟知的老地方” 。(35)
翌年,我第一次得到真正的暗示,他或許是真的老了。7月間他告訴我,他不得不取消其馬尼拉之行,因為“我視力無法聚焦,必須去醫院做眼科植入手術” 。他在等待新配的眼鏡,“在這個蒙昧國度,那是要花時間的,”三到四週,而在香港,“48小時就可以搞定” 。(36) 他最終肯定得到了眼鏡,而且對其有助,因為那年 (1984)耶誕節他來信稱,他(取道香港)“愉快地遊覽了”澳門。另外,他期待着1985年去里斯本。(37) 當然,那時他已經年屆八十。
80年代至90年代初,查爾斯以其英國赫特福德郡 (Hertfordshire) 靈歇爾區 (Ringshall End)的家為永久基地,繼續外出旅行。1991年,他最後一次回到心愛的澳門,參加第六屆印-葡史國際研討會。他沒有宣讀論文,但澳門大學卻趁其光臨,向其頒授了榮譽博士學位。會議期間,法國資深學者熱納維夫‧布尚(Genevieve Bouchon)教授代表全體與會者發言:“我們將永遠銘記查爾斯‧博克塞教授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慷慨幫助。”場面十分感人。1996年,在其第一篇文章問世之後的七十年,九十二歲高齡的查爾斯發表了最後一篇學術作品。他畢生發表學術論著三百五十多篇/部,幾乎全是論述葡國或荷蘭擴張史的。(38) 次年6月,在墨爾本及弗里曼特爾 (Fremantle) 參加瓦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逝世五百週年紀念大會的全體與會人員,聯名致函九十三歲的查爾斯,向其表達“最熱烈的問候” 及“最崇高的敬意”。(39) 然而此時的查爾斯,已經是弱不禁風,視力惡化近盲,短期記憶也越來越不可靠。
查爾斯最終於2000年4月27日仙逝,享年九十六歲。輓辭如雪片,多為讚頌,茲舉數例。安東尼奧‧德‧費蓋雷多 (António de Figueiredo) 在《衛報》(The Guardian) 上撰文,稱其為“研究歐洲早期海外擴張史的最優秀的英國史學家之一”,還稱其“高於生活”, “情感十分豐富”。傑佛瑞‧斯卡梅爾 (Geoffrey Scammell) 稱其為“學界最偉大、最特立獨行、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查爾斯的忠實朋友約翰‧卡明斯 (John Cummins) 在悼念文章中,讚其“精力旺盛,從容不迫”,“思維清晰、敏銳、精確”。但也存在唱反調的。2001年2月24日,海韋爾‧威廉姆斯(Hywel Williams)在《衛報》上發表文章,讚頌查爾斯為“優秀的戰士、才華橫溢的史學家”及“權威人物”,然而他筆鋒一轉,繼而令人驚訝且無根無據地稱:“儘管博克塞天資聰穎,但他也很可能是個叛徒。他在香港戰俘營出賣了自己的戰友,從而使整個英國東南亞情報系統陷入危機。”(40) 查爾斯的朋友、家人、學生及同事,立即表示強烈憤慨。許多人寫了評論及信函為查爾斯辯護,最有力的反駁來自查爾斯一絲不苟的傳記作者道利爾‧奧登,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熟悉博克塞的故事,此外還有外交關係理事會的肯尼斯‧麥克斯韋爾 (Kenneth Maxwell)。威廉姆斯的說辭顯然含沙射影,純屬臆測,無法出示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來支持其惡意譭謗。對於那些在博克塞顯然無法自辯之時挺身為其辯護的人,他未作任何回應,也就是說,在丟下炸彈之後,他若無其事地走開了。
我與查爾斯的最後一次會面,是在前文提及的1991年澳門研討會上。他是去接受榮譽而非宣讀論文的,因而受到精心照顧。此時,他的信函也日漸稀少。說來也怪,我讀到的他的最後一封信,是其給某個寫信向其徵求課題意見的學生的回函。查爾斯用顫巍巍的手寫道,“親愛的某先生,謝謝來信。不幸的是,我太老了(九十多歲),病太多了,其它雜事也太繁了 [⋯⋯] 顧不上您的問題。但是您似乎處在正確的路線上,應該能寫出有用的東西。”顯然,他終於準備封筆了,他也有權這麼做。然而他卻仍在努力鼓勵後進。——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
【註】
(1) 關於博克塞早期成長的概述,參見道利爾‧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不平凡的一生:戰士、史學家、教師、收藏家及旅行家》(Charles R. Boxer: An Uncommon Life. Soldier, Historian, Teacher, Collector,Traveller),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1,特別是頁28-29、頁44及頁47。
(2) 關於博克塞在香港當情報官及此後的戰俘經歷,參見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第六-八章。
(3) 博克塞在此期間確實發表過四件作品,包括《葡萄牙復國時期的澳門》(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澳門:官印局,1942年) 及《澳門船隊司令及總督歷史資料》(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s Capitães-Gerais e Governadores de Macau 1557-1770) (澳門:官印局,1944年)。但這些作品幾乎肯定是在香港失陷前交付出版社的。
(4) 博克塞不久前得到該手稿的兩個已知抄本之一。該書的第二版為《中國與日本的亞洲》,兩卷本,澳門:1988年,增收了耶穌會士潘日明神父 (Benjamim Videira Pires)新作的序。
(5) (6) 博克塞:〈盎格魯-波斯的波斯灣競爭〉(Anglo-Persian Rivalry in the Persian Gulf 1615-1635),見艾德加‧普雷斯蒂奇 (Edgar Prestage) 編《英-葡關係選編》(Chapters in Anglo-Portuguese Relations),沃特福德 (Watford):沃斯暨邁克爾出版社,1935年,頁59;頁285-304。
(7) 參看布雷爾‧沃爾頓 (Blair Worden)〈百歲老人特雷弗-羅珀〉(Trevor-Roper at a Hundred), 見《牛津歷史學家》(The Oxford Historian),第11期,2014年,頁14。
(8) 關於對博克塞這一時期重要發表的更全面的評價,參見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特別是頁341-355。
(9) 博克塞,《遠東的貴族,1550-1770》,海牙:馬蒂努斯‧奈霍夫出版社,1949年,〈引言〉,頁X。關於博克塞的傳記作品,參見安東尼‧迪士尼〈傳記作者查爾斯‧博克塞:初步評價 〉(“Charles Boxer as a Biographer: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見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第4卷,2003年,頁9-28。
(10) 轉引自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頁348。
(11) 博克塞,《薩爾瓦多‧德薩與巴西及安哥拉的爭奪,1602-1686》,倫敦:阿斯隆出版社,1952年,頁X。
(12) 兩位葡語作者分別為伯來拉 (Galeote Pereira) 與克路士(Gaspar da Cruz OP),西班牙作者為奧斯定會修士馬丁‧德‧拉達 (Martín de Rada)。
(13) 在《葡萄牙殖民帝國內部的種族關係,1415-1825年》(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63年) 的頁40,博克塞評道,安哥拉“風行的社會模式,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有意識的白人至上主義” 。他接着補充道:“在這方面,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卡東尼加上尉 (Captain António de Oliveira Cadornega) 要比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博士 (Dr.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靠譜,前者在安哥拉生活了四十多年,後者從未踏足過非洲。”(在西非內地生活了近四十年之後,卡東尼加於17世紀80年代初寫了一本“安哥拉戰爭”的史書。)
(14) 此時博克塞與科特桑之間令人傷心的公開友情決裂,在奧登的《查爾斯‧拉‧博克塞》中 (頁369-386) 有詳述。
(15) 奧登的《查爾斯‧拉‧博克塞》,頁386-387。
(16) 參看魯伊‧拉莫斯 (Rui Ramos) 的有趣文章,〈面對戰爭(約1960-約1970) 的一位葡萄牙博學家:對博克塞與科特桑爭論的若干思考〉(“A Erudição Lusitanista perante a Guerra (c.1960-c.1970): Algumas Observações sobre a Polémica entre Charles Boxer e Armando Cortesão”),見《葡萄牙在英語世界的發現,1880-1972》(The Portuguese Discover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1880-1972),特蕾莎‧平托‧科埃略 (Teresa Pinto Coelho) 編,里斯本:Edições Colibri, 2005年,頁189-218。
(17) 博克塞: 〈大不列顛議員的演講〉( “Discurso do Representante da Grã-Bretanha”),見《大發現史國際討論會文集》(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里斯本:紀念亨利王子逝世五百週年執行委員會,第一卷,1960,頁75-77。
(18)博克塞:《熱帶地區的葡萄牙社會:果阿、澳門、巴伊亞及盧安達的市議會,1510-1800》(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and Luanda, 1510-1800),麥迪森、密爾沃基: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65年。
(19) 參見博克塞《法蘭西斯科‧維艾拉‧德‧費格雷多:東南亞的葡萄牙商人冒險家,1624-1667》(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A Portuguese Merchant Adventurer in South East Asia, 1624-1667),海牙:馬蒂努斯‧奈霍夫出版社,1967年,頁113。
(20) 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75年。
(21) 博克塞,《荷蘭人在巴西,1624-1654》,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頁273。
(22) 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頁577。但是博克塞此前確實寫過幾個維艾拉的短作品,包括《盧西塔尼亞-巴西偉人:耶穌會士安東尼奧‧維艾拉神父,1608-1697》(A Great Luso-Brazilian Figure: Padre António Vieira, S. J., 1608-1697)的小書,1957年由倫敦西班牙及路西塔尼亞-巴西理事會刊行。
(23) 1975年7月,博克塞寫道,他仍然決心寫阿勞那傳記,但“由於手頭要緊事情太多”,被迫擱置了一兩年。(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75年6月30日)差不多三年後,他承認,“阿勞那傳記始終沒有進展,因為給外聯處的葡萄牙國家文件 (1661-1780) 分類編目,令我心生旁騖。”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78年5月28日)
(24)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64年11月3日。
(25)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65年7月17日。
(26)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69年3月10日。
(27)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69年5月11日。
(28)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70年6月21日。
(29)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78年8月8日。
(30)參見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79年5月17日。該論文後來收入研究所的雜文叢書《英國人與葡屬巴西的貿易,1660-1780:一些問題及一些人物》(The English and the Portuguese Brazil Trade, 1660-1780: Some Problems and Pesronalities,墨爾本:拉籌伯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1981年)。此書現已成為珍本,甚至沒有收入博克塞的標準出版物書目《查爾斯‧拉爾夫‧博克塞教授紀念文集》(A Tribute to Professor Charles Ralph Boxer,菲蓋拉達福什:CEMAR,1999年)。
(31)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79年8月29日,1979年10月15日。
(32) 後來,我還曾與“伯爾‧艾弗斯”聯繫,向他索要澳大利亞諷刺歌曲〈總有那麼一個孟席斯〉(There’ll always be a Menzies) 的確切歌詞,因為查爾斯想於國內一個耶誕節晚會上演唱。
(33)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81年12月23日。
(34)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83年12月30日。
(35)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82年12月16日。
(36)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84年1月21日。
(37) 查拉博致迪士尼函,1984年12月4日。
(38)他的最後作品似乎是〈對16世紀末與17世紀初澳門、長崎及海上絲綢貿易的反思〉,《天理宗教學刊》(Tenri Journal of Religion),第24期,1996年3月,頁79-84。參見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頁584。
(39) 見奧登,《查爾斯‧拉‧博克塞》,頁504。
(40) 海韋爾‧威廉姆斯,〈英雄秘史〉(“Secret History of a Hero”),見《衛報》,2001年2月24日。
郭頤頓譯
* 安東尼.迪士尼 (Anthony Disney),(澳州)拉籌伯大學榮譽學者,在葡萄牙及海外 (特別是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海洋亞洲的)葡人方面著述頗豐。其首部著作《胡椒帝國的黃昏》(Twilight of the Pepper Empire) 於1978年面世,兩卷本《葡萄牙及葡萄牙帝國史》(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2009年出版。目前安東尼正在為第四代利納雷斯伯爵唐‧米蓋爾‧迪諾羅尼亞 (Dom Miguel de Noronha) 作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