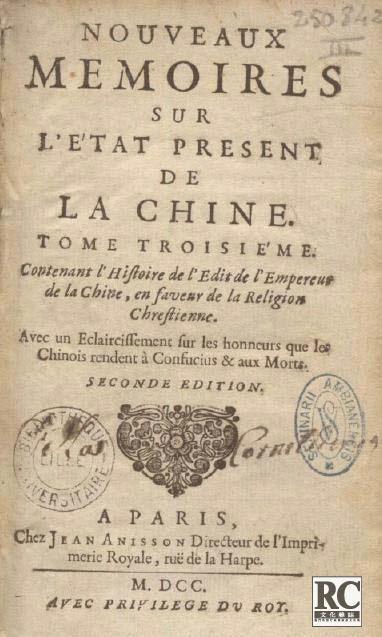 |
|
郭弼恩神父《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1698年第二版封面,由法國里爾三大圖書館館藏
|
法國耶穌會士郭弼恩神父 (Charles le Gobien 1653-1708) 根據在華傳教的法國耶穌會士劉應神父書信所完成的《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於1698年在巴黎出版,該書是研究明清天主教入華傳教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這部著作不僅對1692年康熙帝解禁天主教在華傳教的全過程進行了詳細生動的論述,填補有關杭州教難和耶穌會士在宮廷行走的歷史細節,同時亦可與《清實錄》、《清代起居註冊》等清史史料相互印證,為深入探究康熙朝朝廷和天主教的互動關係提供豐富的歷史材料,甚至可從中窺測清初滿漢關係和夷夏之辨在當時歷史中的反映。
法國耶穌會士李明神父的《中國近事報導》於1696年分上下兩卷在巴黎出版。由此,郭弼恩神父便以“中國近事報導”系列第三卷的名義於1698年出版此書,因此該書全名為“中國近事報導第三卷: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兼論對中國祭孔祭祖問題的澄清”(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tome3 Contant l’Histoire de L’E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vecun Eclairement sur les Honneurs que les ChinoisRendent à Confucius et au Morts)。從內容上講,郭弼恩神父的這本著作可一分為二:一是由上下兩卷組成的〈1692年康熙寬容天主教傳教詔令史〉,其卷一記敍傳教士謀求赦教的起因,即杭州教難的前因後果,卷二則論述康熙在京頒佈容教詔令的具體過程,這二卷即本文節譯的部分;二是一篇〈對中國祭孔祭祖問題的澄清〉的論文,內容是關於郭弼恩神父對於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同耶穌會就中國禮儀問題爭論過程的研究。由於兩者內容不統一,限於篇幅,本文不做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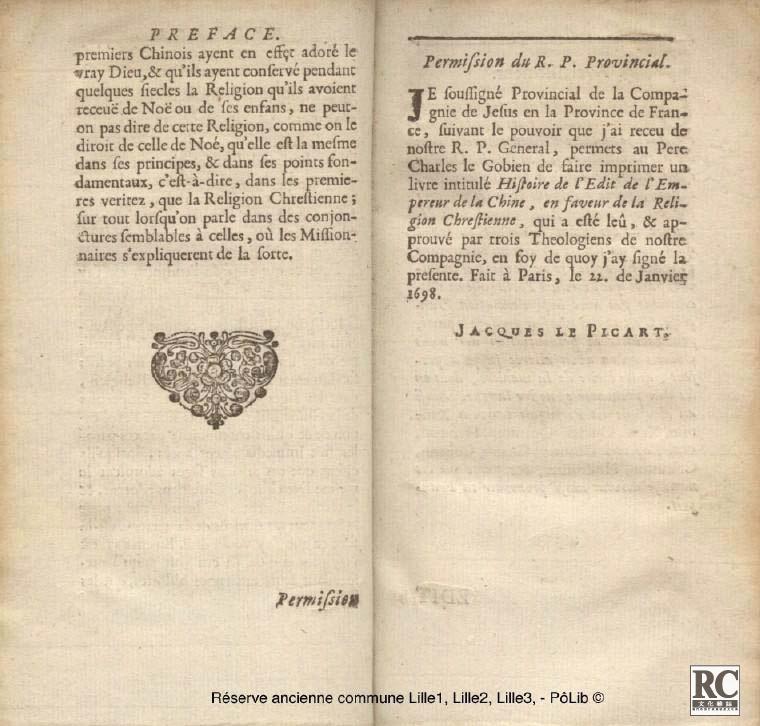 |
| 耶穌會會長的許可狀由三位耶穌會士神學家審查,由耶穌會會長授權耶穌會法國省允許出版。地點巴黎,時間1698年1月22日。 |
本文節譯的主要包括:1. 張鵬翮在杭州發佈的三道禁教命令的記載;2. 殷鐸澤神父在杭州上堂的細節;3. 康熙侍衛趙昌在康熙和耶穌會士之間居中協調的細節;4. 康熙對容教態度的轉變;5. 索額圖支持赦教的具體話語。
本文譯自1698年版,下文每節末尾的頁數即為原書頁碼。限於篇幅,本譯作刪除了部分諸如介紹廣東省地理位置所在等原註,以便閱讀。凡《熙朝定案》有的譯文,祇要準確無誤,本文一概採用,不再另行翻譯。有不解亦或必要之處,譯文加了譯註。譯者水準有限,凡有錯處,請另行指正、賜教。
浙江巡撫張鵬翮禁教舉措:第一道命令巡撫立刻來精神了,因為這正好可以把殷鐸澤神父也牽扯進來,情況似乎對他有利了,他下令審查殷神父。為了挑起這場其蓄謀已久的戰爭,他親自撰寫污蔑基督教的佈告,將其張貼在教堂門口,大量刊印並在杭州城和整個浙江境內散發。大家看到佈告或許不會那麼生氣,我們將其逐字逐句地翻譯過來:
為嚴禁歐洲人四散傳單以蠱惑人心之事,嚴禁百姓違抗朝廷律令入教,誠望此令能維持律法之威嚴,引領百姓歸於正途。眾人皆知世間各國之律法,無論其所蘊含關乎修身和治國之道何其完美,究其根本,皆遜於儒家之言。儒家講求:在家應順父母之命,孝敬長輩;為官應忠君愛國,待民如子。儒家奉周公(1)和孔子(2)為先師,克己復禮,推己及人,以仁義為本。禮,乃克己應守之道;樂,和諧乃其象徵;律法亦或施仁政,乃禮實踐之法度。儒學之完備,宛如星辰輝映下之日月,猶如哺育大地之江河。婆羅門教、佛教之微言豈可與之相較,最多也就好比蘆薈製成之火炬所散發曇花一現之微光,亦如牛跺地所留之水窪。其有何德何能非去膜拜信奉之?
當今聖上獨尊儒術,親自註解四書(3)五經(4),而後分發各地,以為儒家精髓可世代弘揚,以為唯其一家之言獨步天下。如今康熙盛世,萬民應聆聽聖人之言,應傳習孔孟之道,聖意如此也。農工商平日應恪守本分,各盡其事,以求富足安康。閑暇之餘,則可相互間切磋研習〈聖諭十六條〉,以便融會貫通,防墮邪魔外道。故而農工商者之理想乃為儒學,其根本乃是忠貞不渝地期盼天命所歸。
然浙江百姓愚昧無知,罔顧其責,迷信耶穌。基督教源於外海西洋人,明朝 (Taiming)(5)末年(6) 入華。本朝(7) 皇帝曾下旨,其言道:“留南懷仁及其同仁,允爾等拜天主,一如往昔。未免有人新建教堂或入教,朕下令嚴行曉諭各省督撫衙門禁止。”該旨意發於康熙九年(1670)。禮部據此擬旨:“歐洲傳教士中凡有通曉曆法者,着取來京,與南懷仁同居;其不曉曆法者,准其各歸本堂,特許傳教士在教堂內修道,但無論宮中還是各省臣民,皆禁行入教。前旨具詳,故着令嚴守該旨。”(8)
殷鐸澤神父不知何時棄江西堂口而入浙,其若自稱為方外之人,則應遵紀守法,閉門謝客。何故又刊印《天主律法釋》、題名“七勝”(9) 一書等?何故又差人繪製上帝畫像,其後又命信徒擇日前去拜祭且留下年輕人等?何故又在杭州,蘭溪,海寧,餘杭之臨安,德清以及浙江各地四散傳單於民?無知愚民入教者達千餘戶之多,皆因違反朝廷禁令而成待罪之身,為此需適時教導,仍着嚴行禁止。正基於此,本府期望無論達官紳士,亦或尋常百姓,皆應明晰其所應守之法。
爾等棄聖賢所示之正途,而行西洋之小徑,逆聖旨而入異教,大錯特錯。其罪之深,應按律嚴懲。本府念及爾等昏愚,乃為人蠱惑而不慎墮入邪教,故而欲既往不咎,留爾等自行整改之餘地,但從今往後,應務必謹遵聖旨,以防再墮入教。冥頑不靈而未及時脫教者;或者尚有人,無論男女,若不務正業而恪守教規(10),本府下令各府衙凡遇上述者,嚴查不貸並據呈上報;殷鐸澤一干人等若違逆聖旨而傳教,立行拘捕;被引誘入教者亦按律例予以嚴懲;包藏庇護者同罪論處,決不寬待。須示眾人。康熙三十年七月十六日 (1691年9月8日) 這第一封告示是迫害的信號。該省所有的官員都表態獻媚於巡撫,他們每個人都張貼告示竭力羞辱基督教,由此基督教變成了那些偶像崇拜和無神論者們的玩物和笑料。(頁33-44)
浙江巡撫張鵬翮禁教舉措:第二道命令
巡撫很高興其一夥人中有一個像布政司一樣聰明能幹的人,於是向其又發佈一道針對殷鐸澤神父的命令。因為我相信大家不難搞明白中國的司法程序,所以全文刊出如下:
據康熙十年廣東官府發文,傳教士各歸各省本堂,殷鐸澤應回江西建昌府。故須詳查其於何年入浙。再者,據杭州知府上報,康熙三年杭州教堂按令查封,時逢楊光先彈劾湯若望。如今殷鐸澤居於內,是否通報官府?然教堂既已封查,其有何理可匿藏於內?又詔令雖允西洋人復歸各堂,但仍禁行傳教,其須遵旨嚴守不怠。
杭州知府所報,內有一行醫教民Chintasen,據其述省內教堂遍佈,堂內必有一上帝畫像,教民膜拜,且用其蠱惑他人入教。此外,殷鐸澤差人刊印之《天主律法釋》、教民稱之為《七勝》之作,皆為異端邪書。此洋人誘民入教,違抗聖旨,凡此種種皆與朝廷安良之法相悖,遂須嚴查禁行。誠望布政使及各級同僚,克盡己責,查明許伯多祿康熙三年前之居所,浙江亦或別處,其復歸本堂之日期是否有據可查。
至於殷鐸澤,已查明其潛入浙江年份,康熙十年應遣返於江西。然須查明朝廷是否詔令允許其居於杭州教堂內?該堂既已查封,朝廷是否又允許其自行開堂傳教?Chintasen何年成教民,何人唆使其入教?今布政使應與按察使(11)會同查明上述要點並責成上報。Chintasen所言教民遍佈全省一事,應嚴行禁止。各州府衙門告誡百姓西洋邪教妖言惑眾,成教其等迷途知返並焚燬上帝畫像,以正視聽。此外,須尋得殷鐸澤刊書刻板藏匿之所,若朝廷允許其刊書,然則為平息教亂,朝廷是否明示何以為之,如何為?上述要點須明察上報,不得有誤。(頁46-50)
殷鐸澤神父在杭州的答辯辭
他又說:“大人,那些年的事情,當時聖上南巡,春遊西湖(12),湖水淹至城牆,您自己不都可以作證嗎?難道您不記得當時聖上差御前侍衛賞賜我堂,他們還遵從聖旨叩拜天主聖像,聖上賞賜果盤,當時微臣有幸三次覲見龍心甚悅?大人您怎麼可能一點也不知道聖上問我的問題呢?這是呈上給您的詳文。”與此同時,他還將其剛才所述的內容刊印出來一併給了他。
這些事情完全沒有必要掩掩藏藏,因為皇帝像拉家常一樣和他說話,大家並不會覺得很奇怪,問他住在哪裡,最近教會的事情怎麼樣,基督徒的數量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巡撫想要知道的就是這些事情。聽完殷鐸澤一一回奏後,皇帝和藹地說:“老人家(13) 您就安心住在這裡吧。”
殷鐸澤神父不願退讓,於是這位官員就將這些供辭上呈至杭州府,知府對此不滿,他覺得裡面有許多地方都沒有講清楚,於是便立刻發還重審,凡有遺漏不詳之處皆詳查。就這樣,也是同一位衙役傳喚,神父不得不第二次到堂。第二次開堂的記錄如下:
官員問他:“難道您不知道巡撫下令即刻焚燒教堂內的天主聖像嗎?為何您不這麼做?”殷鐸澤回答:“上帝和聖人聖像不可以燒,如果大家要燒,那麼我祇有先自焚。至於燒聖像的問題,皇帝下旨允許南懷仁和其同伴拜天主,一如往昔。我展示聖像,拜祭聖像,不也祇是盡我該盡的職責而已嗎?”
官員繼續問:“您讓人刊印書的刻板(14)放在哪裡?”神父回答:“這些刻板自萬曆年間就已經做出來了,現在我用這些書,裡面絲毫沒有蠱惑欺騙民眾的東西。”官員又問:“你有朝廷律令允許你發行傳播這些書嗎?”神父回答:“我沒有得到允許,但手上也沒有禁令。”官員最後說:“但是現在有人不想看到這些書在全國流傳,您覺得有甚麼辦法可以禁書?”神父回答:“這些書是上帝之書,不是我的書,我從未叫人去發行刊印,您又怎麼會想到要我去阻止它們流傳呢?”(頁53-58)
杭州府縣的判決
這位官員處事公允,並不忌恨基督徒,所以殷鐸澤回答的時候他還處處提點,沒有搞得很過火,所作出的判決也不符合巡撫和其他官員的意願,判決全文如下:
本縣以為教堂所示之天主聖像,乃殷鐸澤崇拜之物件,修行之法門,望愛之圖飾,由此,本官認為可暫緩焚燬之。刊書刻板作於萬曆年間,如今確存於教堂之內,然朝廷尚無律令允其刊發,亦無旨意嚴查禁存,則其雖已刊印多冊,為殷鐸澤每每講經佈道所用,仍不足以明斷其魅惑百姓之罪。書由中文著作而成,確有引人獵奇之效,但文中鮮有錯處。如今各地官員既欲嚴令禁印禁閱,則有書亦如無書一般,亦無必再質問殷鐸澤應如何查禁流傳一事。誠望大人明察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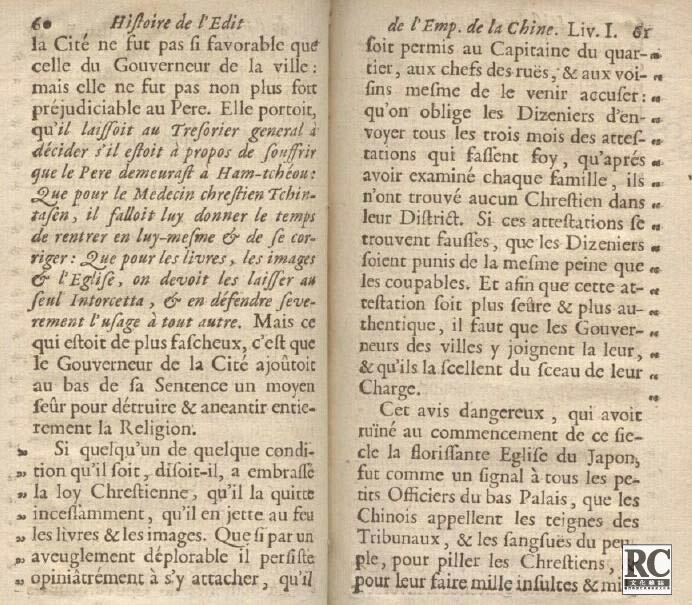 |
|
杭州府縣的判決其中郭弼恩神父認為杭州知府判決中最致命的禁教措施,實行保甲鄰里連坐的排查制度。
|
知府(15)雖不如他那般友善,但也沒有怎麼為難殷鐸澤。他讓布政使決定是否繼續讓其居於杭州;至於 Tchintasen,他給他時間改過自新;書籍、聖像以及教堂唯殷鐸澤一人可用,他人嚴禁使用。不過讓人怒火中燒的正是這位知府在其判辭後面加上了一條足以摧毀整個傳教事業的內容:
無論何人,凡入教者應即刻脫教並焚書燬像。若執迷不悟,則應允保長及左鄰右舍檢舉告發,各甲長保長應每三月排查各門各戶,確保廂鄉內無教民留存後如實上報,如若有誤,則同罪連坐。為確保各甲保所言非虛,責成各縣府親歷親為,以官印為證。
這種舉措曾在本世紀初摧毀了日本的傳教事業。而如今,那些中國百姓眼中被當作是豺狼的芝麻綠豆官們,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搜查十字架和聖像的旗號任意搜刮凌辱基督徒了,而他們根本不該如此遭罪。
知府的判決送到布政使那裡,會同按察使和議後,按照巡撫的意思,除了有關處理殷鐸澤的內容外,核准了其它所有處理意見。對殷鐸澤的調查報告並不公允,諸如他是要來杭州定居等等,最終的處理意見是:必須將其驅逐出省,查封其教堂,將其發回最早落腳的江西省。特別是每三個月排查的那一條,布政使特別欣賞,認為這是禁教的絕佳手段。(頁58-62)
殷鐸澤向北京求救、索額圖介入、張鵬翮快刀斬亂麻的最終判決
此人正是出身高貴、位高權重、功勳卓著的索額圖(Sosan)。這位大人所有職務都擔任過,可以稱為一位偉人,他甚至擔任過十餘年帝國地位最高的閣老(16) (Colao)。他還是皇帝的姻親,皇太子母親皇后的舅舅,這讓他有別於其他朝廷重臣。聰明的頭腦、敏銳的洞察力、果敢的決斷力以及睿智和幹練讓其深受皇帝信任,朝中大小事務都會找他商議並委以重任。但是無論各方面有多麼的出色,相比其才智,索相的人品使之顯得更為偉大和平易近人,其本質上就是一位正直、真誠、公正、忠誠、慷慨並且很好的朋友。正因為張誠神父和其性格相像,這位親王在赴中俄邊境談判的旅途中亦有同感,他對神父的友情已至溫情和放開而且毫無忌諱的程度了。
張誠神父將畢嘉神父的信給索相傳閱,信中講到浙江巡撫無故自稱是基督教的宿敵,以貶斥該教為樂,發告示上公堂這些不公道的事情一股腦地加諸於基督教之上。張誠神父懇請索相阻止浙江巡撫的暴力行徑,對他說此事非得全仰仗大人您的庇護不可。索相非常客氣地說:“您大可放心,我曾施大恩於浙江巡撫,其不敢不從吾之命。您放寬心一切皆會恢復原狀。余之諾,必成也。”最後幾句話他重複了很多次。
事實上,索相一回到北京就立刻寫信給巡撫,要其與殷鐸澤神父言歸於好,糾正其所犯之過失。而且他為了不忘記和神父見面,還把張誠和白晉二位神父致殷鐸澤神父的書信放在龕盒裡以便自己親自處理。要讓別人都像浙江巡撫那樣桀驁不馴似乎太強人所難,他已騎虎難下,以至於現在又要讓一切恢復原狀簡直太丟面子了。因此,無論索相曾經如何提攜過他,他如何感恩索相,這件事情他都不打算聽命於他。索相寫了第二封信再次向他施加壓力,但是這封措辭嚴厲的書信也祇不過是使得巡撫不得已赦免了殷鐸澤神父並且允許其繼續在教堂居住而已,並沒有起到其它甚麼作用。他反倒覺得索相應該會對他的野蠻行徑感到滿意,應該會以為他在浙江搞得不會太過火。為避免再度接到讓他感到難堪的信,巡撫決定了結此事,批准布政使和按察使判決中的所有條款,內容摘要如下:
余查悉此類異書,據殷鐸澤供辭,乃印於萬曆朝。而今,是許之亦或禁之,雖尚未有明示,卻理應為西洋教士所獨存也。如若殷鐸澤無心宣教於民,蠱惑百姓入教為徒,又何須雕版印刻之?若眾人允其留板存之,須其許諾日後必當停印禁刊,然殷鐸澤竟明言欲一意孤行,一如往昔。故必燬之,以絕後患。布政使判決及每三月查訪之判令發佈之日起,若還有人膽敢散播異書,遂成教民,嚴懲不貸。若鄰舍和各保甲之長懈怠,則以包藏之罪論處,戴枷示眾。如此,皆為秉承聖旨而行之,皆因朝廷禁令而為之。由此,則正道歸心,邪謬皆廢。殷鐸澤所居之教堂雖非其所建,卻因久居日長,似如其所建也,故其留居似為宜。
Tchan-chaa 街之女堂,嘉興 (kiaa-him) (17)、海寧(18) (Haïnim)堂口,無論是否由教民資助西洋人而建,既已空置,兩地官府應予查封。余查得巴道明 (Sarpetri) (19) 曾居於金華(Kinhoa),康熙二十一年 (1682) 辭世。據金華和衢州所報,許伯多祿康熙三年 (1664) 既已入閩,同年潛居蘭溪教堂,巴道明偕其同赴京,終回蘭溪,廣東布政使遣其回浙,亦可為證。該堂典當而得,後贖回,許伯多祿購得一宅為教堂之用,今允其留居閉門研習禁行傳教。金華教堂既已售,則毋庸多言。衢州教堂得之不久,許伯多祿須遵從當地知府之命速售之,遂即回稟。Tchintasen領頭唆使教民違抗朝廷律令,杭州知府既已查實,務必嚴懲,帶枷示眾,以儆傚尤。(頁77-85)
康熙處置山東茌平縣教案的方式
山東茌平縣令不喜歡基督徒,欲禁止教徒行聖事,讓他們嚴守禁教詔令。暴力事件實已發生,遭罪的是法國耶穌會士汪儒望(Jean Valat)。他一直照管着當地教堂,作為最年長的入華傳教士之一,耕耘近四十餘載,成果顯著,實至名歸。正因為他愛戴信徒,所以致信在京的耶穌會士請他們阻止茌平縣的教難,並防止蔓延至山東其他地區。
皇帝似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烈感覺到耶穌會士在其身邊的存在,似乎很想找機會犒賞其一番。神父們都認為這是一次解決長期禁教的絕佳時機,他們有的很冒失,向皇帝進言道:“廣東官員,假借執法教民之口,實則擅妄加害於教民教士。早年吾皇年幼,所頒之詔令易損我教,今陛下若不廢,則將終日為官府肆意欺凌。承蒙陛下多年厚澤,今若陛下向天下示意護教,准行聖事,則必當感激涕零。”
這番講話為皇帝所不悅,他回覆他們勿為茌平縣縣令和山東官員的過激行為所困,他會讓他們停止迫害,下旨重修舊好,但是無論他有多麼關懷愛戴他們,傳教士都不可以妄稱皇帝是基督教的保護者,也不可以亂說他推崇基督教,其實中國人都搞不清楚基督教是甚麼呢,在這個問題上傳教士必須頭腦清醒,不要自我發揮過度詮釋。(頁100-102)
趙昌為在京耶穌會士向康熙傳話的經過
當時在京的耶穌會士祇有四人,分別是葡萄牙人徐日昇神父,佛拉芒人安多神父 (AntoineThomas) [則暫代閩明我神父 (Philippe-MarieGrimaldi)(20) 任欽天監副監一職],以及兩位法國耶穌會士張誠神父 (Gerbillon) 和白晉神(Joachim Bouvet) [他們被皇帝留在宮中受到特殊禮遇和關懷]。他們一面向上帝祈禱以求借助他的光輝成事,一面一起入宮請求覲見。(21) 皇帝對他們向來隆遇有加,雖然沒有召見他們,但卻派了一位侍從(22) [皇帝一般派這位趙姓大人傳旨] 見他們,以便可以更清楚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意願。
他們哭着對趙昌說:“朝廷既然禁教,臣等亦祇得向聖上請旨,按律嚴懲我等,一勞永逸,免留後患。若禁令延行,又或陛下臣民中凡信教者皆按罪論處,則臣等不得不揚帆回國。眾所周知,臣等離鄉背井,親朋好友,榮華富貴,一一拋於腦後,福音施佈天下,唯此獨願。陛下厚愛,隆恩不絕,無以為報。所尋所求,非名非利,敢受皇恩,皆為傳教,以平教難。禁教法理,援自律令,臣等請旨,廢此禁令,准傳教士自由佈道,臣民亦可皈依。若陛下准奏,臣等必當鞠躬盡瘁,以報聖恩。”
趙昌喜歡他們,願為効勞,於是速回稟明,皇帝不為所動,命其傳話給諸位傳教士:“傳朕口諭,命其等勿以有人為難你等為怪,教民望朕庇𧙗,卻又行為不端,自落官員問責之口實。浙江一案,朕會循山東一例密令處置,可寬心,靜待其候。”
諸位神父對此回覆頗為驚訝,於是相互商討此等微妙之時應取何等應對之策,他們發現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他們都處境堪憂:如果拒絕皇帝給予我們的恩典,就會將自己置於惹惱聖上的危險境地,將大難臨頭。如果我們接受的話,也祇不過是飲鴆止渴而已,到時候看到的還不是我們的教徒被官員們騎在脖子上任人凌辱罷了。換言之,要麼任憑事態發展而不顧,要麼按過去的辦法不斷上奏討皇帝嫌,但是這很有可能會激怒他。
如此路路不通,繼而苦無良策,難下決斷,他們祇得向上帝尋求指引,蒙受天主聖啟後便下定決心,圍着趙昌說道:“臣等行走宮內,全賴陛下庇𧙗,豈敢忤逆聖意。臣等不禁向萬歲爺稟告,祇為浙江一事已人盡皆知,不可收拾,刁難問罪起於天主教法未獲朝廷首肯之緣故。聖上明鑒,誠然我教不受律例保護,律令亦禁絕臣民入教,然欺凌侮辱仍將不絕。臣等唯有每每乞求陛下,惴惴惶恐,唯恐君棄。”(頁108-114)
耶穌會士求容教,康熙為傳教士改奏摺
雖然皇帝最後說的幾句話令人不安,他們還是堅信上帝必將助其成功,因此一心一意祇想着寫好奏摺。他們用漢語寫了兩份,裡面沒有指責浙江巡撫,也沒有抱怨其他人,而是申明:基督徒本質上並非不安和受害的代名詞,基督教從不教導任何違法亂紀、有違常理的事情,相反卻把最純正最高尚的倫理道德傳授於民。全國所有被禁的宗教裡面,唯有基督教遭到迫害打擊,這點並不公允。如果人們再去回味下基督教教誨的東西,毫無疑問就會不禁主動地為基督教辯護。
一週後(23),他們帶着奏摺去找皇帝,當時他還在南苑,正是為了趕在公開召見之前好心特意先見他們一面。皇帝召見,將他們留下,不過一句話也沒有和他們說,他的沉默讓諸位神父感到尷尬惶恐。
由於張誠和白晉二位神父每周都有幾天進宮陪侍皇帝研習物理和數學,將歐洲最新的科學發現告訴他,這樣他們就借此有利位置向他進言,跟他說他們斗膽,已將奏摺遞上來了。於是一向敬重他們的皇帝就跟他們說這些摺子不宜對外公開,硬讓漢臣(24) 接受他們的要求也不合適,他會再仔細看看,讓他再考慮考慮。幾天後他從南苑出發去另一處行宮(25),諸位神父自然不會忘記也跟過去,急切地想知道後續進展如何,但是皇帝依舊甚麼也不跟他們說,一直等到1692年的主顯節(26) 前夜趙昌到北京住院傳旨。
他把四位神父都叫過來,向他們傳話,皇帝意思是他們的奏摺還不足以說服人,所有辯辭都在說基督教的優點,這樣不可能讓那些仇教者印象深刻,還要再多點關注點,要知道有些事情不讓中國人為之動容是不可能讓中國人為之掛心的,皇帝意思你們用滿文再寫一份奏疏,要更加懇切點,符合國情更討人歡心點。張誠和白晉二位神父過去奉旨學習滿語,如今很是精通,立刻起草了一份,很快就交給了皇帝。
這次比上次等得更加揪心,那是因為他們擔心這位世上最英明的君主同意他們所請之後又會不會改變主意。他們這樣乾着急是沒有用的,因為上帝想要試煉他們的耐心,讓皇帝把這件事情忘卻掉,或者假裝把這件事情徹底忘掉,因為皇帝之後再也沒有提及過此事。他們覺得他是在等李國正 (Emmanuel Ozorio) 和羅歷山 (Alexandre Ciceri) 兩位神父入京,蘇霖神父 (Joseph Suarez) 奉旨去澳門接他們入京。皇帝接見了他們,對他們非常照顧,還很開心地收下了他們帶來的禮物,這些東西是以閔明我神父的名義送出手的,他當時還未抵達歐洲。這一過程中無論皇帝有多麼地堅信他可以給諸位神父更大的驚喜,卻始終都沒有提及有關容教奏摺的事情。神父們變得愈發沮喪,這是因為中國春節將至,事情的發展越來越遠離他們的預期了。
諸位神父為此很擔心,於是找人稟告皇帝,如果他不高興處理他們的奏摺,就很難分享到臣民節日的愉悅,等待他們的是一個悲傷的節日,而這個春節會因為浙江巡撫騷擾殷鐸澤神父,迫害教民而顯得更為悲慘。
皇帝捉摸他們提出的理由,反覆掂量他們謙卑的請求後,甚至親自操刀修改奏摺,整篇內容大幅改動,然後發還給他們。他讓趙昌向他們傳話,讓他們注意奏摺是否具詳細無缺,其等所請是否皆囊獲無漏,並於次日奉旨覲見。於是,諸位神父滿懷恩情地前去見皇帝,他們首先向他表示陛下聖恩和其無私庇護,其等心知肚明,然後又說既然聖上有心恩准其等呈遞奏疏,為承聖意,他們想要推遲規定提交奏摺的時間,對奏摺必須所做的修改也想要延後,次日是基督教的一個重要節日(聖母獻耶穌主堂瞻禮),如果皇帝恩准他們在那天把奏摺遞上去,他們定會感激涕零。因為聖母會在這一天將她的兒子獻給聖父拯救萬民,他們希望借此時機能為教難一事換取一個好兆頭,畢竟成千上萬靈魂的得救都指望着康熙頒佈容教詔令呢。(頁117-126)
在京耶穌會士遞上奏摺
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1692年2月2日)
向索額圖求助
人們可能感到詫異,奏摺中竟絲毫沒有一點褒揚基督教的地方。皇帝想要助他們成事,為此覺得那些讚美基督教的陳辭自當難以為漢臣所接受,不如換成他授意的那些還湊合,況且諸位神父一心祇想成事,都依附於他。
皇帝循例將此奏摺發往內閣 (Tribunal des Colao)(27),兩天後再發往專職處理宗教事務的禮部,命該部商議後回奏。由於皇帝須赴皇陵祭祖,且封印期將至,禮部無暇會題議奏,祇能等到開印之時的三月初。
皇帝的作為讓大家信心倍增,希望滿滿,諸位神父相信他尊重基督教,願為其出力。他們在禮部也能找到支持者,兩位禮部尚書(28) 似乎便是,正因為他們地位重要,大家相信他們不會不引導其他大臣跟隨他們支持容教。大家覺得這件事情會更加好辦,主要是因為尚書之一的顧八代(29)某日宮中遇到張誠神父,一邊上去擁抱他一邊跟他說事情他會放在心上的,對他其本人很滿意。大家還得依靠熊賜履(30) 大人,他可是閣老,亦同為禮部尚書,他不久前剛回工作崗位,期間中斷了二十七個月,因為他的母親去世,他必須回南京奔喪。在其留居該城期間,其與畢嘉、洪若翰以及劉應神父交好,並送禮往來,他同諸位神父經常討論基督教,其論道的方式讓他們覺得這位大人距離上帝之國並不遙遠。一次偶入教堂,其見十二門徒畫像,遂讓人複製置於宅內其中一間類似於禮拜堂的房子,這讓人相信他已是教徒了,流言隨即傳入宮中,連皇帝都向諸位神父詢問原委真假,熊賜履回到北京後,他待在京耶穌會士不比待南京諸位神父為差,因此諸位神父相信這件事情他不會不幫忙,對他亦同樣意義重大。(頁137-141)
索額圖會見浙江巡撫派赴北京
向其解釋原委的官員
張誠和白晉兩位神父某日前去拜訪索相,求他在皇帝面前美言幾句,讓他的朋友們都來支持這份奏摺。索相很樂意幫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對浙江巡撫非常不滿。封印期前幾天,巡撫反覆思量過去他對索相的行為和態度後,派了一位官員赴京拜見他的這個靠山,對於之前索相寫給他的信做一個交代。這位官員向索相表示巡撫對他感恩愛戴之情無以為表,請他相信針對殷鐸澤和教民的行動中絕無過火行為發生,他所做的無非是為了堅決執行皇帝詔令,不讓他們在房門上放上些具有煽動性的東西,並且阻止他們焚燒祖先畫像和牌位,以免引起國內的混亂。他如此關注此事,也是為了遏制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為此懇求索相轉告殷鐸澤盡責管束教民,勿在該省挑起教難。
巡撫的心思索相一清二楚,才不會被他的花言巧語所蒙蔽。他深知基督徒不會落人口實,沒有理由對他們嚴加打擊。教徒百年來都把耶穌的名字貼在房門上以同他戶相區別,其他人家門上貼上偶像崇拜的圖像就沒有人說三道四覺得是一種犯罪,還有甚麼比之更無辜的呢。此外他也深知基督徒焚燒祖先畫像牌位有錯,不過教徒也是完全按照律法和習俗的規定根據世俗禮儀拜祭他們已故雙親的。他也知道巡撫如此誹謗是為了詆譭他們,是要他們為這個嚴守執着這種古老禮儀的國家所不容。他也不會不清楚巡撫指教徒圖謀不軌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為大家甚至於都不會去懷疑過他們會怎樣,巡撫在對付他們的過程中也沒有專門提到這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祇要教徒給他找到哪怕一點點藉口,因為他用心險惡,早已派人秘密潛入宮中散佈謠言說基督徒有圖謀不軌之心。
索相崇尚正直和公正,很不滿巡撫的狡詐和壞心眼,又一次寫信教訓他並且對前來解釋的官員生氣地說:“爾主不配與人為友,受人恩惠。西洋教士,終日侍奉皇上左右,德行備受聖上讚許,爾等如此苛待,實為昏愚。今吾執筆,非諂媚於洋人,祇為救他,免觸聖怒。伊不從我,不聽我命,你傳話於他,彼之惡行,終召我棄,就當從未相識,一了百了。”索相言辭激烈,令這位可憐的信使惶恐不安,連忙跪下不停磕頭,請求他息怒,勿遷怒於巡撫,依舊一如往昔地關照他。生氣的索相不想聽他解釋把他打發走了。 (頁142-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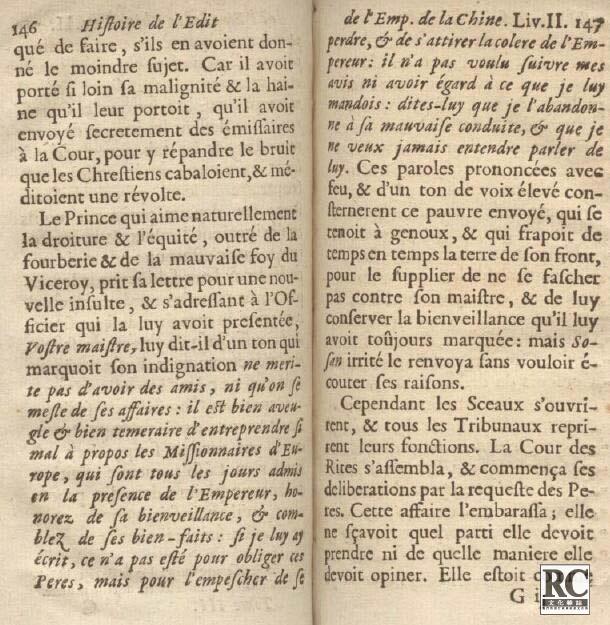 |
|
索額圖會見浙江巡撫派赴北京向其解釋原委的官員 (其中的斜體字部分是索額圖訓斥官員的話)
|
禮部拒絕赦教、傳教士試圖再次上奏
康熙對此態度前後的轉變過程
他們都愕然了,這絕非他們所期待的結果。他們不敢相信皇帝為他們做了那麼多事情後居然拋棄了他們,神父們還指望着他,幻想着他在批准禮部決議後前還會留心修改下,他們都是這麼想的,因為當時他們知道皇帝沒有按例將此決議發往內閣(Colaos)。他們最終發現自己判斷失誤,是於次日去皇帝所在的南苑為其講解物理數學並且回答前一天皇帝所提問題的時候。他假裝對他們噓寒問暖,比以往更加關懷備至,事實上這樣堵住了他們的嘴巴,讓他們相信他們是那麼得得寵,皇帝是不會不插手的。但是他們不久就發現不對勁了,因為第二天他們就知道皇帝已經批准了。
這對諸位神父而言簡直就是晴天霹靂,他們驚愕不已,備受打擊,深陷苦楚之景象無不為其諸友所動容。由於皇帝可能就在這幾日回京,他們決心面聖陳情,入宮後他們對趙昌說:“我等淒苦哀鳴之態、大人已見。滿心期待,卻慘澹收場,是該如何為好?從今往後,聖上萬千恩寵於我等又有何用?受人凌辱不得翻身乎?有何臉面見同僚?歐洲故里該如何視我等乎?如今聖上依准,萬民禁行我教,然我等曰來此祇為傳教,豈有人信乎?又或曰,皇上聖明,明察秋毫,隆寵厚待,何故此等小惠拒施於我教,天下焉有此理耶?必是在京教士,以隨駕侍奉為耀,貪戀權位,故而懈怠教務。遂請大人容稟,如今臣等孤苦,生不如死,國之浩大,卻容我不得,不如一死,免遭罵名。”他們把所有能想到有關於痛苦的詞一股腦兒地都加了上去,終於到最後他們的意思是要求皇帝恩准他們再上一份新的奏摺請求赦教。
趙昌待他們向來不薄,不過也不想攬下此事,以免觸怒聖上,因為他也不知聖意究竟為何。他嘗試安撫他們,為了哄他們,還建議他們再度上疏,密封後他想辦法將其秘密呈上。這個法子並沒有要趙昌使甚麼陰謀詭計,而他也沒有幫神父這個忙,因為除了他長期插手此事外,更重要的是未獲允許就這麼做的話太過危險。因此諸位神父央求趙昌一定要讓皇帝徹底搞清楚其等想法,他們死纏爛打,趙昌拗不過也就答應了。
萬歲爺直到入夜才回宮,由於他直奔其祖母孝莊文皇后的故居,一直苦等他的諸位神父見不着他,祇得回去了。皇帝一回到寢宮就問趙昌他們是否來過,趙昌回答說:“一直候着,直到丑時,奴才費得九牛二虎之力方得勸伊等離去。”皇帝接着問:“說些甚麼否?”趙昌回奏:“其中一位病得半死,其他未言片語,皆恍若神形俱消之態,着實為人噓唏不已。”他利用這個絕佳機會說盡好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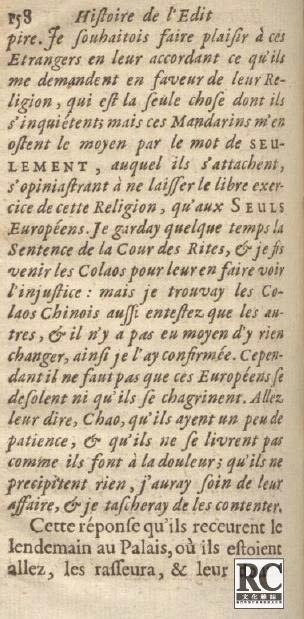 |
|
禮部拒絕赦教,傳教士試圖再次上奏康熙對此態度前後轉變過程中談到漢臣阻撓容教的原話
|
皇帝很注意地聽着,神情自若,然後轉身對在其寢宮侍奉的人說:“朕不知漢臣針對西洋人之所為,雖已明示有意容教,不曉伊等執着依然。外國人乞求容教,乃唯一掛心之願,朕意許之。孰知伊等好用‘止’字(31),以此駁回,議得天主教止令西洋人供奉。朕留禮部決議多時,傳召諸位閣老(32) 前來以正視聽,豈料閣老中之漢臣亦同樣拗執。既已無迴旋餘地,朕亦唯有依議從之,然致其西洋人等傷懷悲鳴亦屬不該。趙昌,你傳朕口諭,着伊等耐心等待,切勿自棄,此事朕自當掛心,盡力了卻伊等心願就是。”
第二天諸位神父入宮獲悉了皇帝答覆,這讓他們心安並且重燃希望,催促着趙昌利用如此有利時機替他們說好話,他們對他說:“煩大人稟呈萬歲,臣等境遇眾人皆知,今日抱怨之深,遠甚於楊光先時期,皆因當年正逢顧命大臣臨朝,借陛下年幼,視我等為邪教,唯有仰望聖上快快親政,以平波瀾,還我公道。待之今日,皇上統御四方,惠澤四海,聖名遠播,萬民敬仰,任用臣等効命朝廷,隨君奉駕,榮寵萬千。臣等所盼,唯容教一願,卻為人所阻,日後我等有何指望?豈非終日為人所譏諷輕視?任憑我等同僚於各省為人凌辱?必有人折磨教民,以嚴酷報仇之法迫其等絕棄我教,異日必當生不如死。我等已淚盈奪目,懇請大人將我等慘狀稟明聖上。”
趙昌回去後向皇帝如實回稟,君為之動容,再派其前去撫慰諸位神父,讓他們放心皇帝會保護他們的。幾天後他們親自前去謝恩,見到皇帝後,滿肚子的苦水一股腦兒地向他傾瀉而出。皇帝英明,深明諸位神父如此之用意,其等盡忠職守,無非祇是為帝國可以容教而已。
當時還有一件事情對於說服皇帝作用不小。諸位神父心情沮喪,如果他們的請求得不到滿足,傷痛就會久久不能平復,就在這時皇帝知道了有一位意大利年輕人(33) 不久前剛剛抵達澳門,此人擅長醫術,而皇帝也研究解剖學,心醉於西方最新之發現,很想見見他,於是便命廣東總兵護送諸位神父中的一位陪同其進京面聖。
神父們婉拒推諉,回稟說他們不敢公開露面以免引起混亂,如果這個時候動身的話,他們不忍直視各地傳教士教徒淒慘之態。正因為基督教在諸位神父看來比他們在世上所擁有的一切都要珍貴,所以他們絕對無法對傳教之凋零熟視無睹,這倒並非是說教難之痛甚於父母摯友故去之痛,因為諸位神父正是為獻身於天主才棄他們而來的。(頁152-163)
康熙和索額圖的對話
皇帝見狀,為之感動,決心盡快准其等所請。他知道索相是諸位神父的朋友,於是傳召其入宮,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索相自然完全站在神父們那邊,他向皇上請示,皇帝對他說:“漢臣執意止令西洋人供奉天主教,致伊等惶惶不可終日。”索相回話:
陛下竟受如此對待?漢人妄自尊大,何時起竟敢如此忤逆聖意?洋人得蒙聖眷,不亦陛下厚澤乎?伊等奉君,由來已久,且盡忠職守,今陛下庇𧙗,受之無愧。漢人食古不化,何以貶斥天教?奴才細查,通覽教義,未覺其有何異於道法自然者,唯仁德忠是也。視其邪教者,未得其旨也。倘若舉國皈依,俱奉其法,則匪寇亂黨盡消,亦無需為固江山,竭耗養兵無數。萬歲爺登基三十載,何人可曾參奏各省西洋教士教民乎?伊等犯蠱惑之罪,安在?責其等煽亂,可枚舉乎?奴才蒙聖睿鑒,位列議政大臣之內,十餘年來,未聞絲毫他人檢舉之訊。喇嘛教、佛教、道教、回教,諸教廟宇,何等壯麗,欲建則建,見怪不怪,何人異議?而今天主教,任憑其教義何等純正,任憑其禮法何等神聖,任憑其教化何等裨益於安邦定國,唯獨天主教漢人不屑一顧,天下豈有如此不公之理乎?
陛下聖明,深蘊驅西洋人不遠萬里來此動機唯傳教是也,絕非貪圖名利權位者也,眾人皆欲圖之,獨其等不為所動,又無妻室兒女,無人可繼享其業。其等所求,無損道法,亦無害於朝廷福祉,若駁伊等容教之獨願,則絕非激勵伊等來華効命我朝之良策也。陛下記得西洋教士治理曆法,殫精竭慮;吳三桂造反,南懷仁鑄炮有功;又有人等差往沙俄,行文翻譯以襄助和談,正如奴才過往所奏,全賴伊等傾心辦差,朝廷才免於一戰。臣請陛下施天子之權,容教開赦,勿再推遲。
皇帝打斷他:“有理,然赦令已出,朕亦依議,為時已晚,另有辦法否?”索相回話:“聖上是主子,主子有命,臣子必從之。陛下再不援手,唯恐西洋人西歸不復返。”
皇帝沉思片刻,似乎有些猶豫不決,不過忽然一個轉身,對索相說:“朕意已決,命禮部重審來看,禮部各員,諸位閣老,由你遊說,務必讓伊等公允處事,寬容赦教。爾所奏之言傳於諸臣即可。”索相回話:“尊旨,這就去,奴才有理而身正,定當傳話到。”(頁163-169)
索額圖對官員們的講話
與此同時,為爭取禮部,索相的勁頭比傳教士還要足,他恩威並施,在和幾位主要大臣談好後,他去找禮部官員和諸位國老,他們聚在一起,索相把皇帝的話重覆了一遍,之後他發表講話:
諸位大人,天主教道法自然,爾等何以驅之出境?諸位大人自當公道明理,請問某教法導人敬天,驅民忠君,勸婦從夫,教子順長,亦教導主子之命有理,奴才不可不從,仇視命官,違抗朝廷,怨懟他人,放蕩不羈,該教法皆禁,爾等何以禁之?某教教旨純正,導人向善,反之邪魔歪道諸位大人倒容得下,何以爾等拒之?就是論事,杭州城內回教徒所建之堂,其恢宏壯麗,其它建築不也是難以匹敵嗎?其他教派城內無堂?天主教篤行至善,何故獨其驅之以為快?諸位大人,捫心自問,西洋人來此為朝廷効命,功不可沒,然我朝視其為邪教竟不堪忍受之,公允否?眾人皆知,朝廷任用西洋人觀測星宿,修繕曆法,你等還曾記得三藩之亂,尼布楚議和,我朝佔盡上風,全賴伊等之功。西洋人若名不副實,談判何等大事,余拗勁委其等重任,豈非自毀英明,你等信否?萬歲爺受命吾欽差大臣,若論功行賞,看似余自當首功,將心比心,不敢攬功,理應俱歸於西洋教士。罷了!諸位仍有異議,大可提出共商榷,若無人反對,余請諸位秉公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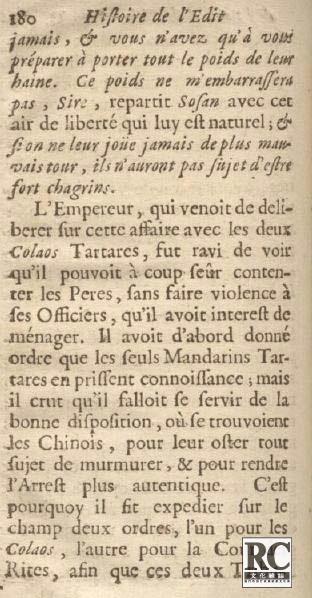 |
|
索額圖對官員們的講話索額圖向康熙奏報同禮部官員會談的情況,康熙和他開玩笑說,你這般對官員疾言厲色,他日可要小心!
|
索相身份個性使然,充滿火藥味的這番話讓在場的人為之一驚,漢臣們亦不得不承認他說的話沒甚麼不真實不公道的,他們並不是厭惡西洋人和天主教,直至今日他們都認為不該允許朝廷容教,這是因為天主教是洋教,由西洋人主持施道,他們有理由憂慮一旦開此先例,很快全國各地就會有許多人入教。索相回覆說:“敬天,自當舉國從之,唯天命是從。屆時各地姦淫擄掠俱無存,家家貧富紛爭盡勾銷,官官相輕亦不見,盜竊亂賊而不作,天下為公,是為大同,天朝威武,舉世無雙。”
他又一次發言讚美天主教,慷慨激昂又鏗鏘有力,說服了那些最固執的人,大家不再反對甚麼了,之前態度最強硬的官員此刻也熄火了,這定是上帝沁入他們的心扉,讓他們回心轉意順從了主。現在這些官員都異口同聲同意傳教士在國內自由傳教,百姓亦可以皈依天主教了,於是立刻擬旨上呈皇帝。
大獲成功的索相很高興,離開會場向皇帝彙報情況去了。他向皇帝保證漢臣都已就範了,他發覺他們和滿族官員一樣老實了,皇上就等着他們請旨即可心願成矣。皇帝笑了,然後開玩笑地跟他說:“如此發作,漢臣絕不會善罷甘休,等着日後穿小鞋了。”索相泰然自若,回話道:“回萬歲,穿小鞋算不得甚麼,若不給點顏色,伊等定不會明瞭孰輕孰重。”(頁173-180)
禮部通過容教詔令,索額圖督陣
皇帝剛剛和兩位滿族閣老商議此事,現在看到可以確保讓神父們滿意,同時漢臣亦未受責而感到高興,兩方面都顧及到了。一開始他祇打算讓滿臣議事,但是他覺得還是要左右平衡,畢竟還有漢臣在,一方面要讓他們緘默,另一方面又要讓詔令服人名正言順。因此他立刻下了兩道命令,一道給諸位閣老,一道至禮部,以便他們一道議事。
於是大臣們遵照皇帝的命令於次日在宮中開會,皇帝希望索相亦親自到會見證整個過程,同時也完成其親啟的這一偉大事業。大家都不敢有違索相的意志,字字斟酌,都同意後,草詔就唸了出來,皇帝的意思完全體現出來了。今日,正由於這份詔令已享譽全國,終於傳教士可以自由佈道,人民可以皈依,教民可公開供奉了。
索相和王熙當時對諸位神父還是關懷呵護的,前者受皇命列席會議,在擬詔中加入了兩點:天主教勸民忠君,子從父母。忠孝是中國人所有美德中最突出的,會議宣讀結果的時候這兩點是有的,但是後來皇帝按慣例將此令發回給他們的時候被某位閣老刪掉了,大家都沒有察覺。在皇帝批准其生效後,神父們才發現上當了,還好這一點也不是太重要,更何況大家想的不都做到了嘛,於是諸位神父也就不打算再和皇帝提及此事了,息事寧人作罷。
索相原本加在裡面的一句話:差往阿羅素,幸得伊等而成其事,改成:差往阿羅素,誠心効力,克成其事。託王熙的福本來還加上這句:天主堂凡人皆可行走供奉,或者說是:凡人即可成教民。這些話本來都已經敲定了,但是到手的詔令上卻含糊其辭,表述歧義。
皇帝曾經訓斥閣首(34) 第一次的時候沒有順他的意,如今看到事情得到圓滿解決非常高興,他第二天問趙昌諸位神父是否已知曉,趙昌回話說:“回萬歲,詔令副本伊等剛剛交予我手,其等感恩欣喜之情,史未所見,迫不及待恭候陛下准奏。”皇帝說到:“伊等盡本分傳教,朕自當許之,樂聞其祥。”
皇帝批准的日子是1692年3月22日,這天對於天主教而言可謂倖哉,因為正是這一天標誌着天主教擺脫了百餘年來的奴役,從皇帝年幼時親手為天主教套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頁180-192)
【註】
(1) 原註:中國最早的儒家學者之一。譯註:原文為Tchéoucoun。
(2) 原註:中國人將孔子視為老師,他比我們的主誕生早500年。譯註:原文為 Coun-tçé。
(3) 原註:孔子和其弟子孟子的著作。
(4) 原註:五經是中國的經典,李明神父在其新書《中國近事報導》中已有提及。
(5) 原註:這個朝代建立於1369年,歷經十六位皇帝統治共計二百七十六年。
(6) 原註:1581年。
(7) 原註:本朝為大清(Tai-cim),是統治中國的第二十二個朝代。
(8) 譯註:參見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398。
(9) 原註:第一本書由耶穌會士艾儒略神父所著,是一本全面介紹基督教的讀物。第二本由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於南京教難時期在澳門所著,他在那裡於1618年去世。譯註:《天主律法釋》原文為 Explication de la Loy de Dieu,蘇霖神父的《1692年康熙容教》也有張鵬翮禁教令的全文,不過未提及這本著作,至於到底是艾儒略神父的哪本著作待考。《七勝》原文為 les sept Victoires,在蘇霖神父的《1692年康熙容教》中梅謙立教授譯為《聖神七恩》,根據郭弼恩神父原註提供的資訊,應排除這本書是龐迪我神父的大作《七克》,因為《七克》成書於1604年,而非南京教難時期所作。比較確切的是郭弼恩神父在下文記錄殷鐸澤神父的辯辭和浙江官員的禁令中都提到這兩本書都在萬曆年間已有刻版,本譯文取直譯以進一步待考。參見G.G.萊布尼茨著,楊保筠譯《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第頁23。
(10)原註:巡撫注意到安息日和基督教節日新皈依者嚴格遵守其中的教規。譯註:所謂不務正業,指的是基督徒在週日和基督教的齋戒期內不工作。
(11) 譯註:原文為 le Juge Criminel de la Province。
(12) 原註:原文為 le Lac délicieux。
(13) 原註:“老人家”在中國是褒義詞。譯註:據《熙朝定案》所載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殷鐸澤和潘國良兩位一同覲見康熙帝,而非殷鐸澤一人,皇帝對其二人說的原話是:“送君千里終須別,老人家好好住在這裡。”參見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173。
(14)原註:中國印刷業和我們西方完全不同,我們印刻的字元不多,不難用板將它們組配起來;但是在中國,他們有超過八千餘個字,這樣配頁是無窮無盡也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們就用和我們一樣的辦法把字刻在木板上烘焙,用的是銅板印刷法。
(15)譯註: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張鵬翮任浙江巡撫起至杭州教案結束的時任杭州知府是:魏麟微,溧陽人,進士,康熙二十八年到任;苏良嗣,奉天人,康熙二十九年到任;李鐸,奉天人,康熙三十一年到任;参见民国十一年《杭州府誌》,卷101,頁1954。
(16)譯註:指的是索額圖於康熙九年八月從國史院大學士改任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至康熙十九年八月因病解職改任內大臣、議政大臣的十年。康熙二十五年授領侍衛內大臣,康熙四十年九月退休。
(17) 原註:巡撫至此下令將兩所教堂改建為關帝廟,如果覺得太小的話,則改建為學堂。
(18) 原註:上述所說的地方都在浙江省。
(19)原註:多明我會的巴道明神父曾在楊光先教難時期被囚廣州,他曾寫過一篇關於中國人祭孔祭祖的文章,人們可以在中國經典和新教徒的辯護書中找到這些相關的內容。
(20)原註:閔明我神父奉旨出使俄國,他接替南懷仁神父成為欽天監監正,在他離京期間皇帝讓徐日昇和安多神父共擔其職。
(21) 原註:1691年12月22日。
(22) 原註:大家一般稱呼他趙老爺 (Chao-laoyé)。譯註:其真名趙昌,是康熙的近身侍從。有關趙昌研究請參見陳青松〈趙昌家世及其與傳教士的往來〉,《亞洲研究》(韓國)、2009年第8期。
(23) 原註:1691年12月28日。
(24) 譯註:原文為 les Mandarins Chinois。
(25) 原註:距京1.5里遠的暢春園 (Tcham-tchun-yven)。
(26) 譯註:羅馬天主教的主顯節是1月6日。
(27) 原註:國務會議,帝國最重要的機構。
(28)原註:滿族入主中原後,沿襲前朝制度,留用漢臣的同時,還任用滿族官員充斥所有中央及各部,由此每一部都有兩位尚書,一滿一漢。
(29)譯註:顧八代,滿洲鑲黃旗,伊爾根覺羅氏,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接麻爾圖任禮部尚書,三十二年做事革職。可參見朱彭壽著,朱鼇、宋苓珠整理《清代大學士部院大臣總督巡撫全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8月,頁194。
(30)譯註:熊賜履,時為大儒。康熙十四年遷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二十七年授禮部尚書,二十九年丁憂期滿複職,三十一年改禮部尚書,三十八年遷東閣大學士。可參見朱彭壽著,朱鼇、宋苓珠整理:《清代大學士部院大臣總督巡撫全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8月,頁115、194。
(31) 譯註:原文為 seulement,意為“祇”,而“止”同“祇”,“止令西洋人供奉,俟命下之日,行文該撫知照可也。”參見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頁184。
(32) 譯註:原文為 Colaos 和 Colaos Chinois,文中分別泛指內閣學士和內閣學士中的漢臣。
(33) 譯註:盧依道 (Isidore Lucci) 意大利耶穌會士,1691年入澳門,擅長醫道,為康熙所用。參見費賴之《明清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11月,頁544-545。
(34) 譯註:閣首原文為 le premier President des Colaos, 應該意指大學士排名之首的王熙。《清史稿》卷174表14〈大學士年表一〉記載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四十年,王熙一直居於大學士之首。
* 謝子卿,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