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僅對澳門語言文化的歷史狀况提供一些尙未被本地學者吸收消化的腳註資料,期望藉此引起決策階層對澳門歷史失語症有所警覺。
澳門的歷史失語症是文化整合的負量現象。但倘把澳門跨世紀的文化整合祇看作是一種區域性邊緣文化的偶然現象,那眞是小題大作了。澳門的文化整合具有眞正近代史意義和世界全景色彩的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宏觀視野(1)。這個課題在目前顯得太迫切了。
語言作爲一種文化現象是各民族文化的傳承載體,且構成各民族文化的基礎和精華。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認爲,無論從哪方面考察,文化都離不開語言。薩丕爾認爲: “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自給自足的。”(2)不僅語言對文化變異有很大影響,文化對語言形式亦產生很大影響。文化差異和語言差異顯現爲互爲鏡像折射的映照關係。因此,布龍菲爾德認爲各族語言是取長補短的。(3)人類文明發展史可以被描述爲一部各民族各社團交際接觸以及各種文化碰撞交流的歷史。社會語言學作爲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其特點是通過種族、語言、文化三個綱目來硏究人的社會存在形態,“高度重視語言變異中社會文化因素,尤其注意到社會文化因素的變異”(4)。現代語言學理論値得硏究澳門文化的學者們借鑑。
令人不無遺憾的是,迄今仍然相當缺乏對澳門進行跨文化的語言硏究和跨語言的文化硏究。僅就語言對文化變異的作用而言,加強這方面的硏究毋疑“將會促進文化人類學、社會文化學、民俗學、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等學科的繁榮”(5)。語言形成史與多語發展史表明,文化因素的作用遠遠超過任何政治因素。倘對澳門過渡期的語言政策單從政治因素方面考慮,恐怕將會造成因小失大的歷史性失誤;因爲跨世紀整合的澳門文化無疑是中華文化圈最具開放型因子的精彩部份,它同時也是現代人類文明的一份珍寶。
在這個時候,對澳門歷史失語症的追溯和描述並非沒有現實價値。從共時性方面考察,目前澳門社會存在着極度混雜和彼此隔閡的多語現象。常見的“失語症”三種症候在澳門也幾乎隨處可見: 第一種表現爲言語表達困難,含糊其辭(6);第二種則滔滔不絕,但言之無物(7);第三種是永遠聽不懂別人說甚麼,祇認識官話之類的書面語(8)。以上三種“失語症”往往不同程度地糅合爲三位一體的综合症候群現象。無論在澳門的官方文牘、議員辯論或新聞傳媒、民間輿論等形形色色的對話方式上隨時都有不同程度的異常表現,其中有一部份表現爲語義轉換的先天性困惑,一部份表現爲遺傳性的語言功能障礙,一部份表現爲言不及義的表達機制擾亂。上述情况甚至嚴重到即使使用同一語種的不同社團之間亦存在明顯差異,語言障礙和文化鴻溝幾乎成爲澳門文化的一種特色。澳門多語流通的混雜現象可從澳門一位華人學者講述自身經歷的一個片斷中得到生動的印象:
一位世伯母出生於廣東石岐(屬中山縣),抗日戰爭時移居澳門,在澳門期間將其女兒嫁給葡國人,後來世伯母又到美國住了多年,再回澳門,她的口語混雜多種語言成份。她在請客吃飯時對客人說: “tudo冚唪冷〔 ltu’gΛda: 〕食晒佢! ” 冚唪冷是粵語,“tudo”是葡語“統統”,〔
ltu’gΛda: 〕食晒佢! ” 冚唪冷是粵語,“tudo”是葡語“統統”,〔 ltu’gΛda〕是帶石岐方音的英語al-togther,“食晒佢”是粤語“吃完它”。(9)
ltu’gΛda〕是帶石岐方音的英語al-togther,“食晒佢”是粤語“吃完它”。(9)
澳門當地文化與外來的葡萄牙文化以及英美文化在不同關係上有不同程度的互相滲透和互相影響。澳門一些葡人學者認爲: “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上,澳門之特有文化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南方的);作爲與西方貿易之通商站而產生具本地特色之中國文化,由佔人口百分之二的土生葡人所認同的葡中文化;葡式行政文化及受香港影響之英美式商業文化。(10)在這位葡萄牙人的眼裡,在澳門分明存在着不止一種的“中國文化“和不止一種的“西方文化”。對於澳門的葡萄牙人來說,面對“不同的”中國人和“不同的”中國文化往往無所適從。目前在澳門的葡萄牙社會流行一句俏皮話: “在廣東話及普通話之間,葡語同時並存,卻不是選擇的範圍……”。他們認爲由於在過渡期中發生形態上的轉變,而導致損失,將是“悲哀及令人憤怒的”,並覺得“在轉換中若葡語與澳門脫節”,這將是他們“文化的哀痛”,因爲“葡語在澳門,將趨向於以文學的方式而存在”。(11)
無論如何,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眼裡,澳門始終是一座“中國城市”。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一位葡籍敎師馬丁士(Maria Aline de Sousa Martins),是這樣看澳門的:
……我們可以說澳門是一座中國城市。除去2%或3%的外國人之外,其他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構成了這個城市最真實、最牢固的部份。作爲能顯示由誰在領導一個地區的思想及活動的宗教證實了這一點: 中國的廟宇雖然有時藏於深巷,有時破爛衰敗,但在澳門和離島還是佔據着主導地位。作爲社會生活的另外一非常重要的主體的市場在澳門也是無可爭議的中國式。市場最初的建築(一般市場因之而得名)可以在風格上具有鮮明的殖民地色彩,但市場走出了建築,擴展到了狹窄的街上,構成了一座東方式的迷宮。(12)
然而更令人發迷的是這座“東方式迷宮”裡的中國人各自操着五花八門的方言,其中包括粤、閩、吳等方言區的形形色色的“方言中的方言”。單就澳門的粵語而言,“它與廣州話、香港話共屬一個系統,尤其與香港粵語接近,祇是個別詞語與個別聲調的變調略有差別”。(13)這種“略有差別”之中郤包含葡語和英語的影響,後者甚至形成所謂的“Chinglish”。(14)至於澳門的中國人所使用的書面語甚至令此地大學的外籍敎師也感到沮喪。
作爲一個外語老師,很明白澳門的情况。澳門受歐洲文化模式影響很大,大部份學生,包括那些就讀文學院的學生,對於中文認識程度很低。事實上,視聽文化已取代了文學文化,導致母語的掌握亦隨之而變得貧乏。尤其是書面語不可與廣東話結合,因爲廣東話祇是中文衆多方言的其中一種。(15)
由於澳門多種語言的習得行爲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而形成種種差異;又由於生存空間的限制作用,一方面出見異質涵化現象,另一方面出現同質異化現象。這種逆向轉化的變異現象不單出現在中西(漢語和葡語)兩大語種上,作爲兩種母語各自的子系統之間也出現了文化變異。恩伯爾的觀點認爲,基於“地理隔離”(geographical separation)標準,應把那些不居住在一起但說同一種語言的民族描述爲不同文化。因此探討澳門歷史失語症起碼的兩大課題: 一個是蛋(蜑)家一族的失語症現象,它表現爲澳門“史前”土籍居民的漢化現象;另一個是土生葡萄牙人的失語症現象,它亦表現爲澳門葡籍居民在四個世紀逐步“漢化”的現象。它們可作爲澳門文化跨世紀整合的生動例證。
在葡萄牙人發現澳門之前,此地是屬於香山鎭的一個小漁村。在宋朝香山鎭爲東莞轄地,包括浪白滘(大嶼山)和珠江口零丁洋諸小島,皆爲當地漁民活動的區域。迄今澳門粵方言仍稱“水上居民”爲“蜑家”(俗寫成‘蛋家’)。
唐時已有“林蠻洞蜑”的記載,陸居山林,逮宋以降遂“游居水上”,以艇爲家。郭棐《廣東通志》卷七十有蜑民於“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潮尤多”之說。蜑民之中有一種稱爲“蠔蜑”的,以捕漁採蠔爲業。澳門原稱蠔鏡嶴,爲珠江口聞名的牡礪產地,應爲“蠔蜑”謀生活動的重要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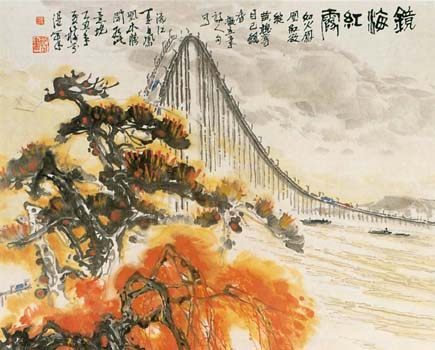
鏡海紅霞 (中國畫) 嚴樹芬作
民族學者公認蜑民、輋民(畬人)、傜民三者同源。有人說廣東的輋人始於宋末。其實無論是傜民、輋民或稱爲蜑民者,皆爲南粵古稱“百越”的土著。番禺雖自趙陀開闢,而至東晉“始染華風”。《永樂大典》卷一一九○七引《廣州府圖經志》說: “至於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自是以來,漸染華夏。”(16)到了宋代,廣東境內“仍多蠻區”。淸代雍正年間尙有記載說: “粵東地方,回民之外,另有一種蜑戶,猺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17)周去非《嶺外代答》有“蜑蠻”條云: “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蜑也。欽之蜑有三,一爲魚蜑……二爲蠔蜑……三爲木蜑。”(18)被漢人視爲“四民之外”的蜑民,不是“獸形鴂舌”就是“椎形裸體”(19),本身沒有任何文字,”一切記載,靠漢人代書”。由此可以想象,早在1513年有個叫做喬治·奧維士(Jorge Auares)的葡萄牙人“第一個由海路踏上中國大地”(20)的時候,那時的蠔鏡嶴仍然是“蠔蜑”、“魚蜑”“木蜑”聚息活動的小漁村,他們那“南蠻鴂舌”的言語會有何等景象。
現時澳門流行的漢語方言勢頭最大的是粵方言和閩方言。早在十六世紀之前,閩語即隨媽祖娘娘在澳門西灣內港口登陸。首批葡萄牙人在澳門聽到的中國話可能就是媽祖娘娘的鄉音。其時在南海沿岸珠江口一帶活動的“水上居民”除了“蜑家”之外,還有稱爲“鶴佬”的。“鶴佬”即閩音“福佬”尤其跟福建的興化話接近,海上漁民的保護神媽祖娘娘就是莆田媚州嶼人氏。葡人學者路易(Rui Brito Peixoto)論文《中國南部社會群體差異初探》一文中有關於對“鶴佬”的猜測:
“鶴佬”講的是從福建話派生出來的一種變異的方言,對這種語言的描述是很少的,它同潮洲(Teochiu)方言相似,但是“鶴佬”講的這種方言當地人聽起來是有些困難的。講這種方言的幅射中心似乎從福建省一直延伸到廣東省北部沿海地區的Swaton 和Swamei地帶。然後又從這一中心向東北沿着福建省的海岸,向東南香港地區分佈開來。在這些地區,“鶴佬”在當地整個渔民團體中祇佔極少數,因爲他們主要都集中在Tai po地區。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以澳門地區爲基地的“鶴佬”核心體,但這並不是排除“鶴佬”可能也在澳門有他們的代理人。(21)
其實,路易只猜對了一半,即“鶴佬”使用的閩方言,但他完全疏忽了的正是“鶴佬”恰恰成爲歷史上“以澳門地區爲基地”的“核心體”。澳門天妃宮有史可考者爲建於明弘治元年(1488);由此推想在此之前“鶴佬”早已於澳門西望洋山石窟供媽姐了。而澳門最早具有文獻記錄的村落“望廈村”據說即爲閩人聚居之處,簽訂“望廈條約”的所在地普濟禪院亦爲閩人籌建。澳門閩人對澳門文化的貢獻也不可低估,如在敎育興學方面,即有“漳泉義學”的創立,學舍就設在天妃宮左鄰,遺址尙存。路易的論文還提到--
“鶴佬”由於被他們自己創造的很難的語言孤立起來,所以,他們是人類文學極少描寫到的社會團體之一。有時也有一些零星的記載,但無人知曉哪篇文章是專門爲他們寫的。除了語言將“鶴佬”與廣東的漁民區別開來以外,其潛在的文化價值還可以通過其它外部的特徵來挖掘,讓我們來看一下漁船建造的一些細節吧。“鶴佬”所造的船一般總是船舷(船梆)一直向前延伸,並超出船頭,在船首的兩側還要刻劃出兩隻塗顏色的眼睛,廣東的漁民稱其爲“大眼雞”,直譯爲“母雞的大眼睛”,其中帶有某種嘲諷的成份,而廣東的漁民是沒有這種習俗的。但令人奇怪的是陳列在澳門內港的中國廟宇裡的這種漁船的微縮模型正具有上述特點,這似乎在向人們暗示: 歷史上,福建的漁民在這塊土地上出現是極其有意義的(22)。
其實,“鶴佬”並非被自身的語言所孤立,而是他們“入鄉隨俗”,逐漸使用粤方言,選擇了與當地蜑戶“同聲同氣”的生活方式。這種情形不必多加考證,即以目前已超過十萬之數從80年代始移居澳門的閩籍居民而言,他們多半都能使用廣州方言融入澳門社會,表現得有聲有色,可見他們並沒有被自身的方言所孤立。反之,路易結論說“歷史上,福建的漁民在這塊土地上出現是極其有意義的”,信哉斯言。
路易也認爲“直接觀察的法則似乎在語言學範圍內也行得通”,他在論文中提到--
直接觀察的法則似乎在語言學范围內也行得通,人們都能聽得懂“蛋家”講的廣東話,儘管他們帶有口音並使用從他們專門化了的生活方式中產生的詞匯。
Cornell大學的語言學家,John Mc-Coy先生專門研究過Kau Sai(香港新界)漁民的語言,他觀察到,儘管在整個詞匯中,與捕魚和漁船上生活有聯繫的術語很少,但它的使用會使不熟悉這樣的環境而講同一種語言的當地人感到驚奇,因爲其使用頻率是非常高的,這個事實,連同語音上的差異,使觀察者從語言學的角度過分誇大了本來是很小的變化(McCoy 1965:50)。於是,語言學者發現了目前水上漁民所講的語言,無論從語法还是語音的任何成份上都是不起源於中國語的,這樣的說法倒是可以給水上漁民部落起源假設提供憑證(McCoy 1965:60)。此外,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與一般的意見相反,另有一種說法,認爲水上居民並沒有自己的語言,或者說,中國南部的漁民講幾種不同的語言,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中國方言,例如來源於沿海岸的幾個地區的不同方言。(McCoy op. cit)。還有,不要忘記大部份分散生活的水上漁民一直都是文盲這一事實。
諸多理論中最能令人至信的是: 水上漁民來源於當地土著部落的說法。我們的介紹傾向於Wiens(1954)和Eberhard的研究爲基礎而創立的理論。根據這兩位學者的見解: 水上居民很可能是粵人子孫,他們與越南的“Viet”(越)很相似,2000年前當北方的漢人(廣東話稱Hón)來到廣東境內時,粵人已經是中國南方居民了。粵人包括多個部族,他們有的被漢人同化,或者迫於其壓力流逐於南部,他們其中的一支“Tán”很可能即爲“蛋家”的由來--可能他們曾抵制過漢民族的同化過程,努力保持其部族的原始風貌,成爲水上漁民的前身。所以,根據Eberhard的說法,粵文化沒有一個確定的特徵,它是多種文化交織融合的結果。這種現象在“粵”這一稱呼作爲政治概念出現在公元前七世紀時就已經存在了。這種文化交織融合的進程至少吸引了“瑤”(Yao)“蛋”(Tán)以及“傣”(Tái或Chuang)人的文化成份。但後來被漢民族的南進所中斷了,並被豐富的漢民族文化所融化了(Wiens 1954:41-43)。(23)
路易甚至認爲:
在澳門社會中,儘管地方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文化影響爲我們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但請不要忘記,澳門本身文化的多樣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葡萄牙當權者對地方風俗習慣採取了一種不干涉態度(laissez faire)。任何一個傳統的社會組織祇要不同政府搗亂,就會享受比較大的言論自由。這些地方社會組織之間的文化差異,儘管還沒有從社會結構和基本價值的角度將它們區別分開來,但它們有時充當了“種族壁龕”(nichos étnicos)的角度,這又爲修辭學提供了研究的課題,根據修辭學,一部份人要比另一部份人更加“中國化”或更加“文明化”,這兩個詞是作爲同義詞使用的。(24)
這種在“中國化”與“文明化”之間劃等號的提法是値得深入思考的。我們把所謂“中國化”理解爲“中華文化圈”的“涵化”現象。澳門歷史失語症從土著文化(無論是“蜑家”文化還是“鶴佬”文化)的逐漸“演化”過程,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圈在跨世紀文化整合方面所顯示的“文明化”作用。同樣,“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季羨林語)的提法對於澳門歷史趨向的槪括尤其適用。
在分析所謂“涵化”過程中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以及所謂“深層結構”的某種“復舊”作用時,如果從逆向方面而言,中西文化經過長期接觸終必呈現“生態平衡”現象,對於所謂“外來文化”一方而言,在此種涵化過程中,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復舊”作用往往作爲一種全新的文化因素被吸納,或者說,中國文化的“復舊”作用反而被那“外來文化”的一方收納爲新文化。(25)
季羨林敎授論斷“從下一個世紀開始,河東將取代河西,東方文化將逐漸主宰世界。”(26)我們也可以從這一論斷去思考澳門文化發展的前景。澳門目前已進入“轉型”時期,正確看待“河東”與“河西”的更替關係尤爲重要。而澳門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文化整合”亦應如季先生所說的,“正確的做法是繼承西方文化在幾百年內所取得一切光輝燦爛的業績,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濟西方文化分析思維之窮,把全人類文化提高到發展到一個更高更新的階段。”(27)
解決1999年澳門治權移交問題表面上似乎祇是中葡雙方政府之間的事情,實際上這是一個長期糾合錯綜複雜的歷史問題。如果中葡雙方考慮從文化融合的角度對待未來的澳門發展路向從而取得共識,澳門問題就有可能採取一種認同人類文化價値的對話方式,對雙方更有益和更有建設性,亦可望由此逾越歷史失語症造成的種種障礙。我們不妨先看葡國對待未來澳門的“文化政策”是怎麼回事兒。“一廂情願”並不合時宜,但“兩廂情願”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
葡萄牙官方“文化政策”的“宗旨”是在歐洲“友好國家”面前“體現葡國作用,體現它的語言、它的文化和它作爲歐洲一個現代國家的特點”。並且認爲“葡國在這地區的發展,包括我們的事業在澳門的永久存在,在很大程度有賴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播”,等等。如果祇是從里斯本制定的針對澳門的“文化政策”去判斷澳門文化的發展路向,“澳門文化”可能祇被看作葡萄牙文化在遠東的一種存在方式。其實,在遠離里斯本的澳門,同樣是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門行政當局針對澳門自身的“文化政策”就有頗爲不同的表達方式。1987年主管澳門文化事務的澳門文化學會主席曾作出相當“澳門化”的表述:
澳門不是一個文化單一的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尊重其文化自主權自然是要維護歷史遺產,使受到中葡兩國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復合文化得到發展。
由於幾乎不存在有關澳門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人文科學和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因此也不存在有關澳門人口的研究資料,包括澳門人口的現狀,不同文化之間的影響以及各自的變遷。
澳門具有絕無僅有的研究條件,卻直到如今不鼓勵專家學者從事不同文明史的比較以及相互之間關係的研究。
澳門的“土生社會”是葡中共有的最豐富的文化遺產,然而,對它的研究微乎其微。
所以,我們面臨三個重大的課題,對於它們的研究有助於理解澳門作爲東西方接觸和相互影響之地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從頭擯棄一種不正確的態度,即把澳門看作葡國文化區,或者是長在中國文明身上的一塊古怪的息肉。
這種看法有可能爲帶殖民性的和反殖民的激進的政治服務,而且忽視和貶低了澳門在四個多世紀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文化現象。
聯合聲明所提出的澳門過渡時期的政治制度與葡國人到達澳門直至費雷拉·阿馬拉爾(Ferreira do Amaral)政府之前的制度相仿: 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國當局手上,由他們頒佈涉及澳門利益的規章制度,包括葡國人的利益在內。這個階段在澳門歷史上佔了三份之一的時間,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文化角度來看,是最豐富的鼎盛時期。正是在這段歷史時期,耶穌會在澳門創立了遠東第一所大學,成爲在中國宣傳西方文化的中心和向西方宣傳中國文化的傳播站,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重新恢復最古老、豐富和持久的傳統,爲澳門文化復興創造客觀條件。(28)
事實是早在“西學東漸”之前的十七、八世紀通過澳門而興起的“東學西漸”之風使飽經三十年戰爭(1618-1648)浩劫的歐洲驚羨不已,並由此引起了持續一百多年的“中國熱”浪潮,Chinoiserie(漢風)影響至大,中國的理學思想對歐洲啟蒙運動所起的深刻影響直到現在仍應給以充份的評估。其實“葡萄牙文化在東方的影響”背後有一個“東方文化對葡萄牙(或整個西方)的影響”同時存在,文化接觸產生的影響向來是雙向或多向的。事實上,所謂“葡萄牙在東方的影響”即使在澳門也並非一廂情願的。有位葡萄牙學者認爲葡萄牙人幾百年來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的慘憺經營早已匪夷所思:
我們這些後輩目前在澳門的表現與以往相比是一個180度的轉變(恕我作此比喻)。我們的先人曾在此艱難創業,邁出了巨人般的步子。
我們的先輩爲澳門增添了一種語言,並從這裡出發傳播基督教教義。
又通過語言和教義擴大了人際的交流和人們的視野。
撇下基督敎義對東方的影響暫且不談,就說四百年前來澳門隱居的葡萄牙大詩人賈梅士(Camões)曾經在澳門用來寫出驚世之作的葡語,經過十六、七世紀之後的邅變,也逐漸與本地語言結合出現變異。賈梅士曾寫詩驚嘆澳門發生的各種變化。詩人的感受是這樣的:
且不說每日裡這些變化,
還有個變化更令人驚訝:
變化的方式也在變化……(30)
於是,“混在一起的時空與人在澳門產生出一種非歐洲非亞洲的與衆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着一種特有的不抵制接受其它民族風俗習慣的葡萄牙人的生存方式,一種共存的能力,一種力圖入鄉隨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和一種對世界各種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作爲海洋民族的葡萄牙人一旦在澳門道塊中國的土地上“定居”下來之後,竟然失去了冒險精神。於是--
距離香港50公里,廣州100公里,一小時到馬尼拉,澳門卻顯得很不相同,長達四百年,兩種強大而又不同的文化--拉丁和華夏文化交往,有時甚至衝突,澳門卻因此獨一無二而標新立異於世,由葡國人所建,但由中國人居住並以其創造性調整,澳門是,而必然是一塊有強烈對比的土地,兩種文化之遭遇在歷史每一個階段留下印記並超越一切常規。(32)
澳門的確是在中國文化所有的“創造性調整”力量支配下使觸及它的生活模式的一切東西都發生變異,這就使在澳門長久居住下來的葡萄牙人的“民族性”甚至語言表達方式都發生了變異。這樣就出現了澳門的土生葡萄牙人問題。
如果我們把澳門土生葡人和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人看成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似乎比把兩者混爲一談更有說服力。澳門土生葡人樂於使用FILHOS DA TERRA(大地之子)或OSMACAENSES(澳門人)的稱謂,他們在澳門的確也是“自成一族”。早在1897年,平托·達法蘭西在他的一篇文章《澳門及其居民》之中提到:
澳門土生葡人最能夠引起歐洲學者興趣的無疑是他們的語言。那是一種由16世紀的葡文和中、英文短語混合而成的方言。舆我們接觸较多者,所講的葡文尚可接受,儘管發音中帶有新拉丁文在熱帶特有的緩慢輕柔的變調。然而他們之間,特別是女性之間使用的語言,因其怪異奇特和約定俗成,使我們歐洲人無論如何難以明白。(33)
馬爾克斯·佩雷斯寫於1920年的論文也指出了其餘的澳門土生葡人的語言與眞正的葡文相差很遠,指出此種“方言”具有三種形式:1)低下層使用的語言;2)一種與純正葡語更爲接近的語言;3)中國人講的土語。
Polomé用三個條件判斷土語化過程是一種語言內部轉變的決定因素:1)語言發展過程中有明顯的中斷間隔的證明;2)存在着典型的土語化特徵(由簡化到再造過程);3)證明存在着適當的社會經濟或政治文化條件,在外來者(非母語使用者)掌握官方語言的過程中,促成文化融合。我們考察澳門土生葡人語言變異現象時,上述三個決定因素是很重要的。
依貝荷·湯馬斯正是如此看待澳門土生葡語的生存與消亡的:
上一個世紀保存下來的用澳門土語寫成的文章,因其本身呈現的許多不同,也明顯地體現了當時正在進行的非土語化進程。更有意思的是,從一些文章中還可以看到,土語使用者當時已意識到了其語言結構之低層次和向規範語言改進的壓力。
毋庸置疑,地方語言的包圍和因社會、經濟繁榮而出現的文化融合幾乎將這些土語完全同化。另一方面,將土語視爲這些社團的文化宗教本體的良好傳播工具而抗拒其被吞沒,隨之變成了一種爲爭取土語生存而進行的長期抗戰。(34)
我們從目前仍在澳門工作對澳門文化硏究具有公認權威性的傳敎士潘日明神父的著作中也可以瞭解到澳門土生葡語的歷史面目:
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幾乎所有葡國人家中的傭人和他們的妻子都講一種澳門方言。有關此方言所遺留下來的記載很少,散失在各地,並從未收集成一本論文集。馬爾克斯·佩雷拉、弗朗西斯科·雷戈和格拉謝特·巴塔娅合編的《大西洋國》雜誌中收集了此“混血文學”的一些有趣的片斷。格拉謝特·巴達婭是位語言學家,她研究了七百個澳門古方言詞彙的詞根並出版成書。隨着葡文學校的發展,雖然在書寫及會話方面還會存在一些只有經過高等教育才能改正的語言、語法和句法的錯誤,但我們可以說當地的方言將會逐漸消失。
在馬六甲,我們可以列举出三千個源自葡語並沿用至今的簡單詞匯,實際上用這些詞彙可以表達一切意思。我們日夜夢想着在遠東和東南亞重建葡語在其黃金時代的“通用語”的地位。
在澳門,葡國的存在持績了较長的時間。澳門的方言中還包括了印度、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日本的一些詞匯。當時的方言應該比我們今天所見的遺蹟豐富得多。難道若澤·多斯·桑托斯不是用先輩甜美的“方言”盡情地以散文或詩歌的形式表達他想表達的一切嗎? (35)
葡語在澳門歷史上的變異,毋疑是受到異質語言的影響,我們不能不考慮漢語方言對它的滲透作用。第一批到達澳門的葡萄牙冒險家就本能地激起了學習漢語方言的慾望。據說MACAU 亦由澳門粵人的一句粗話被誤會音譯而來。(36)即使到了今天,由於澳門回歸中國的日期逼近,澳門不少土生葡人並不滿足於自己能操流利的廣州方言而努力去學習普通話,其熱情並不低於本地大多數祇懂講廣州方言也想學講“國語”的華人。早在1555年,葡國探險“王子”文第士·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隨貝爾斯·努內斯(Beechior Nunes)到達澳門。平托於該年11月2日那一天寫的一封信可以被視爲它是出現MACAU的第一份葡文歷史文獻,它也是反映葡國人對漢語發生極大興趣的最早文獻。該信內容如下:
願基督的慈愛和恩寵與你和所有的親愛的弟兄們同在,阿門。
由於時間關系,我不能如願詳述我們的旅行見聞以及與殿下分手後所做的一些工作。今天,我從居住的浪白島來到相距不遠的澳門,遇見了貝爾簫神父,他從廣州回來,輾轉廿五天,花了一千兩銀子贖回了貴族馬戴烏斯·德·貝力杜及另一名被囚禁的人,並遊覽了城市,觀賞風土人情,也試探了将果以斯的兄弟魯依斯留在廣州學習語言的可能性……(37)
隨後,澳門傳敎士主動承擔起兩種異質語言進行交流的歷史任務。我們如果把澳門土生葡人言語的“變異”現象看作是部份“漢化”的過程也不無根據,但這跟傳敎士一直想通過澳門向中國內地宣傳基督敎敎義是存在着“雙向交往”的“語言需要”有直接關係的。澳門在19世紀之前一直是天主敎和歐洲影響進入中國的唯一大門。
1711年,葡國耶穌會會員用中文書寫並出版了42部著作,其中包括伊納西奧·達·科斯塔翻譯的孔子的文章。
在耶穌會撤走之前,會員把許多西方書籍譯成了古漢語,其中有佩德羅·達·馮塞卡的哲學叢書《哥印伯人》和曼努爾·阿爾瓦雷斯神父著的拉丁語語法。阿爾瓦羅·塞門多神父出版了中葡及葡中兩本字典。19世紀末,聖若澤修道院院長卡爾瓦尤曾把字典寄給里斯本的地理協會,今天我們在那裡還可見到這部作品。但與其它作品一樣,原木刻版本已經完全失傳了。這是不是因爲這些書的主人--耶穌會會員們相繼去世和他們的圖書館日趨荒廢之故? (38)
這說明了“葡一中”與“中一葡”兩種語言在澳門產生雙向的干擾滲透。潘日明在他的著作裡指出一些葡語詞匯滲透進漢語的例子,例如:
在上海地區有三十個詞,在廣東自然有更多,因爲一直到今天仍與那裡的人民還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詞例: “麵包、方包”(Pão)、“蕃茄”(Tomate)、“所有、一切”(Tudo)、“朋友”(Amigo)、“再見”(Adeus),葡語中同樣也引入了漢語的詞與句子: “斤”(cate)、“穀”(Nele)、“滴”(Pinga)和“茶”(Chá)。同時還有一些中國特有的食品的名稱和諸如“是不是”、“今天放假”等句子(葡語中的“Ter”和“Haver”譯成漢語都是“有”的意思;“é”和“Sim”都是“是”;“Como se chama”和“Como se diz”都是“你叫甚麼”),等等。(39)
潘日明神父的《殊途同歸》爲讀者提供了大量的通過澳門歷史演繹與文化交結反映出來的有關古老而新鮮的葡中關係的主題、情狀和知識,這正如作者在該書前言所說的,這都著作阐明了四個世紀各種文化共存和不可置疑的文化相互滲透。誰能主觀妄斷地回答他提出的問題:
文化上的混合、同化、異化還是排斥? 任何類型的人類學對自己都尚無定論,更談不上能給他們之間劃出界限了。由此可見,文化互相滲透,這種在人們的軀體或者發現中文化並存的現象會持久下去,因爲人們會以開放的精神境界和睦相處。應該說這種文化並存的形式要比其它的形式好得多。從無限的時空觀來看,葡中這方面的歷史給這種文化並存的形式提供了活生生的總結。現在我們在澳門有兩種古老而豐富的文化--葡萄牙文化和中圃文化--相互交織在一起。(40)
葡萄牙人約在中國宋朝的時候才建國,但很快地靠新航道的發現到達遠東,元末明初就登上了中國海岸的土地;而著名的三寶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固然一時使“國威遠播”,卻沒有想到去佔領分割別人的一寸土地,以便種下中國政權的碑石。這也許就是蔚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異質的明顯差別。然而,中國人表面上的逆來順受卻隱藏着精神擴張的強韌力量。在澳門定居下來的葡萄牙人終於在四百年漢風華語的熏陶之下一步步接受了東方文明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們從澳門土生葡人之中文化層次較高的人物去看漢風華語的“涵化”作用,就可能傾向於“澳門土生葡人具有認同中華文化之傾向”的結論,而不會去斤斤計較1999年之後澳門“權力分配”的得失問題。進一步說我們如果能充份認識“澳門文化”即將成爲中華文化一個獨特的子系統,未來的澳門能夠建設成爲一個“文化特區”的意義就要比搞成一個遠遠差勁的“經濟特區”要寶貴得多。
這裡順便舉一個澳門土生澳人學者作爲說明他們已經深度滲透進漢文化圈的例子。著名的高美士不僅是澳門“文化人類學”的先驅,同時是一位素有學養的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由於“在澳門出生和生活,高美士對澳門的實際瞭如指掌,由於他精通中文,因此能夠進入一些‘葡國佬’所難以滲透的領域,深入瞭解社會之內幕”。(41)
澳門所有的“漢風”或稱“中華文化”對即使並非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葡萄牙人來說,只要他在這個“夢幻島”定居下來,也很快就會受到“深度”的潛移默化。1970年才從葡萄牙移居澳門的施利華說,澳門華洋雜處、東西合璧的“萬花筒般的生活,令他如墜煙霧”,在這之前,他已經“受了二十四年的葡式薰陶”。他終於在澳門這個奇異的狹島工作和生活了十六年之後寫道:
我開始愛上澳門,希望更多地瞭解它的人民和歷史,這是東西方一張複雜的網。澳門是一本絕無僅有的世界外交術“大全”,作者是普通人,用行動而不是文字寫成,澳門無愧爲葡語世界自然價值補充的傑作。
熱內拉(Armando Martins Janeira)強調,如果東西方之間多文化往來,而不是政治權術,東方的平心靜氣可以給動蕩不要的西方帶來平衡,也有助於世界和平。
在這一點上,我談自己,我認爲每個人的切身經驗是接近真理最可靠的途徑。
多年以來,我逐漸在“葡圃的我”和““澳門的我”之間建立對話,幾經反省,神益非淺: 有所摒棄,有所保留,有所充實,產生新的自我。而今,我愈加重視我們的所作所爲,歷史將把我們作爲一個整體來評價,而社會風波和個人生活祇是過眼煙雲而已。我學會忍耐,嘴角掛著微笑,控制急跺,保持心平氣和,儘管有時會忘記學會的東西而拉丁本性大發。
我逐漸認識到有些民族的習性與我們完全不同。他們的一些行爲和反應甚至使你吃驚和不解。中國人永遠變幻無窮,生活在他們身邊今人銷魂。(42)
行文至此,我們應該回到理論的抽象認識上來,去肯定文化行爲傾向於整合的論證。我們是這樣去分析澳門的: 我們一開始就把澳門的歷史失語症與跨世紀的文化整合看作是互爲消長的同一問題的兩個側面。美國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認爲,“相互之間沒有內在關係的、歷史上獨立的諸特質之間的融合(merge)與交結(inextsieable),爲那種在不構成這樣一些識別標記的範圍中未出現類似情况的行爲提供了表現機會,其必然結果是: 無論是行爲的哪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從肯定到否定的一系列標準。”(43)他還進一步提到“良性文化整合”的作用,這一觀點是値得硏究澳門文化與人種(或民族)融合現象的學者注意的。他說: “每一種文化中都會形成一種並不必然爲其它社會形態所共同具有的獨特的意圖。在順從這些意圖而行動的時候,每一個民族都越來越加深了其經驗。與這些推動的緊迫性相應,各類相異的行爲也取一種越來越和諧一致的外形。由於良性文化整合的作用,最不良分類的行爲,也經常由於最靠不住的變形而成爲其特殊目的的特徵。這些行爲所取的形式,我們祇有靠首先理解那個社會的情感上的和理智上的主要動機才能得以理解。”(44)
正好我們看到了一份由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現爲里斯本社會科學學院硏究員的賈淵敎授和里斯本新大學社會學博士陸凌梭敎授合作的以大量訪問資料爲基礎的報告譯稿(45),它對本世紀中、後期澳門土生葡人的處境有很客觀的描述,是迄今硏究澳門土生葡人現狀最具說服力的論著,恰好補充了《大地之子》一書的欠缺部份。
自從四十年代起,澳門人口爆炸性增長,引起生存空間的變化,使不少長期受葡中文化熏陶的土生葡人舉家離開澳門,這種變化加劇了“土生社會”的瓦解和“混合文化”的式微。値得注意的是澳門土生的“新族群”動態,戰後出生的一代跟中國“文革”後出生的一代在文化的價値觀和自覺意識方面有很大的差異。“區別兩代的標準在於同一族群內退讓一代(GERAÇÃO CESSAENTE)和操權一代(GERAÇÃO CONTROLANTE)之間的政治權利。”兩代之間的主要分別來自各自環境的差異。目前正在退讓的那一代成長的時候,澳門正處於社會經濟癱瘓時期。而在80年代澳門經濟大躍進期間,通過對政府中層的控制,操權一代保存了他們的族群壟斷地位,“手段祇是利用他們溝通族群的能力,即他們能說廣東話並且能寫和閱讀葡語的特長”。
至於在90年代初才冒頭的操權一代,問題截然不同。1987年4月13日的聯合聲明爲澳門葡人政府定下了限期。雖然葡國語言和法律在未來數十年依然會保留官方地位,但這個問題對土生葡人來說關係重大,他們不可能相信一個善變政府的含糊承諾。他們估計在1999年将會喪失在過去30年來替他們抵禦着新冒華人階級的族群壟斷地位。到時,他們將要和華人公開競爭,不同之處就是他們的一度優勢,即是說與統治者在文化上的聯繫,將會落到華人中等階級手上。
因此,對於正在冒頭那一代,形勢大有改變。目前精英份子(不論是華人還是土生)的對策就是讓子女在英語系國家接受高等教育,如果可以的話,举家在該處落地生根。從子女在外國唸書的父母口中我們得知,在當地(主要是英國、加拿大、美國)認同中國文化比認同葡國文化有利,華人圈子比葡人圈子提供更有效的社會經濟整合(INTEGRAÇÃO.)
對於沒有機會出外求學的年輕人來說,接受葡語教育有一弊病,那就是要成爲中文文盲。這些在廣東話香港電視支配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的年青人覺得葡語已沒有吸引力,故而抗拒父母和教師(退讓一代和操權一代均有)試圖把葡語文化傳給他們的努力。受訪葡語教師一致認爲土生學生沒法學好葡文,因爲他們的日用語是廣東話。最近,許多土生和華人結合的父母把子女送去中英文學校讀書。
80年代在澳門受教育的土生葡人領會到與華人有聯結才是他們將來的保證。於是,他們把敵意從華人身上轉移到葡人身上。1988年葡文中學學生的騷亂正是這種轉變的見證。一個當時在場的證人告訴我們,那些土生學生的主要聲明是: “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葡國人。我們是另外一族。”(下略)(46)
我們想,引文至此,凡是具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會嚴肅思考未來澳門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乃至“語言政策”應該選擇何種模式才能保存澳門的獨特性或者取消它的獨特性。當澳門土生葡人一族出現向華人文化認同的趨勢的時候,正是達到跨世紀文化整合的突破性高潮點的時刻,歷史性地將成爲澳門這個不妨類比於的基爾特式的袖珍資本主義社會統治者的華人權力集團一方,到底宜採取民主開放的政策,還是閉關自守的政策,此項決策恐怕不僅與澳門土生葡人的命運休戚相關,從宏觀的方面看,也跟整個中華文化的興衰休戚相關。
格式塔完形理論認爲,整體決定着它的部份,不僅決定着這些部份之間的關係,而且也規定着它們各自眞正的本質。所謂“澳門文化”也超出它各個部份的總和,而在其複雜性的每一個層面上,甚至在最簡單的層次上,都趨向於整合。因此,我們判斷: 澳門的歷史失語症與跨世紀文化整合不單是一種客觀存在,它同時也是一個理論問題。
【註】
(1)詳見黃曉峰: 《澳門的文化視野: 世界與中國》(參加1991年4月北京大學東方文化國際硏討會論文)
(2)引自薩丕爾: 《語言論·言語硏究導論》
(3)布龍菲爾德: 《語言》
(4)申小龍: 《中國古代思維之語言表象》(見《中國文化論》一書,百家出版社,1991)
(5)同註(3)
(6)指Brocás aphasia(布洛卡失語症)
(7)指Wernichés aphasia(維爾尼克失語症)
(8)指Word deafness(詞聾症)
(9)程祥徽,劉羨冰: 《澳門的方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兼評CHINGLISH》(《澳門語言論集》,1992.)
(10)高瑪莉(Maria de Conceição Gomes):《小議主權移交下語言在澳門法律領域之作用》(《澳門語言論集》)
(11)利高素(Maria Trigoso):《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葡國人不參與選擇》(《澳門語言論集》)
(12)《在澳門的交流》(《澳門語言論集》)
(13)(14)同註(12)。
(15)同註(11)。
(16)《廣東新語》記澄海有輋戶。沈作乾認爲在明代征西南部傜人後,部份東至贛粵之間(參考林天蔚、蕭國健: 《香港前代史論集》)。
(17)《東華錄》記雍正七年五月壬申上諭。
(18)《嶺外代答》卷三,外國下。
(19)《東莞縣志》卷二十九。
(20)Luis Keil: Álvares O Primeiro Português Que Foi Á China,1513》(《歐維士--第一個到中國的葡萄牙人,1513》(澳門文化學會出版,1990)
(21)(22)(23)(24)《文化雜誌》第5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87。
(25)這一段文字轉自劉月蓮《蔚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的融合體--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與現狀》一文,北京《發現》雜誌第5期,1992。
(26)季羨林: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27)引自1987年5月9日葡萄牙共和國總統蘇亞雷斯在里斯本貝寧宮舉行的澳門總督文禮治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28)彭慕治: 《聯合聲明與澳門文化復興》(見澳門《文化雜誌》第2期,1987)。
(30)賈梅士: 《葡國魂》
(32)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略談澳門》(見澳門《文化雜誌》第3期)。
(33)澳門《文化雜誌》創刊號: 《九十年代文化綱領》
(34)Isabel Tomás: 《一種土語的生存與死亡》
(35)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中葡兩國的相互影響》(澳門《文化雜誌》第6期),收入他的著作《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
(36)MACAU一說爲“媽閣”的閩南話音譯;另一說爲由廣東方言一句粗話音譯而來。
(37)引自澳門《文化雜誌》第5期中J. M. BRAGA的文章: 《第一次中葡和約》
(38)同註(35)
(39)同註(35)
(40)這一段文字原爲澳門文化雜誌對《殊途同歸》的書評,由總編官龍耀(Luís Sá Cunha)執筆(見《文化雜誌》第9期)。
(41)見《文化雜誌》第一期馬若龍撰文: 《高美士與摺紙》
(42)Beatriz Basto da Silva。此段資料轉引自他的文章《省略號》(見《文化雜誌》第1期)。
(43)(44)〔美〕南尼迪克特: 《文化的整合》
(45)賈淵、陸凌梭: 《根源問題: 澳門的族群關係以及女性地位》,轉引自一份譯稿(未刊)。
(46)同註(26)
*劉月蓮,澳門文化研究會秘書長,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訪問學者。黃曉峰,澳門文化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