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土生葡人最能够引起歐洲學者興趣的無疑是他們的語言。
那是一種由16世紀的葡文和中、英文短語混合而成的方言。與我們接獨較多者,所講的葡文尚可接受,儘管發音中帶有新拉丁文在熱帶特有的緩慢輕柔的變調。然而我們之間,特别是女性之間使用的語言,因其怪異奇特和約定俗成,使我們歐洲人無論如何難以明白。
本托·達法蘭西《澳門及其居民》,1897
本托·達法蘭西在上個世紀對澳門土生葡人語言所做的上述描寫,雖然不無輕視和賣弄的成份,却並不罕見。它反映了歐洲人遊歷東方,聽到自己扭曲變調的母語後而表現出的過份關注。
從中世紀起,就可看到用土語記載的遊記、書信、傳敎報告、官方函件和翻譯成土語的宗敎文章和散文。一方面,它與歐洲語言在詞滙構成上有相似之處,因係從其中派生而來;另一方面在結構和發音上又具有歐洲語言的不同之處,因而從一開始就被當做是社會文化地位低下的底層種族,社團對現範語言的纂改和謬傳,混雜怪異的行話,幼稚和原始的語言。
從聖仙方會對16世紀黑人土語的評價--“即使强行用力也無法敲開黑人與白人社會同化的魔幻大門,黑人本身的語言就不可挽救地將其置於不等人的地位”,到本世紀初《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對土語的定義--“落後、無規則的、充滿幼稚和謬誤的俚語”,直至不久以前,學術界關於土語的槪念--“統治階級爲便於與低下層交流而刻意簡化的規範語言”,都體現了西方對此類語言的認識中摻雜着傳統的偏見。
然而,近幾十年來土語研究方面的進展使這種觀念,即使不在整個世俗間至少在學術界有所改變。土語研究成了探討語言進化和人類交流的複雜過程的一項基本環節。
甚麼是土語
土語是一種形成時間相對較短(和歐洲語言及其文大部份非西方語言比較),因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政治和語言環境中交流和約定俗成而產生的母語。但是,其相對年輕的歷史並不妨碍(這點應該强調)它像其它証言一樣展現出其複雜、細微的表達能力,這在語言上是不論歷史長短的。
因是母語,任何一種土語都必須具有讓其使用者交流、表達和抽象思維的功能,使之能用於談判、祈禱、討論、談情說愛、敎唆、說笑、描述、管理、欺侮、傳授知識、翻譯、勸說、辯論和請求等。如果一種語言不能滿足其使用者因從事一系列人類活動而對語言的一般要求,無疑將排斥、遺忘和淘汰。“死亡語言”、的例子即已證實這點。對導致其喪失語言能力的因素我們在本文其它部份將再作分析。
也許有人認爲,某些土語和西方規範語言相比,在詞義上較爲貧乏;或許還會說,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土語書寫而成的文學、哲學、法律和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一般均處於被歧視地位的講土語社團,觀察其社會、文化和政治特徵,(社會發現)土語總是被强置在低級落後的地位,或是因爲講其它語言的統治階級本身,或是因爲要維護宗主國語言--這一統治階級的交流工具的模式與聲望。
當土語因歷史和政治的原因而獲得聲望,呈現出有史以來的最完善的程度,發展成爲文學語言(如在佛得角),擁有新聞出版物(如在幾內亞(比紹)、塞拉利昂,甚至達到(如將其作爲官方語言)官方合法地位,同時有機會發展敎育和科學水平,就一定會像其它語言一樣,創造出能擔負起語言功能的適當方式(翻閱葡文古典書籍即可找到這方面的例證)。
儘管土語一詞傳統上都是用來形容形成時間較短的語言,研究一下由拉丁文到各種拉丁語言的進化過程,可以較淸楚地理解要求賦予土語以成熟地位的觀點。
波洛梅(Polome)以下面三個條件,來判斷土語化過程是一種語言內部轉變的決定因素。
1、語言發展過程中有明顯的中斷間隔的證明。
2、存在着典型的土語化特徵。(由簡化到再造的過程)。
3、證明存在着適當的社會經濟或政治文化條件,在外來者(非母語使用者)掌握官方語言的過程中,促成文化融合。
異族侵略在拉丁文的正常進化過程中造成了中斷,在這過程中亦可看到一個結構簡化,隨之是結構再造的階段,異族語言均參與了這一簡化和再造的過程,於是就出現了一個雙語階段,其中高層使用的古典拉丁文,即有聲望的語言和異族帶入並很快在民間流傳的土語化拉丁文的並存。
拉丁文的正常進化本應是循序漸進地自然進行,當口語或民間拉丁文開始區别於古典拉丁文時,這種進化就趨於明顯。但是,第5世紀的社會、政治動蕩和羅馬統治集團面臨的搖搖欲墜的局面,及最終而至的帝國滅亡,突然中斷了語言進化的延續性。即使是後來由基督敎以拉丁文來完成的羅馬語言書寫形式也沒能抵擋住後於分裂狀態的帝國內部的來勢凶猛的語言再造。拉丁文內部各種方言成份的增强,各種前拉丁語言的長期影響和帝國各地不同的社會文化特徵帶來了各種方言的初期發展。
因此,從“土語”一詞的廣義而論,我們可以斷定,拉丁語系的各種語言,除去作爲規範語言的地位和複雜結構不論,在其初期也是一種土語。
現階段被稱爲土語的語言在其進化過程中,波洛梅提出的三個條件正在履行之中。
從15世紀起,歐洲人大量地强迫遷徙奴隸,使奴隸語言出現了中斷。這不僅是因爲被販賣的奴隸包括講各種不同語言的非洲人和東方人他們之間無法相互溝通,而且基於“共識”而採取的政策是,將講同一語言的奴隸分散,以減少和消除暴動的危險。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况,一個被强迫招募的勞動力,被迫去適應無論社會還是生活上都完全不同的,由主人擬定的生活方式,因而突然陷入了一種被除根失去個人原有的一切的境地,陷入了一種多語環境,而且必須用統治者的語言來交流。
這就是種植園土語--種植園環境中的語言產物--的典型情况。在那裏,講各種不同語言的大多數人被分隔居住,由一小部份人統治,而祇有小部份人是講一種共同的語言,即宗主國的語言。因爲奴隸制而產生的土語幾乎代表了大西洋沿岸所有土語的情况,如蘇里南、庫拉索、海地、牙買加、伯利兹、聖多美和普林西比、阿諾博、佛得角等。
我們對種植園的理解是:
1、位於熱帶或亞熱帶的土地耕作團體,
2、從事商業種植活動,
3、產品銷往歐洲市塲以賺取利潤,
4、勞動力由歐洲以外的奴隸組成,
5、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歸歐洲人所有。
如果觀察一下葡國人在海外擴張初期在大西洋地區建立的種植園,即可發現上述特點。馬德拉島,與發現時期的其它島嶼一樣無人居住,從加納利羣島招來的奴隸們,作爲“蔗糖”師傅,促成了那裏的甘蔗種植業。
然而,到了佛得角殖民時期,加納利羣島的土著人已被大量屠戳,葡萄牙人隨即由非洲大陸帶來了大批奴隸。之後,在聖普,種植園的生存也是依靠非洲奴隸。
儘管完全被排斥在奴隸主和工頭階級的生活之外,奴隸們又必須被迫去適應葡國人的生活方式,與葡國的文化特徵保持一致。在這種相互矛盾的重壓下,早在十五世紀末,就出現了一種土語化的文化本體和語言,而它們中間,從一開始就摻有非洲語言和文化的成份。
在非洲大陸,祇是到了十六世紀末,才出現了第一批土語。這些土語(幾比─賽內加爾)隨着由佛得角羣島向幾內亞灣一帶的移民而產生,因而模仿了佛得角土語的模式。
葡萄牙對非洲大陸的統治,從一開始就帶有商業和宗敎的目的,在那裏設置了商業中心,攫取掠奪財富;並和當地的首領談判條件,有時還按王國的等級將這些首領提升,賦予象徵性的地位,給予非洲沿岸土著民族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允許他們保持傳統的語言和習俗,條件是承認葡國對其擁有主權,對强加給他們的宗敎和經濟要求表示順從。這也是在安哥拉未曾產生混雜土語的緣由。
但是,在東方,葡國人和當地人民的接觸方式却完全不同,在通往尋找香料、檀香木、絲綢和瓷器的路上,我們(葡國人)接觸到了具有複雜的政治、社會體系、古老文化和儘管形式多樣並各具特色,但仍可與歐洲文化相比美的文明。
一直以來,葡國在東方的殖民政策就是“一項建立多種族,通過異族通婚而實行的人口固定”的有别政策。
在阿布盖克(Albuquerque)的領導下,一項旣有形體又有精神準備,旣有血緣聯繫又有文化融合的政策得以實施。
如果說在各民族交往中消除種族偏見,便於並促成了同化,東方缺少歐洲婦女的實際情况使通婚變成了一項明智的擧動。
海上長途旅行艱難多險,“船在巨浪中翻卷,甲板上擠滿了言語粗俗的士兵,飲食質劣量少,居住擁擠不堪,毫無任何安全保障,隨時都有被吞沒的危險。”〔埃列納·聖賽(Elaine Sancean)〕
“每條船上運載500、600、甚至700人,還有武器、生活用品和奴隸,暴亂時有發生。從啓程至抵達,很多人死於途中,之後慘被老鼠分食”。〔列莎(Lessa,ibidem,第7頁)〕
由於以上原因,爲數極少的婦女敢於加入這種險象叢生的旅行。
除此實際情况外,還有一層更深的政治原因促使阿布盖克及其繼任者支持通婚。
十六世紀的葡國人口,與其擴張計劃規模極不相稱。堂·若昂三世(D. Joao)下令在1527年進行的人口普查,人口總數僅爲110至140萬。
印度美夢使人陸人民付出了血的代價。然而,不論參加這一行動的人數有幾多,都不能滿足佔領海上貿易通道,維護和守衞東方市塲在人力方面的需求。爲了印度美夢能夠實現,人力短缺的狀况必須以某種方法來克服。於是就出現了傳敎通婚,十分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而這部份人口的忠誠也因宗敎和血緣上的一脈相通得以保證。
對此項政策之緊迫性和重要性的認識,使葡萄牙王朝通過其代表--各任總督和攝政憲章,鼓勵並保護葡國人與當地婦女結婚。由此產生了語言和文化融合的鮮明特色,相互間努力適應對方的模式,東方的土生葡人正是這一方面的例證。
當我們講到土語,特别是東方以葡文爲基礎的土語,總要用“死亡”或“濒於死亡”這些詞語來描述,就像在談及植、動物等生物。植、動物作爲有機物體,都要完成注定的不可避免的生命周期,即出生、童年、成熟和逐步衰老這一系列過程,最終不可避免地必定要死亡。
十九世紀語言學者常用的生物借喻法,使德國語言學家弗朗斯·布博(Fvanz Boob)做出了如下論述:
應將語言視做按旣定規律運作的有機的自然物體,根據自然界內部的生命定律而發展,並逐漸消亡。
一個半世紀以後,這種將一種語言的死亡簡單地看做是自然旣定的生命規律的看法,是不能被接受的。
一方面,一種語言幾個世紀以來,有時因某種歷史原因而經歷的逐年演變中,也伴隨着名稱的變化。那些因無人將其做爲母語而被稱爲“死亡”的語言,其實仍具生命力,儘管在形式上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就是拉丁文的情况。經過幾個世紀的變遷,雖然在名稱和形式上發生了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拉丁文還在其直系後裔--各種拉丁語系語言中有形地存在着。
另一方面,我們不應否認,某些確已“死亡”或消失的語言,並沒有經歷一個緩慢逐步的語言變化過程,而是在僅僅兩三代的時間內就迅速徹底的消亡。
一種語言爲甚麼會死亡? 這正是我們今天與上世紀語言學者的著名生物借喻派的觀點的分歧之處。
一種語言的死亡,並不是因爲到達了其生命同期的最後階段,即有機體客觀定律內必隨的語言老化期,而是因爲其它語言將其逐漸排斥,緣於社會和政治的原因。
“已經死亡”或“瀕於死亡”的土語即是解釋社會和政治因素導致語言死亡的明證。
土語的死亡
一種“規範語言”的生命周期要持續上幾多個世紀,其變化過程在各代使用者間幾乎體會不到。從最初用“原始拉丁文”記載的葡國文件到阿米格詩文式的葡文,從吉爾·文森特(Gil Vicente)到若昂·德巴語(Joao de Barrs)和賈梅士,從埃古拉埃(Hevculano)和埃薩(Eca)到貝索阿(Pessoa),從若澤·德賽納(Jorge Sena),和阿古蒂娜(Agastina)時期到我們今日公衆和私下塲合所用的葡文,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經歷着持續細微的變化,而一般使用者却很少能體會到,除非是在一些特定的時間和塲合內,如16世紀的語法攻勢和葡國電視報章上的語法諮詢”過程。
研究一種“規範語言”,例如葡語,描繪其世世代代經歷的語音、詞法、句法的緩慢變化,是一項長期細緻的工作,是一部包含了幾個世紀的巨幅影片。
相反,語言生命周期却節奏快速,其中社會和政治因素佔主要住置。
相對比較年輕的語言,其初期發展階段,即由在講不同語言社團中起輔助交流作用的混雜行話到一種社團內部的母語,僅兩代左右的時間裏,土語就快迅發展到了其最後階段。
今天已經死亡的以葡文爲基礎的東方土語,在上個世紀還具有生命力。而那那些殘存的,如斯里蘭卡和印尼土生葡人的語言,印度達曼人和開利開爾人(Korlai)的語言,却出現了將會即刻消亡的跡象。
一種土語變成某社團的母語後,將會出現何種情况呢?
很明顯有以下幾種可能:1、可無定期無本質變化地生存下去,如海地土生法國人的語言;2、可以消亡,如Nergevhollands和GUllah;3、甚至也可以演變成一種規範語言,儘管很難找出這方面的例證的記載,更難確定甚麼是非土語或超土語的語言;4、還可以和與之相關的規範語言混合,如牙買加出現的那種情况。
第一種情况的例證,海地土生法國人的語言,表明了社會和政治因素促使雙語制的形成兩種互不相通的語言在一個社會中並存,一種被稱爲高級語言--法語,另一種被稱爲低級語言--土語,每一種語言都具有其各自的特定作用。
在某種塲合適用A語(高級語言),而在另一些塲合則適用B語(低級語言),兩者間等級上的區别很少。
B在家庭、朋友及非正式塲合中使用,A則在學校、書面和正式塲合中使用。一個受過敎育的海地人,根據不同塲合(正式或非正式,同親人或同上司,在街上或工作中)而使用的不同語言,與使用母語和外語這兩種不同的語言是一樣的。
這種情况同樣發生在各土生葡人社團中,那裏土語總是和葡語或其它任何一種官方的、社會威望更高的語言並存。
第三種情况也應該是由社會和政治因素決定的。土語要進化到一種“規範語言”,必須獲得官方語言和威望語言的地位(我們所說的“規範語言”,即不帶有一般加給土語的那些低級標誌的語言)。
佛得角的土語似乎正在朝着此方向發展,儘管葡文仍在那裏作爲官方語言。佛得角土語向規範語言結構的方向發展明顯地體現在土語文學作品和將其做爲母語的使用者的態度上的轉變,他們不在有自卑感--這一殖民意識等級社會留下的烙印,而是將其視爲植根於社會,具有佛得角特色的民族文化本體。
但是,我們本文專注研究的則是另外兩種情况,即土語與規範語言的混同和土語的消亡。
吉思·艾奇桑(Tean Aichinson)用自殺和他殺這兩個詞來比喻語言消亡的兩種情况。
第一種是古老語言使用者繼續使用它,但逐漸引用官方語言的一些用語和句式,直至古老語言無法再與官方語言分開。這實際上是一種特别形式的語言借用。於是就像自殺,古老語言隨着引用越來越多的官方語言而慢慢地自我毁滅,甚至其本體完全消失。
第二種情况更爲劇烈,因某些情况,古老語言完全消失,不是自然消亡,而是他殺式的,即被官方語言以廢除或排斥的方式消滅。
一個自行消亡的例證
澳門土生葡人的語言是土語自行消亡的一個例證。
與宗主國的語言,即土語之前身,佔統治語言地位(同時是官方語言和有威望的語言)的語言長期共處同一地理環境,是決定性的條件之一。
另一個必要的條件是兩種語言互不相同,但又有某些相似之處。
第三方面,澳門土生社團和宗主國社團之間並無嚴格的等級差别,這點與大西洋沿岸的土生情况正好相反,那裏的土生被視爲下等人(一般均爲奴隸的後代)。儘管長期以來地區行政長官的職位幾乎都由宗主國派人擔任,但一直都存在着動員大批使用土語人士接近規範語言的足夠動力。
最後一點,澳門,尤其是在本世紀,推行了一套有力的敎學計劃,大力强制地用葡語矯正土語。有些澳門土生葡人告訴我們,在三、四十年代,孩子們在學校裏一旦被發現講土語即要受罰。
但是,這種强制性的語言矯正並不是以統一方式在所有使用者間實行的。語言的同化融合程度因各種不同因素,如年齡、性别、社會層次、文化程度及與規範語言使用者接觸多少而異。
還應指出,與規範語言同化的過程進展比較緩慢。在那裏有一個非土語化的進程,這個進程的每一階段中均可觀察到一個非土語化的連續統一體,即和土語使用者不同社會層次、種族和性别相聯繫的同步階段,上述因素不僅決定了一個講土語人的受敎育程度,而且也決定了其與宗主國規範語言的接觸機會。
馬爾克斯·佩雷斯(Marcpues Pereiva)指出,至少可準確地爲他那個時代的土語分爲三種不同類型,並認爲,那個時期的土語仍具有較强的生命力,即使不用在公開地,與官方打交道的塲合,也在家庭中使用。
1、封閉式的土語或曰純正土語(如果可以如此稱呼的話),是最吸引人興趣的,一般均爲社會低下層的語言。
2、隨着潮流變化而逐漸和葡語接近的土語,多爲性格圖滑善變,與宗主國人員接觸較多者使用。
3、中國人講的土語。
一篇寫於1920年,大槪同樣出於馬爾克斯·佩雷拉之手的論文指出,澳門土生葡人的語言與眞正的葡文相差甚遠,此種方言有三種形式:1、低下層使用的語言;2、一種與純正葡語更爲接近的語言;3、中國人講的土語。在那裏(指澳門)有幾份葡文報刊,文學水平似乎要高過果阿。
由以上論述中可以推斷,上世紀未存在着一個雙語並存的時期,“公開塲合及與官方打交道時”和“家庭中”分别使用不同的語言,同時也可看到一個正在進行中的非土語化過程,以及不同社會層次的不同進化程度。
本托·達法蘭西將這一非土語化進程中與規範語言的不同程度的同化歸因於性别的不同。
“與我們接觸較多者,所講的葡文尚可接受,儘管發音中帶有新拉丁語在熱帶特有的緩慢輕柔的變調。然而在他們之間。特别是女性之間,使用的語言,因其怪異奇特和約定俗成,使我們歐洲人無論如何難以明白。”
“在表示喜怒哀樂的私人交談中,除了一些混雜的詞語之外,再用一些隨意編造的詞語,加上詞意完全相反的短語和約定俗成的短句,如此將語言印上了十分原始的模式。”
以上所講的非土語化進程導致了土語的最終消亡。但是,時至今日,澳門土生葡人家庭交談中還會流露出一些土語的痕跡。
“儘管這一切(指入學敎育),在學校學到的葡文並不完全用在家庭中,那裏會出現一些他們明知是錯誤的表達方式,在和宗主國人員交談中則會即刻改掉。例如,三塊錢,他們將錢說成單錢,但是知道應該變復數。”
除了以上擧出的語言形態方面的情况,巴塔亘(Batalha)還找出了其它許多的土語痕跡,有句法亦有詞法上的。
上個世紀保存下來的用澳門土語寫成的文章,因其本身呈現的許多不同,也明顯地體現了當時正在進行中的非土語化進程。更有意思的是,從一些文章中還可以看到,土語使用者當時已意識到了其語言結構之低層次和向規範語言改進的壓力。
馬爾斯·佩雷拉還講到了學校中葡文敎學的效果: 隨着宗主國在殖民地(指澳門)公共敎育中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情况發生了顯著變化。這裏姑且不論這些政策的執行情况的好壞,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未曾去過葡國的土生的講話方式,還是報紙文字,其葡文的準確性遠勝過印度的土生葡人。
緩慢的進化過程,土語痕跡的遺留,不僅體現在語言而且也體現在澳門土生的文化中。土生人對其祖先語言所表現出的親切感說明,澳門土語的自行消亡或曰自殺,是無痛苦無反抗的。
一個被迫消亡的例證
一種語言的被迫消亡,其過程遠比上述自行消亡要迅速、劇烈和突然。
首先,被迫消亡必然發生在兩種互不相通的語言並存的同一地理環境。政治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語言在一、兩代的時間內即可將某一社團作爲母語的土語取代。
被影響的第一代人一般從童年起即可使用兩種語言: 能夠講從父輩那裏學到的母語,又能夠在公共塲合、商塲和學校運用當地的統治語言。
由於土語社團一般經濟資源短缺,加之其傳統職業,如漁業(馬來亞)、農業(開利開爾)和和小手工業(達曼),面臨着該地區經濟變化而帶來的威脅,因此就將移民作爲一種維持生存或改善其經濟狀况、社會地位的選擇,於是就進入了一個完全講不上其母語的全新的語言環境,迫使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放棄母語。祇有在拜訪長輩時才偶然用之。
而當移民在同一地區的人數較多時(如新加坡和香港的土生葡人),因血緣和同一本體建立在文化、種族和語言等因素上的聯繫,使土語有可能在幾代人中繼續使用。
澳門土生葡人移民香港是另一個有意思的例證。移民帶去的土語本來可能已經歷了向規範葡語被迫改進的某些階段,然而當地的統治語言--英語和廣東話的包圍,很快就促使那裏的土生葡人放棄自己娘家的語言。
在新加坡、馬來亞土生葡人社團從未經受過與規範葡文同化的壓力,除去和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葡國傳敎士接觸時需要,葡文在那裏很早就不用了。地理位置上的毗隣,新移民不斷湧進·加之宗敎所起到的强有力的聯繫作用(無論是到馬來亞參加宗敎儀式還是新加坡土生葡人社圑之間擧行的聚會),都使他們在幾代人的時間內仍能使用自己的語言(土語)。但是,今天的年輕一代已不再會講這種語言了。
對於定居的移民來說,抉擇是改變職業。從漁民、農夫變成工人、公務員或從事服務行業,這些工作要求他的掌握官方語言。同時,靑年人所受的義務敎育都是官方語言敎授。年輕一代在他們之間或家庭中使用官方語言的趨勢亦被其父輩所推動,因對子女前途擔憂,家長們都努力要求後代熟練掌握官方語言,以期找到提高社會地位的好職業,於是我們發現,馬來亞土生葡人社團中大多數家庭都將英文或馬來文當作娘家母語。
類似的情况同樣發生在印度土生葡人社團中,英文或當地語言被認做是社團母語。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社團一直以來都是雙語或多語並用,因係一個多語社會的少數民族。如今,如果說多語制在這些社團中仍然保持着,那麼土語却不再算作一部份了。
這種一般是快速的語言消亡過程,有個别時候也會推延。例如在一些仍然保持傳統職業的較封閉的社團內,土生的語言和文化在與有關語言和文化同化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較爲緩慢的再造過程,這就開利開爾土語經歷的情况。由於和講馬拉塔語的社團毗隣,其經濟活動--漁業和貿易,與基督敎村落互爲補充,創造了一種共存的關係,促成了某些文化形式(如飲食和服裝)的變化和語言再造,這種再造不僅是通過詞滙的逐漸變化(即由馬拉塔文詞滙代替土語詞滙),而且也通過句型和句式的重新組合,土語和葡語的一般句式(主謂賓),讓位於按典型的馬拉塔文再造的句式(主賓謂)。類似的句法再造也出現在斯里蘭卡土生葡人社團中,那裏是按照坦密耳語的形式。
毋庸置疑,地方語言的包圍和因社會、經濟變革而出現的文化融合幾乎將這些土語完全同化。另一方面,將土語視爲這些社團的文化宗敎本體的良好傳播工具而抗拒其被吞沒,隨之變成了一種爲爭取土語生存而進行的長期抗爭。
人物索引
吉思·艾特桑,1981年,《語言變化: 進步亦或衰退? 》,倫敦: Fontana Paperbacks 。
格拉西特·諾盖拉·帕塔亞,1959,《澳門方言之現狀》,葡國語言雜誌,1958年第9期,科英布拉。
達尼濟·帕萊羅,1943─44,《澳門的葡語方言》,《復興》,澳門。
本托·達法蘭西,1897年,《澳門及其居民》,里斯本,國家新聞署。
大衞·德坎波,1971年,《關於非土語的延續的一般研究》,語言中的行話和土語,劍橋大學出版社。
弗古桑C. A. ,1959,《雙語),世界,15:325。
大衞·杰克遜,《不害羞的歌》,印度土生葡人土語的詩歌口譯。
萊莎·阿爾梅林多,1970年,《澳門人類學和人類社會學》,圍盧兹大學社會科學系論文。
馬盖斯·佩雷拉,1901年,《土語歌集》,里斯本,出版公司。
埃德卡·帕洛梅,1983,《土語化及語言之變化》。
埃莉亞娜·聖賽奧,1959,《海外擴張初期二百年間的葡國婦女》,--巴西研究國際滙編,里斯本,第Ⅰ卷。
伊思·盧賽爾·史密斯,1977,《斯里蘭卡土生葡人語言的發音》。
瓦沙布和格林菲爾德,1983,科內爾大學論文《大西洋土語的發展》。
全部外文引文均由作者翻譯。文中還保留了葡文和土語引文的原來拼法。
(鄧炘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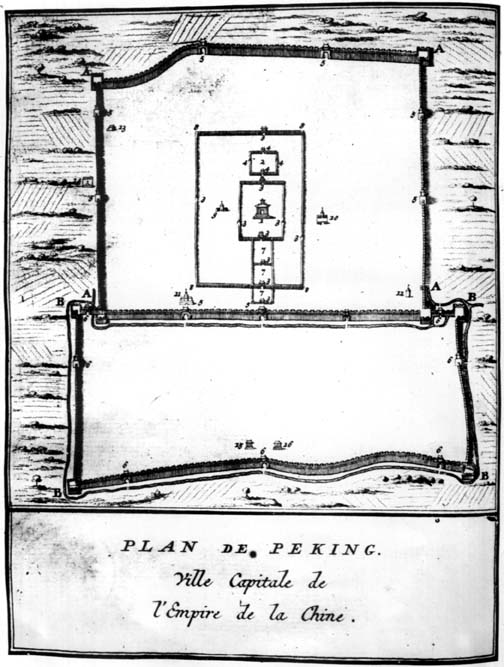
註釋
(1)、伊思·漢考克著: 《土語化和語言的變化,區域的開發》。
(2)、在馬德拉和亞速爾羣島,同樣地僱用了加納利的奴隸,但都未能產生土語,大槪是因爲這地的宗主國殖民者人數大大超過了奴隸的人數。
(3)、作者譯。
(4)、作者譯。
(5)、作者譯。
(6)、作者譯。
(7)、弗朗斯·博布(1827),引自奧·杰西珀桑著。《語言,其特性,發展和來源》,倫敦,1922年,艾倫和安溫,第65頁。
(8)、原文係意大利語。
(9)、和平手册,第13册,84:4。
(10)、抄自Barreias’1943 Barreias’1943:89。
(11)、杰克遜,即出版,第158頁。
* 作者爲(美國德克薩斯)奧斯汀大學語言學系研究員,澳門文化司署資助學者。